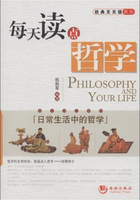漆黑的夜晚,外面阴森而寂寥,我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时不时可以听到风敲打窗户的声音,它在阴冷的嚎叫着,现在已是午夜时分,我能感到外面有一个黑影掠过人间,它的黑色逐渐蔓延,进而变为吞噬一切的黑暗,我不敢多想,口中默默祈祷着,祈祷这一切只是我的一场梦罢了,头一回,我是这样期待黎明的到来。
应承岑扬的预言,已经有一个又一个的人,继王阿姨之后,悄无声息的死去了。
同以往一样,当有人发现他们的尸体时,面具已荡然无存。
他们的面孔各式各样,有的年老枯黄,还覆盖着黄色雀斑和层层皱纹,有的却年轻俊俏,死时脸颊还泛着点点红晕。
可有一件事,我猜错了,岑扬也猜错了。我们这里的人虽然看似冷漠,虽然不怎么在乎别人的生死,却还是极度自爱的,在看到这么多悬疑案件后,我们意识到了,自己不再是置身事外的局外人,于是我们头一回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恐慌,聪明些的人,通过花样手段推断出这等诡异事件与元日有关,元日越盛,伤害越甚,至于他们是夜观星象还是查阅古籍,就不得而知了。
七天,七天的元日之期,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更何况,现在已不足七日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恐慌的人群。
他们像受了惊的兔子四处逃窜,他们瞪着大大的眼睛顶着苍白的面具奔波四方,暗暗祈祷着自己离开了这座城镇或许就可以逃过一劫,他们也像发了疯的狮群,在马路街道上横冲直撞,往日的交通规则行人规范都全然作废,遇到了树木,直直撞了过去;遇到了房屋大门,直直撞了过去……他们互相推搡着,房子倒塌了,没有人看见;车辆侧翻了,没有人看见;植物在尖叫,动物在嘶吼,而我们,在垂死挣扎。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说!”镇长高举着双手想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是现在人命危机,谁还顾得上听你讲话,镇长百般无奈,只得咬着牙抬起自己一条腿,手脚并用的费力爬上轿车的顶部,他平常运动甚少,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后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后,他接过一只红色的大喇叭,深吸了一口气喊道“大家停一停,别挤了!就算你们逃出去也是没有用的!”,这一声中气十足,公鸭嗓也亮了出来,众人这才停下了手中动作,不是因为他吼的声音,而是他最后的这句话。
“大家…大家听我说!”镇长一手扶着膝盖,一手插着腰费劲的喊道“虽然元日即将到来,但关于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我们也不甚了解,况且这荒郊野岭的你们能去哪里?若元日之说是真的,这是千百年一遇的壮日之景,又怎会只是涉及到我们一座城镇,别的地方也定是如此啊!所以……若要贸然出逃,实属下策……”镇长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嗓子都变得嘶哑了,他垂下喇叭揉了揉酸疼的手臂,重重的咳嗽了几声。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一个人大声叫道,“是啊是啊!我才二十出头,我从学校出来刚刚进入社会,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怎么能这样对我?”一个穿着毕业装束的年轻人捶着胸口大喊道“若元日是真的…那我岂不是只有几天的生命了,那我这么多年的辛苦算什么,都白白浪费了!”,“这算什么?最起码你还活了二十年,你还为自己活了二十年呢……”一位梳着发髻的妇人哽咽道,她白皙的臂弯中还抱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正在吮吸着大拇指,一双眼睛圆通通的,他还太小,定然不明白这些大人为何这般吵闹“我的孩子…他生下来还不满一年啊,老天就要夺走他的生命,那我当初还不如不生!”,妇人的声声哀啼将人们的情绪又引的爆发了出来,他们有的从头到脚的捶打着自己,有的已站立不住倒了下去,倒在旁边人的身上,倒下了的顺势就瘫在扶住或撑住自己的人身上大声哀嚎着,他们抱得是如此之紧,离得是如此之近,我想,在这一刻,我们不再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们不再是尔虞我诈的竞争对手,我们是一样的,一样的被命运玩弄于掌心的可怜人,城镇哀声不断响彻云霄,声声嘶吼似乎要将厚重的云雾破开一条锋利的口子,可那太阳,却仍然躲在乌云身后,亦正亦邪的泛着光芒。
突然,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中音传了出来,从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中,电脑中,车辆中,传了出来。
“大家好,这里是“领航员”空间站,现面对全球做最后播报,由于元日即将到来,在未来的几天里,我们将面临前无仅有的重大灾难,在各方人士的拼搏与牺牲下,我们确认有关元日灾难的消息属实,但万分遗憾的是,元日的破坏之大已经超出了现有的科技防御水平,我们,已经丧失了最后的机会”
“我们是人类,有着人类的尊严和骄傲,即便到了最后一刻,即便到了生死关头,我们也要延续人类的文明,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英雄,亿万年后的新世界新家园也一定会铭记着我们的牺牲与奉献,为了我们的家园而死,我们是死而无憾的”
“在元日来临之前,在太阳将这里的一切燃烧殆尽之前,我们还有不足七日的时间,请大家回家吧,抱一抱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吻一吻自己的父母和朋友,祝愿每一个人都能与心爱的人团聚,好好的道别,在最后的最后,祝大家幸福美满……”
广播停了,整个世界仿佛被颠覆了一般,鸦雀无声。
取而代之的,是永无止境的绝望,是黑色幽灵般的空洞无神。
这段广播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压死了人们最后的希望,它直白的告诉我们,告诉所有人:嗨,快看啊,看你们这些蠢货!死就在眼前了,还哭个什么劲啊!
我们,已经连哭泣的权利都丧失了。
我们站在原地,呆呆的望着天空,望着地面,望着看不见的远方,双目毫无神采,只有无限的空洞,好像被掏空了身体取走了灵魂,嘴唇下意识的蠕动了两下,却又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我感到脸颊有火辣辣的痛,它像是被人狠狠揪住,扯得生疼,我痛的呜咽起来,这才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发出或轻或浅的吸气声,他们的手也不安分的在脸上抓来抓去,甚至将尖利的指甲抠进了肉里,肉眼可见的是,我们的面具,好似在慢慢脱落。
“完了完了!别揭下来,千万不可以揭下面具!”一个人跳起来大吼道“你们忘了吗?死去的人都没有脸了,只要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去的,这个...这个...”那人拼命指着自己的脸道“只有一直戴着这个,我们才能活!”
那人的话语犹如醍醐灌顶,其余的人一听恍然大悟,都强忍着脸颊的不适,甚至用左右手死死的附在面上,似乎想用这种方式将面具盖的紧一点,他们捂着脸喃喃道“还在,还在...我的还在...我不会死的,一定不会...”
我在人群中被挤得东倒西歪,只有脚尖勉强能挨着地,稍有碰撞便整个身子都被荡了起来,忽然,一双手扶住了我的肩膀,我惊得抬起头,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岑扬一只手阻挡着来势汹汹的人群,一只手环住我的腰,随着他手臂渐渐用力,我整个人已被圈进了他的怀里,我安静的看着他,看着他的汗珠顺着脖颈流下,看着他紧锁的眉宇,看着他太过干裂甚至出了血的嘴唇......
突然,我挣扎着抽出一只手,按下了他的头。
我感觉到,岑扬扶在我腰上的手颤了一下,他的呼吸错乱不已,他猛地向后退了退,惊愕道“你做什么?”
“没什么...就是”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只觉得世间万物都已消失不见,我能看见的,只有他这一个人和那一双唇。
“就是,看你嘴唇干裂了,都出血了...”我忽然心生烦闷,不想再胡言乱语的解释些什么,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呢?我心中恼怒渐起,反而生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来,只踉踉跄跄的离岑扬又近了些,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岑扬反而被我看的有些窘迫,他微微别过头去,一时不知说些什么,看他神色古怪异常,我突然觉得很好笑,蓦地,我竟双手环过他的脖子,踮起了脚尖。
我闭上了眼睛,朝着那片清凉,朝着那片净土,深深的吻了下去。
蝴蝶的吻,带走了鲜花的梦;清风的吻,触动了明月的情;小溪的吻,湿润了岸边的堤;柳条的吻,拂动了湖水的涟漪。
岑扬的唇冰冷微凉,初碰时冷的我打了个寒颤,一呼一吸间似乎都处于寒冬大雪,可我不甘心,我强制性的覆在他的唇上,轻轻擦过那流血的伤痕,将我的余热缓缓而渡,我的手脚已经冻得麻木,黑色的发丝也都染上了点点雪白,我紧紧拥着他,双手抚摸着他光洁如玉的脸庞。
岑扬并不反抗,他只是一动不动,犹如寒冬世纪希腊的冰雪雕像,我闭着眼,不知他脸上是冷漠还是惊愕的神情,慢的,慢慢的,岑扬俯身,回应了我苍白颤栗的亲吻,这像是惊雷一闪的迅速,又像是流水飞逝的永恒。岑扬浅浅的吻着我,蔓延出了绵绵的温柔,方才的大雪纷飞,方才的刺骨寒风,在这一刻的深情和炽热中消失殆尽,真情能融化一切,即便是嚣张的冷漠在此刻也只能沦为一旁的祝福者。
鼻尖飘过岑扬身上的清香,清沁,清凉。
时空好像冻结了,好像就一瞬,好像又很久,犹如雪花飘落冰面刹那间的凌结。
周围的人群还在你推我搡沸反盈天,愤怒的咒骂声,叫苦连天的悲啼声,孩子受到惊吓的哇哇大叫,有的人站在屋顶上烧着大把大把的纸币,那是自己多少个日日夜夜辛苦赚来的,此刻却都一文不值了,有的人则跪在地上痛苦道自己离家太远,离心爱的人实在太远了,就剩下这几天了,这怎么够啊,怎么够回家啊!元日还没有到来,可末日却似乎已经来临了。
只有我们两个人,独立于世俗之外,喜悦于一吻之欢,其实这样也挺好,若是往常,我怎么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勇气呢?还好,还不算太晚,差一点,我就要与这份美好擦肩而过了。
不得不说,时间真的是个奇怪的东西。
一辈子很长,长到什么都可以改变。
可一辈子又很短,短到一件事都有可能做不完。
我的睫毛在风中颤抖,岑扬的瞳孔也在随着闪烁不定,他静静的凝视着,我默默的靠近,我感觉,感觉到了一片摇曳不出波澜的月光。
没有任何激情荡漾,
有的,
只是寂静的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