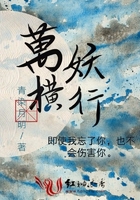年底的时候,芭蕉换了第四个男朋友。
豆红也有了她不为人知的新动向。
圣诞节前夕,芭蕉组织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酒局,这是隔了三年之后我和豆红第一次踏进C-MOON的大门。
我们去得晚了,离芭蕉约定的时间早就过去了半个小时,而我和豆红还在柳浪闻莺里那一排排冬雪覆盖下的草丛边不紧不慢地磨着。
豆红已经不是当年的豆红了,专心在家奶娃半年,这样的局蓦地使她紧张起来。
路上她不停地抚摸着大衣里自己那隆起的肚皮,偶尔使劲一拽,一叠松松垮垮的肉就被她抓在手心里。
紧接着她的眉心就一紧,眼神垂下来,干裂的嘴唇上起了一层小小的白皮。我看见了,心头一酸,从包里摸出一支润唇膏递给她。
“要不要涂点口红?”我问。
“怎么?”
“气色不好。”
她看了看我笑笑。
“我丑了吧?”她说。
“哪儿有!都说做妈妈的女人最美。”我慌忙说。。
“人都胖了一圈了,没心思打扮了。”
“运动几天就能瘦下去。”
“头发也掉了很多,发际线移后了不少。”她的眼皮垂下去。
“哎,保养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的。”我拍怕她的肩膀,拉着她便往酒吧的方向走去。
“对了,你写文章那个平台叫什么?”路过C-MOON前的广场时,豆红问我。
我吃惊地转过头,不明白她这么突然一问。
“我想起这么久了我竟然都还不知道你在哪里上班。”她说。
“在哪里上班?”
“是啊,你公司在哪儿?你现在的话……待遇怎么样?”豆红惨淡地笑着说。
我愣了愣。入职两年以来,这是豆红第一次问起我的公司。我马上一五一十地报上了公司的名字、位置,我如今的月薪、福利。
说完了,发现眼前的女孩还陷在独自的沉默里。
酒吧在柳浪闻莺一带,又是一年过去,西湖里依旧人声沸腾。遥遥地一望,C-MOON猩红的招牌在黑夜里闪着刺眼的光。
“这里变样了。”豆红蓦地说。
我望着周身铺了一遭大理石墙面的铅灰色外墙,一时间也觉得怅然。
这几年西湖边的文娱场所变了个大样,无论吃的喝的都往当下风靡的网红风靠近了。C-MOON也一样,旧日子里那幢朴实的木房子如今冷然变成寒气逼仄的性冷淡水泥盒子,屋前还有一个粼粼的水晶池。
侧头一望,里头没有鱼,印着黑金字体的水晶瓷砖密密麻麻地镶在池底。
“这些名字……”我指着瓷砖疑惑道。
“好像是些网红的名字。”豆红说,“最近的综艺里都有。”
芭蕉从褐色的胡桃木门后闪出身子来,用胳膊将我和豆红一左一右地搂住,“哈!你们都来啦!”
我笑着巧妙地将胳膊移开。芭蕉便两只手都去挽住豆红。
“你看,你们现在一个宝妈一个宅女多难请得动!知道吗?这里换了老板,味道也全变了。”
“是哦。”我想了想说,“那我们进去吧。”
“哎,等等。”芭蕉神秘的一笑,“还要等个人。”
“新男朋友?”豆红问。
“不是啦”芭蕉嘿嘿的一笑,转动着眼珠子,“是等这里的老板,于—宣—吟—”
啊?豆红惊诧地望望我,又看着她,我也感到一阵匪夷所思。这些年来于宣吟这个名字逐渐早就消逝在过去的记忆中,连她的长相,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起来了。
然而随着芭蕉渐渐地讲述与她有关的事情,我想起大学时期是总有个消瘦脸蛋上印着孤傲神情的姑娘,总是不合群,总是一个人走着。
大家都说她给一个教官做了情人,后来被男方甩开,因为宫外孕在医院足足躺了一个月,学业中断了,人前的脸面也都没了。
“她在班上没什么朋友,吃穿用度却都不凡。”当年芭蕉总是在背后哼哼地说,语气眼神颇为不屑。
然而多年过去,对象还是同一个人,现在的芭蕉却带着近乎崇拜、近乎骄傲的某种神色讲述着她,甚至在这样飘着雪的圣诞夜里,自愿拉着朋友们在寒风中缩着身子等她。
我的朋友们,她们在经历各自部分的人生之后,因为各自的经历对彼此都有了一点点的理解。而这一点点的理解,加上多年来并不曾有其他真正的朋友出现在各自生命里,这便足以加重了她们久别重逢后的感情。
现在的芭蕉挽着豆红的手,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她们共同感兴趣的某个人,而豆红,也睁着眼睛好整以暇地听着。
她们挽着手,互相挨着,好似因为共同认识宣吟这件事,一下子将两个人这么多年来的恩怨全都挽走了。她们乐此不疲地谈论着,豆红对这些事的热情看上去也比以前感兴趣多了。
我的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一点笑容。那点笑容埋藏在这年冬天圣诞夜里,谁都没有意识,后来西湖里的风一过来,当然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