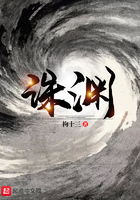也许是刘盈见有两位兄弟帮衬,又也许是刘盈的病一日重于一日,他上朝的时间越来越短,直至开始退居于宫内养病,同时指派赵王刘如意与代王刘恒分别处理朝中事务,月余下来,两王代政倒也谨慎,虽然没什么建数,偶尔还会出一些差错,但总的来说,还算是井井有条。
只不过,这种磕磕碰碰的政务处理的过程中,一些朝臣渐渐的向两王靠拢,并且逐渐形成派势。偶尔还会小有争论。也多亏两王皆以‘弱’示人,那争论才很快消退。
不知不觉,又过了将近十多日,边界告急。
大汉帝王重病不能理朝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匈奴,匈奴的军臣单于也不是吃素的,当初刘邦离世时,就已经以书信辱过吕后。今日这等天赐良机,他又岂能错过。
振臂挥师,大军压境,边界点燃锋火台。
消息传来,举朝哗然,战与不战的争吵、已经不止是两王说些谦虚安抚的话就能解决的了。
而这也只是一个导火索,将近两月的不满与对立而积下的矛盾之火迅速点燃。
满朝火药味浓重。大大小小的吵嚷又是持续了十多日,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传信的使者依旧没有弄清楚,到底何时启程回边界复命、又到底何时帝王会派大将领军至边界。
就在这时,齐王嫡子刘襄再过三四日的行程也要抵达长安城了,只是据说,他人虽然还在途中,却也知晓了匈奴大军压境一事,为了表示对大汉的忠诚,他当即下令原地驻扎等候封地调动来的一万军士,同时上奏汉帝刘盈,他封地十万军士随时待命,若是汉帝有命,当即开赴边界支援以共同驱除匈奴贼子。
刘盈听完审食其的禀报,当即冷笑出声:“他的消息倒是灵通。”
“想必是朝中吵嚷十几日间,有人传讯于他。”审食其恭身道。
“转告太后,我俱已知晓。你退下吧!”刘盈恢复面无表情,虽然吕后信得过审食其,且审食其的所作所为也的确尽心尽力,可是刘盈就是没法喜欢审食其。
“诺!”审食其作为臣子,也只能在心中苦笑,既然完成吕后交待的,退下也是应当应份的。何况帝王已经下了令了。
“太后想是该有些作为!”张嫣跪坐在刘盈的榻边,听完所有对话之后,伸手将案上已经凉了许多的汤药拿起,边侍奉着刘盈服药边道:“若依然如此安逸下去,该当引得他人疑心,届时陛下功亏一篑,可白白受这躯体煎熬之苦了。”
“阿母这两月有余并未放松布置,她的动向如今人人皆观之甚重,阿母不会轻易授人以话柄、自然也不会轻易叫人看出异端。且,朕也从未轻看过任何人。只是……朕此次也算是开眼了,这些人比朕先前所料想还要神通广大……”刘盈停顿了两次,笑意中带出些嘲讽道:“兄友弟恭,看来,真如阿母当初所言,那只是朕的一厢情愿。”
“所谓一朝蛇咬,多年惧绳。日照下总有阴阳两面。”张嫣略微皱眉,两世为后,她是了解一些刘盈的心理了,这一世不管怎样,对于刘盈过于仁厚与脆弱的性格,无论如何改变,都不希望刘盈走向另一个极端,曾经的吕后有一个就够了,这一世吕后没有前一世凶残,而她也不希望刘盈走极端后变成似前世吕后般过分强硬作风的刘盈,于是她道:“陛下可莫要思虑过重,这世间美好还是多过陋相的。”
刘盈边听边饮下那泛着苦味的汤药,放下药盏后,他的唇角露出一抹虚弱的了然笑意道:“阿嫣待我至厚,我又岂能让阿嫣失望。阿嫣之意,我胸中自是知晓。”说完,他又靠回身后的引枕,张嫣将薄毯为他重新盖好,随后朝他看去,两人目光相碰,其中之意并不要说透,当事人心知肚明就好。
这一次计策,刘盈从最初的计划隐瞒,到后面渐渐向张嫣吐露实情。
于他、与她都是一种极大的不同。
宫人之变,成败至关重要,多一人知晓就多一分风险。非至亲至信之人不能相告。
否则他也不必在初定计策时,即选择真的以肉体之躯去赌这个局。
“陛下晓得就好。”张嫣终是收回了目光,他深陷下去的眼窝与憔悴的面容,让张嫣才压下不久的酸意又涌现出来,她不忍再多看。
“真是瞎了你等的狗眼。”大殿上,正当各朝臣再一次争执着让其中一位大臣,当场脱下鞋履朝反对者砸了过去时,一声中气十足的怒吼自殿外传来,震慑了群臣、也让众人心底那似期盼又似畏惧的心颤抖了起来。当然,也不乏有本就等着静观其变的朝臣们,心中不以为然。
纷纷停止言行,看向踏足进来的吕后,恭敬行礼之后,再次分列左右站好。
吕后傲然行至主位上,威严缓缓的转过身来,厉目招过众朝臣,道:“你等多半自先帝时期即已入朝,江山社稷有尔等的功苦、尔等的心血,而如今……”说至此处,吕后略微停顿,显得痛心继续道:“陛下身体有恙,正是需要尔等尽心尽力之时,尔等却在此喧哗争执……若是先帝在世,见到尔等如此,该当何是想?”
吕后声声质问一声高过一声,眼神锐利,丝毫不减当年先帝薨时的决绝立帝之威。一下子众臣纷纷噤声。
毕竟是多年的朝臣,有些话不必要说的太多,就这几句,也算是直接打上脸面。何况,这些朝臣对于吕后的了解,各个心里都清楚,再让吕后说下去,有可能他们中的几个就会被捞出来,然后直接定个罪名。
于是,短暂的沉默之后,有些朝臣就纷纷出来请罪。
而那些各有心思的人,在朝中借势煽风以察看局势之人,也只好鸣金收兵。
朝堂的那一幕短暂的风波,让许多观望的人心安了不少。
吕后的出面,是因为朝局的愈加混乱,而朝局之所以混乱,完全是出于刘盈这个帝王因病而无奈的放手。
对于这样混乱而难控制的局面,吕后的急切已经完完全全的呈现在世人眼中。
所以,对于在局内的所有人来说,一切都是时候了。
“刘襄的五万军士驻扎在城外。”病榻上的刘盈,在看过手上的竹简之后,唇角含着讽哨的笑容,看向张嫣道:“于今日午时时分,他奏请我下诣封他为齐王!”
张嫣抬眼,看向刘盈,也跟着笑道:“真是沉不住气!这点军力就想逼宫!?”
“他自然是知晓的。”刘盈道:“只是他还有后手。”
“再有后手,也被他的这一肆无忌惮而暴露了。”张嫣含笑的看向一旁的沙漏,微微无奈的摇头,道:“他如此失了分寸,想必也是探听宫内之事俱多之后,惊惧之心更多一些。”
“心中有鬼,自当如此。”刘盈放下竹简,‘请君入瓮’之计谋成的愉悦一过,一股疲惫感就涌了上来:“为了权势,兄弟可以相残,为了权势,甚至可以弑父,刘氏江山至我之手,也只不过二代,为何会有如此繁多纷争,子嗣多不是意寓着多福多传承,可为何到头来,往往余下的也就一二,唯留下更多的血腥杀戮而已。又哪来的福!?”
听着刘盈的感慨与伤怀,张嫣也被他勾起了一丝沉重。
她不语。不是无话可说,而是知道,此时此刻,再说什么都觉得苍白与无法释怀。
尤其是他们俩人现下等待的,就是兄弟相残的最后一刻,最后那要了结的一刻,或者也可以说是,拉开兄弟相残的第一场明面上的序幕。
正午时分,一阵与以往并无不同的脚步声传来,刘盈的双眼已经半闭上。
而张嫣,也与往常无异,她让宫人将汤药放下,眼看着宫人悉数退下,张嫣从宽大的袖口中取出一包药粉,这一包药粉放入汤药木碗之后,汤药的颜色有一瞬间的变化,随即在几丝涟漪之后又复归原样。
张嫣的眸色越来越冷,她盯着汤药看了几秒,待她抬起头时,刘盈不知何时已经睁开了双眼。
她看到了刘盈眼中的一丝伤痛,那一丝伤痛渐渐隐去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决绝。
这种眼神,终其张嫣三世至今,还是头一次从刘盈的眼中看到。
她深知,刘盈的蜕变已经由内心的煎熬、渐渐转变到他的付诸行动上了。
帝王的举止直接影响到朝代的格局,这一世,她相信、也肯定,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事要发生。
今日的天气晴好,淮南王刘友举目望向天空,清澈湛蓝的天空,像是洗过一样,天地间的静谧之下,从远处望过去,还以为刘友正沉浸与陶醉在这美好之中。当然,这必须要先忽略他从上至下的阴沉气息。
其实,他在等,他在等着前方宫殿中,传来阵阵喧哗与惊叫!
那是他从未有过的期待,他极其期盼着这一刻的到来。
果然,他多年为的愿望已经实现了,那慌乱的、惊恐的无措的声音告诉着众人,现在宣室那儿一阵混乱。
当下匈奴蠢蠢欲动,若是帝王再有何大不妥,那这种混乱对于大汉现有的局势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不过,也只有在这种打击下,对于有些人,才可以做许多事情。
因为来回奔跑的宫人与宦者们,脸上的表情渐渐化成恐惧,那是一种即将面临死亡的恐惧。
刘友的唇角缓缓上扬,可是也只是瞬间的功夫即隐去不见,取而代之的也是一种惶恐与无助。
“说,为何如此惊慌,方才有人说陛下……,陛下那儿,可是有何不妥?”刘友急匆匆的赶来,伸手抓住一个跑的似无头苍蝇的宦者,问道。
“陛下昏迷不醒,宫中医者也束手无措啊!”被刘友抓住的宦者,一见是他,慌忙跪下,满心的惊惧化成失控的哭泣,道:“太后大怒,要处决所有宣室宫人。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什么!?”刘友似是无法承受这种讯息,他后退两步,不敢置信的看着眼前宦者,突然提高音量,似是极怒,道:“一派胡言!尽然在此胡言乱语诅咒陛下安康之体!拉下去……”
“淮南王休怒、休怒!奴才句句属实,无有虚言啊!”跪在地上的宦者本就极度惊吓了,被刘友这么一暴喝,虽然刘友的年岁并不长,可是到底手上也是有权掌握他们这些宦者的性命的,当下整个人就瘫倒在地上,嘴里也是有气无力只能反复的喃喃求饶。
刘友似是忍无可忍的模样,他拉着宦者衣襟的双手猛的松开,抬起一脚又踢揣到宦者的身上,最后一摆衣袍,就往宣室殿的方向飞奔。
一到宣室,整个殿内的气氛肃穆却是死寂。
吕后满脸怒意与死灰般颓丧交织在一起的表情,让刘友的心头更是确定此次刘盈凶多吉少,想到自己那碗汤药及给他递汤药之人所言,他更加确定,刘盈的死期也就是这两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