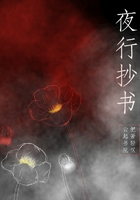我收工回家,把铁锹放到门背后,看见马鞭还挂在墙角,上面已经蒙上了薄薄的尘土。我连钉子一齐将它拽了下来,一撅两段,扔出了大门。
“回来啦?”她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筐鸭蛋,笑着问我。
“回来了。”
“牲口卖了,你舍不得吧?”她把鸭蛋一个个拣到坛子里。坛子里盛着熬好的盐水。
“有什么舍不得的?我连人都舍得!”
屋里暖烘烘的,铁炉盖烧得通红。我把手在炉子上烤热,然后闭起眼睛,将手焐在脸颊上。我感到一阵舒适的晕眩。这就是家,这就是人人都需要的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温暖。但人创造了什么,就会被他的创造束缚住。这冬天的炉火,这些坛坛罐罐,这两间小屋,是供我享受的,但我也付出了自由作代价。
“我在给你腌咸鸭蛋哩,你看!”她在我背后说。
“有什么看头!”我睁开眼睛,漠然地瞟了她一眼。
她并不觉得无趣,停了片刻,又笑着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结婚时候买的小鸭子,这会儿都下了这么多蛋了。”
是的。猫也长大了,这时无忧无虑地卧在炉台上。眯着眼睛打呼噜。这只猫就是那天晚上从曹学义胯下钻出来的灰猫!它也和大青马一样,看到过许多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人最怕的是人,而不是动物,即使是猛兽。
她低着头,继续往坛子里拣鸭蛋。鸭蛋并不沉下去,悠悠地浮在盐水上,雪白的一层。她用愉快的声调问我:“我听说,南方人都爱吃咸鸭蛋,是不是?”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听说的事情太多了!”
她抬起头瞥了我一眼,眼睛里的光芒暗淡下来。一会儿,她撇了撇嘴,谨慎地嗔怪我说:“我的话,你总忘不了!”
“话是会忘记了,但是事情是很难忘记的!”
说完,我一掀门帘进到里屋,在我的用门板做的书桌旁坐下,拿了一本印着“红卫兵日记”封面的笔记本,摊在面前。
写作的愉快不完全在于与出了什么,而多半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分析、综合、推理、判断,这些大脑的智能活动,就和体育运动一样,并不是非要争取到名次才使人高兴,在身体各部分的活动中就可以享受到发挥活力的快乐。将近二十年,除了“自我检查”、“检讨”、“每周思想汇报”、要求粮食补贴的“报告”和那份要求结婚的申请书,以及代替别人抄的“大批判”文章,我没有正正经经写过什么文字。也许,这就是改造我的手段和我改造的目的?象剥兽皮一样把文化从人身上剥离下来,这个过程对于被剥的人来说虽然很痛苦,但对猎人来说却是必须进行的。但在四个月前,在洪水的危险过去以后,在我又成为正常人以后,我开始拿起笔来。最初几天,笔下非常艰涩,几乎写一个字就要停顿一下,大约古代人刻竹简就是这副模样吧。大脑和手指间的传动器官出了严重的故障,生锈了,而且锈死了。脑子里能想出的,嘴上能说出的语言,怎么也不能流利地变成文字,必须两眼呆呆地一个一个地从空中去寻找。但不久,这条传动器官由于经常运动的结果,渐渐地灵活了,一个一个生疏的字也重新熟悉起来。在没有人能够畅所欲言地交谈的情况下,孤独地写作,成了最能帮助思想的手段。大脑里的一个概念落在笔下,变成了由点、撇、横、竖、捺等等构成的方块字,即刻成了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不由得使你要去探究它和别的概念的联系,然后把一个一个方块字配搭起来,串连起来。杂乱无章的思想,一霎间理性的灵感,从书中的某一句话产生的认识飞跃,即使是痴人说梦、梦中呓语,都能通过笔梳理得有条不紊、纲目并张。
在视、听、味、触觉的愉快之外,还有一种理智运行的愉快。这欢愉之情并不是因为得出了什么思想结果,而是从视觉所不能透过的地方,从被人生的重负覆盖的深处,看到了只有属于人的理性的闪光。并且,被摒斥于人群之外并不是坏事,而是获得了思想的自由,使理性得到了净化。这种净化了的理性开始时如荧荧磷火,继而不断地增强。它不能开辟道路,但它能照亮前方。
而前方的道路,是更加险恶了。
今天,我无心写什么。与其说是思想混乱,毋宁说是在把决心酝酿成熟。我把笔记本又合上,棉袄也不脱就朝炕上一躺。棉祆软和的领子擦在我的面颊。这是她一针一线给我缝制的。正如她颇为得意地说:“你大概二十年都没穿过这么暖和的棉袄了吧!”当然,马缨花曾给我用毯子缝过一条绒裤,但那仿佛是上一个世纪的事了,遥远得我都怀疑那是不是曾经有过,而现在,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女人善于用一针一线把你缝在她身上,或是把她缝在你身上。穿着它,你自然会想起她在灯下埋着头,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针,小手指挑着线的那种女性特有的姿势。因而那一针一线就缝上了她的温馨、她的柔情、她的性灵。那不是布和棉花包在你身上,而是她暖烘烘的小手在拥抱着你。
“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可是,吃,毕竟还是重要的,尤其对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农场每人每月只配给一两食用油。每到月初,何丽芳就会骂道:“X他妈!咱们打油光拿个眼药水瓶子就行了。每次炒菜的时候,往锅里按那么一滴……”而香久把她自己的一两油也省给我。她单另把油熬熟,撒上葱花,在每顿饭的面条里给我碗里调上一点。她从来不吃油,只在给我调油的匙子上舔一下。然而这种粗俗的动作表现了她对我的疼爱与关怀。她是必须把她的爱情表示出来,让你明白无误地知道她付出了多少,知道她爱情的重量与程度的女人。农场分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肉,她也从来不吃,总是啃骨头。我常常感到这样的爱情对我是个压力,是个负担,可是她却这样宽慰我:“我不吃肉,不吃油也长得挺壮,你不看,我现在还胖了吗?”她叫我捏她的胳膊。“听人说,男人比女人消耗大。你蹲过劳改队,还不知道?”
是的,六○年在劳改队死的,多半是男人。
总之,我和她结婚以后,过去单身汉的习惯突然被掐断了,续接上家庭生活的习惯。确切地说,家庭生活的习惯就是她给我培养出来的习惯。再往深里说,就早我生活的一切都要仰仗她了;我被她宠坏了。这暖和和棉袄,洗得干干净净的内衣,这被子,这褥子,床单,这炕。这房里的一切,哪怕那洁白如玉的雪花膏瓶子,那用廉价的花布做的窗帘,都出自她的手,但又构成了我的生活内容。她按照她的家庭观念完全自主地创造了这个小家庭,把我置于其中,我也适应了它,成了它的一部分。要摆脱它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首先要摆脱我自己。
我茫然地望着用报纸糊的顶棚。那上面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文字,但是没有一行字是解释生活和指导人们应该怎样生活的。这十几年来,人们象煞有介事地、正正经经他说了多少废话和大话啊!这无数的废话和谎言构成了一个虚幻的而又是可怕的世界。我象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真实的世界,我现在的处境,一个是虚伪的世界,而那个世界却支配我的生活,决定我的生与死。我不但要冲出那一个世界,还要冲出这一个世界。在前途茫茫,风雨飘摇的时候,难道这一个世界就不值得留恋……
她突然一掀门帘冲进房来。
“我告诉你,”她一屁股坐在炕上,满脸怒容,“你别老抓住我过去的事不放,你也有可抓的!”
她还系着围裙,使她丰满的胸脯格外地高耸着,两只手抹了润肤油,反复地揉搓,好象是在痛苦地拧自己的手。
“什么?”我莫名其妙地坐起来。我已经把刚才伤害她的话忘记了。
“我告诉你,你要抓我过去的事,想跟我离,我就抓你现在的事,反正咱们谁也好不了!”她的眼睛是滚烫的、充满怨恨的,没有一点眼泪,但却是一副要哭的样子。
“我……我现在有什么事?”我应该早料到她会发火。她总是象水一样驯顺,一样默默地积聚够力量,然后突然来个冲击。她这番火,大概就是在她腌咸鸭蛋时候积聚起来的,咸鸭蛋腌了,火也积聚充足了。
“哼哼!你每天晚上都在写些啥?”她说,“我看这个家,非要败在你手里不可!”
“我晚上没事的时候写点东西,关你什么事!”我故作镇静地间。
“当然关我的事!当然关我的事!”她叫道,“你要知道,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你有了家,家里是两个人……”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是的,是两个人!这点我为什么一直没想到?把另一个人蒙在鼓里,却又要叫她承担责任。可是,她又这样说:
“哼!你当是我不知道:你晚上人在我身上,可心早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我轻蔑地一笑,即刻打消了向她说明的念头。“笑话!”我说,“我早就说过了,你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
“你别打马虎!”她神色严肃地说,“我也早跟你说过,咱们不要惹事,不要生非,你偏不听,要去打死!有多少人就是为了写日记给送进劳改队的,你还不知道?那种罪你还没受够?”
“没受够!”我死皮赖脸地说。
“那也行,”她说,“只要你忘记我过去的事,要死,我也陪你去死!”
一瞬间,我觉得我动了感情。这是一出从久远一直到现代反复演出的故事。是不是干脆告诉她我想干什么,我在干什么?但她是那样的女人吗?我下意识地斜睨了她一眼:漂亮、肉感而又愚蠢。她随时都会引起曹学义这样的男人的兴趣,被人诱惑。我脑海中又浮上来一个人影,一个写过歌颂爱情的诗的小学教员。他跟我一起以“反革命言论”罪劳改过三年,而检举他的正是他妻子。我撇了撇嘴,说:
“算了吧,哪有那么严重?老实说,我只是怕把过去学的东西忘了,才写些乱七八糟的话……”
“你不是说过去的东西你是忘不了的吗?”她脸上掠过一丝尖刻的笑意,但倏忽之间又消失了,露出白白的牙齿,咄咄逼人地说,“乱七八糟的话!反正你写的东西你知道!你哪一个字不是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宋江对着干的?!好歹我还上过中学哩!还有,我给你买个收音机,是让你听个戏解闷的,可你每天晚上戴上耳面,跟个特务一样,你这是干啥?……”
“好了好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我慌忙阻止她大声的嚷嚷,朝炕上一躺,表示休战。
“那你想干啥?那你想干啥?……”她拧过身子,盯着我追问。说着,她的眼睛湿润了。但她噙着泪,没让它流出来。
我想离开你!不但离开你,并且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我没有说,两眼凝视着窗外。那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高高的灰色的天空中,有什么东西使我心动。窗外有一只麻雀啁啾地在寒风中飞过。这间屋子是温暖的,可是我情愿跟它易地而处。
“我还以为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你讲道理,你不狗肚鸡肠。”她坐在炕沿上絮聒,“我告诉你,多少次在你睡着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你、摸你、亲你……可结果你还是跟没知识的男人一样!你现在好了,你现在是人了,我就那么一次,你就老抓着我不放,老拿捏我。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你干的这些事。只要我向上面透出一个字,你章永璘就不是章永璘了!哼,你当我是傻子?你当我不知道你这些日子在打啥鬼主意?你当我是那么容易甩掉的?……不信,你就试试!”
她的絮絮叨叨又使我动情,又使我气愤。我不愿意看她,但她非盯着我的脸不可。她温顺的时候是只小猫,躺在你怀里任你怎样摸她、揉她,而寻衅的时候又是只蟋蟀,一定要面对面、头对头地斗个你死我活。她的眼睛阴沉而坚决,可是腮上又蜿蜒而下软弱的泪水。对了,这就是她!啊,爱情,那些冗长的小说中重复过无数次的字眼,从来没有从她嘴里说出过。然而这就是她的爱情,爱得野蛮而专横。爱情,真是既让人眷恋又让人讨厌的东西。没有它不行,它太多了也受不了!
“哼!”我冷冷一笑,“‘就那么一次’!要杀人的话,就那么一刀就行了。你那一次就把我的心伤透了,怎么也转不过来。你还想去告发我,我看你敢!你只要向别人透出一个字,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你看我敢不敢!”她说。
她的眼睛里有一丝游移,一丝慌乱,她不知道现在怎么挽回局面,但又不甘示弱。她在我眼睛里看到了冷峻,但没有看出冷峻的原因。她不理解我;她只把我看她的一部分,因而她连她自己也不理解了。
“你只要再提我过去的事,你看我敢不敢?”她又重复说。
“真没水平!”我说,“我这件事跟你那件事根本是两码事!怎么?你还想拿这件事来拿捏我吗?”
“哎!我就是要拿捏你!”她忽然又理直气壮地耍开了无赖。“你想咋样?你当我是那么容易甩掉的吗?”
“我本来不想甩掉你,可你竟然说出这种话,就是没有这样做,我也非甩掉你不可了!你心里明白:你要告发我的想法,是你心里早就有的!”我在炕上架起二郎腿,同时掏出一根烟。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离开她的借口了,我想。
她的面孔突然气得发白,身子在炕沿上扭了几下,最后下了决心,猛地象猫似地跳起来。我以为她要过来扑我,而她却向那门板做的书桌扑去,一把抓起我的笔记本抱在胸前。
我欠起身,手指点着她:“你不用抱得那么紧,没人抢你的!”说完,我又躺下了,点着了烟,把火柴扔到门口,顺势指着门说:
“我看你往外迈一步,只要一步!”
我知道她不会那样做,但我却希望她那样做。我需要她反常的行为来安抚我的良心,坚定我的决心。在想离开一个人的时候,最好是先让那个人做出伤害你的事情。
她踌躇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又指了指门口:
“你敢!我看你走出一步!”
“那你还提不提我过去的事了?”她问。
“为什么不提?我已经说了,我的事跟你的事完全是两回事!”
她的脸猝然变得难以辨认,变得陌生起来,这是一张失去理智的脸。她真的抱着日记本朝门口奔去,同时发出嘤嘤的哭声。我坐起来,扔掉烟,谛听她的动静。她跑到外屋便停下了,趴在餐桌上嚎啕大哭;那一只花瓶叮叮噹噹地作响。裂痕已经造成了,是弥合它,还是继续加深?我站在裂痕的边缘,向下一看。头晕目眩,但裂痕深处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我只有投身进去才能冲出这个世界,到一个新的天地里,或是再次投入我熟悉的地狱。于是我装作慌张的样子,从炕上跳下来,两步跨到外屋,做出要去抢那个日记本的架势。
她本来是到此为止的。我没有估计错:她见我冲出来,却即刻跳起来又抱着笔记本要去拉开外屋的门,似乎要拿着这个“罪证”跑去告发,我一把拽住她,她更加使劲地在我怀里挣扎。那曾经激起我情欲的柔软的肉体,此刻陡然变得僵硬起来。蛮横起来,变得充满敌意,变得可厌而又可怕。我想夺下那个日记本;她两手死死地搂着不放。我们俩拉来扯去。戏演到这里,剧本突然中断了,演员不知应该怎样演下去,只好凭自己的本能进入角色,把假戏真做起来。
正在这时,门被推开了,黑子一闪身进到屋里。我们猝不及防,脸然僵持着。他一眼就看明白了我们争夺的是什么。他掰着她的手喝道:
“你放开!黄香久,有话好说嘛!……”
她把日记本往我怀里一塞,哭着跑进里屋。黑子朝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把笔记本揣进棉袄口袋,调整好呼吸,跟黑子走到外面。冬天的风在显示自己的威力,大声呼啸着,把荒滩上的枯草刮进小村庄,又把小村庄的垃圾刮到田野上。村庄外的土路,奔跑着浓密的黄尘,一阵一阵的,扑向光秃秃的树林。
我们两人找了一处背风的角落,并排蹲下,背着风把各自的烟点着。吸了几口。黑子眯着眼睛说:
“我可啥也没看见,啥也不知道;我也不问你这本子里写的是啥。”他思忖了一下,啐了一口唾沫。“可是,这样的事情我可经过,那他妈的还是我当红卫兵的时候,在北京街道上,X他妈!有个臭娘儿们就把她男人的啥笔记本交到我手上。我他妈那时候也傻,向上头照转不误。到头来男的给判了刑,臭娘儿们弄到了离婚证……我说,老章,女人懒点、馋点都没关系,可千万别他妈当‘克格勃’!你想想,你每天晚上搂着个定时炸弹睡觉,那多恶心!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女人欠打!也跟你说了:这臭娘儿们跟那‘丫亭’有交情。那时候我看你窝囊,就觉着你准有把柄抓在她手上。原来是这个玩意儿!老章,这可是不得了的事!这臭娘儿们你还能要哇!不定啥时候就把你送进去。你呀,得变着方儿甩掉她……”
村庄的路上空荡荡的,好象连人也被风刮跑了。我没有吸几口烟,但烟在风中燃烧了一半。有谁能理解我复杂的感情?神经不能象电线那样接通,感觉不能传导给别人,因此,当事人的事,在别的任何人看来都十分简单。
“谢谢你!”我说,“你可帮了我的忙。不然,我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结果。至于她嘛……”
会有什么结果?我明明知道她胡闹一阵也就完了。女人的脾气是一条流到沙漠中的河,开始时汹涌澎湃,流到后来就会无影无踪。我气忿地扔了带煤焦油味的香烟,它在风中不能自主地滚得很远。
“啊!”黑子突然颤了一下,说,“妈的,让她一搅和,我差点忘了!我跑来是要告诉你,下午你出工的时候,大喇叭里广播的:周总理逝世了!”
“啊?”我看着他的脸,一时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太快了!
我推开门,顺手拿起门背后的铁锹,把门牢牢地顶住。随后走到煤炉旁边,掀起炉盖。炉中的煤劈啪作响,火焰通红。这是一只独眼龙的眼睛。我从棉袄口袋里掏出日记本,扯掉塑料封面,一叠一叠地把内页撕下来,塞进这只毒眼里:你看吧!你检查吧!……
纸张吐出淡红的火焰,然后发黑,然后发白。灰烬落在燃烧的煤块上,还一闪一闪地放光。好象是它化成了能呼吸的精灵。它是有生命的东西,它是我的心血,它是我大脑中的化合物。现在;它躺在炉火中,还在不安宁地辗转反侧。烧掉就烧掉吧,你那上面的符号,已经永远记在我脑海中了。不管我是浪迹天涯,还是在铁窗之下。我都会记得你,就象人总能认出自己的孩子。而必将有一天,我要把你向人民公开出来。“冬天很快就会过去,而春天是不会再来了。”不!春天是会来的。
她还在里屋,听不见她的动静,但过了一会儿,也许她闻着了烧纸的烟味,她一掀白布门帘跨了出来。
“你这是干啥?”她浑身震颤了一下,扑过来抢我手中还剩下的一点残页。
我抬起手臂格开她。“你要干什么?”我说,“还想拿去立功吗?”
她睁大着眼睛,仿佛很陌生地瞪了我一眼,随即颓然地跌在凳子上:
“我跟你说,章永璘,你不得好死的!你亏了心了,你当我是真会那么干吗?我也是人呀!……”
她两手的手指痛苦地拧绞着,嘴唇悲愤地往两边撇,红红的眼睛呆呆地瞅着火苗,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
我知道你不会那样做,便是我却非要这样做不可。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爱你。我必须伤害你,伤害到使你能完全忘记我的程度!
“完了!”我把最后一叠日记本塞进火炉,说,“我们两个也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