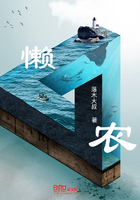“什么?区区一个江州刺史的公子就敢这么嚣张跋扈,简直欺人太甚,欺我们钟家无人吗?”
老太太,秦氏,李氏俱都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江宁钟氏一族,自先祖创业以来,风风雨雨,到如今已经立族二百余年。
至一百年前,钟氏凭借积累的巨额财富,建立江宁城里第一家族学,并先后聘请名师大儒讲学。
族中优秀子弟更是层出不穷,这百年间先后出了五十位贡生,二十六位举人,十个进士,八人入翰林,享有“德积一门十进士,恩荣三世八翰林”的美誉。
陆陆续续有五十多人出外做官,将钟氏一族的名声散步到南北各地。
据历代族谱记载各地为钟氏官员去官时立祠的就多达十几个,由此可见钟氏的名望。
更不用说如今钟家的领军人钟景贤,更是官居吏部侍郎,掌官吏升迁罢黜,地方官员那个不敬?
钟氏子弟竟然被人当街殴打,如此欺辱行径,这可真是近几十年来头一遭。
“哼!拿府里的帖子,让官府拿人…”
老太太目光冷凝如刀,面沉似水,厉声喝道。
“只怕是不行~”
苏氏捏起丝帕掩唇,轻咳了一下,淡淡的说道。
“为什么不行?大嫂,你这话什么意思?”
秦氏眼珠子都红了,几乎暴跳如雷,瞪着苏氏质问道。
苏氏轻“嗤”一声,身子往后一靠,别过脸去,看着同样不满之色的老太太淡淡的说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新任江州刺史是王炳全….”
“那又如何?不过是个四品下的官,和大哥四品上差了一级不说,升迁罢黜也皆在大哥一念之间。”
秦氏原以为苏氏能说出什么了正儿八经的理由,没想到只是说一个名字。
她不以为然的撇着嘴,满脸厉色的说道。
“是呀!他家是刺史又如何?我们钟家也不是好惹的,不行,就给大哥休书一封,看谁斗得过谁?”
李氏也坐不住了,抓紧了丝帕,咬着牙喝道。
“好了~”
老太太皱着眉瞪了她们一眼,转头沉着脸,盯着苏氏不耐烦的问道:
“你说,接着往下说~”
老大媳妇虽然不讨喜,但她从来不作妄语。
她既然这样说,就必然就道理在。
苏氏见状,也不再拿乔,坐直了身体,神情一凛道:
“是,老太太。刚才两位弟妹说的也的确不错,他是不怎么样。可他妹妹去年刚被封了贵妃,深受陛下的恩宠。”
“......”
屋内一片寂静,隐隐响起了抽冷气的声音。
“是王..贵妃。”
老太太张了张嘴,拧着苍眉,脸色阴沉的能滴下水来。
这可麻烦了。
新晋的王贵妃,据说一入宫就惊动了圣上,被圣上赞为天人。
一时宠冠六宫,时时赏赐,年年晋升,从最初的才人一路晋升至贵妃娘娘。
这等恩宠,就说就连当年的孙皇后也比不上。
现在只怕不是自己追不追究的事,而是对方愿不愿意放手。
秦氏一听也是脸色大变,拧着眉头,砸吧着嘴唇道:
“这…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是….”
“老太太?”
李氏心里也提了起来,抓紧了丝帕,上前一步满眼期盼的望着老太太。
“那两个孽障好端端的,怎么会惹上这个花花太岁?”
老太太皱着眉,抓紧了念珠,神色阴郁的叱道。
“老太太,小的们也不知道呀!那公子哥就使人问了一下两位少爷的名字之后,当时就喝令打人…”
几人目光同时盯住地上跪着的长安,长安身子一颤,苦着脸叫屈道。
“无缘无故就打人?这也太欺负人。他姑母就是真的贵妃娘娘,也不能这么嚣张跋扈吧?”
秦氏不忿的啐了一口,咬着牙怒道。
“老太太,容少爷的跟班李贵回来了,说有要事禀告!”
正在这时,门口的丫鬟撩起帘子,进来躬身禀告道。
“快让他进来~”
李贵帽带歪斜,口鼻青紫,脸颊肿张,比长安还惨。
一进来就跪在长安身边,朝上扣头道:
“老太太,诸位夫人,不好了,两位少爷被知府大人捉了,要带回衙门。”
“什么?这吴知府疯了吧?他想干什么?…”
秦氏立时跳着脚骂起来。李氏也是一脸怒容,愤慨的瞪着李贵。
“老三呢?快叫老三,让他赶紧去衙门找吴知府。”
老太太抓紧了念珠,瞪着骇人的目光,厉声喝道。
李氏神色慌乱的屈膝一行礼,急忙退了下去。
“你们俩个老老实实给我说,那两个孽障到底做了何事触怒了那花花太岁?那吴知府以什么罪名拿的人?”
底下的长安和李贵对视一眼,脸颊一抽搐。
老太太慧眼如炬,登时就知道这里面有猫腻。
当即眼一瞪,阴恻恻冷笑两声,看着他们俩人的目光仿佛啐了毒的刀子。
“老太太,冤枉呀!两位少爷什么都没做呀!
都是那花花太岁欺人太甚。
更无耻的是,他见官差来了之后,当即就拔出自己的刀子当着满大街人的面硬塞到宽少爷手里。
然后指责宽少爷当街对他行凶,要求官差拿人…这简直…就是欺负人呀!…呜呜..”
李贵脸红脖子粗,神情悲愤的叫道。
“……”
屋内众人听得都惊呆了。
什么叫仗势欺人,这就是。
什么叫无耻之尤,这就是。
苏氏也觉得天雷滚滚,这么嚣张的儿子,他母亲是怎么养出来的?
……
城北渣子胡同,经过木根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院子里的气氛顿时欢快起来。
一番收拾之后,家里凌乱的景象不复存在。
窗户上也贴上新纸,桌椅板凳也被木老爹修补的七七八八。
床帐被褥也换上了新的,屋内屋外不时响起笑声。
钟子铭坐在书案前,第一次觉得心里既平和又温馨。
他花费了半小时,花了两张草图,准备以后的生计。
其中一张单纯就是一块圆形的铁板,毫无技术可言,那是他用来做山东杂粮煎饼的。
另外一张则是铜制的老北京鸳鸯火锅,烧木炭的。他觉得应该非常适合这个季节。
木根一家来到这里后表面上欢喜,其实心里是很惶恐的,他看得出来。
他必须找到稳定生计的办法,以安稳人心。
煎饼和火锅就是他目前想到的法子,当然也是他自己馋了。
他那天带着念夏去胡同口,吃白汤杂碎时心里就在想若是能吃上一顿火锅就美了。
“少爷,我回来了,药已经抓来了,你看!”
他正思索着,念夏的声音从身后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