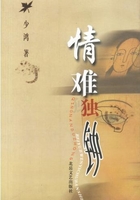卷一
在未尔必北方的广大田野上,有个男人跟在犁后一上一下往复来回地犁着田。他是个高大的男人,具有年轻人的体态,身上穿戴着绽补累累的麻袋布罩衫、红色的绒线腕套,和一双笨重的威灵顿长统靴。靴上有个圈环,一直拉到他的裤管上蓬鼓如袋的膝头。他戴着一顶褪了色的海狸皮帽,阔大的帽边下,他的长发下垂于衣领,头发由于日晒雨淋,已呈灰白;一大把浅淡轻飘的胡子飘拂于他的胸前,还不时地被吹扬到他的肩膀上。他有一张瘦瘦的脸、饱满拱起的前额,和一双明亮而温和的大眼睛。
他头顶约几码高的地方,有一群罗伊斯顿乌鸦在那儿盘旋飞翔;不时会有一只——随后又有另一只——猝然飞降于他身后新犁开的犁沟上寻觅啄食,只有在他抽拉缰绳催促他那迟缓笨拙的马快点往前拉时,它们才在旁边回避地跳开几步以避一下。
这个人是未尔必和斯奇倍莱的教区牧师。他记得他的教区居民称呼他为伊曼纽;而地方上一些较不友善的同僚们则恶意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现代使徒”。
尽管他的衣着如此,头发、胡须也未加修钸,但是不难看出他不仅是个农夫而已。与农夫相比,他的身体显得太过文弱,双肩太过倾斜,不像个干粗活儿的。他的手的确操劳得红紫、肿胀,但也不像那种自小就下田做工的手,显得粗大而突出。他脸孔的肤色也不像一般农夫那样,呈现着千篇一律、皮革般的黝黑色;而是长有雀斑,具有表情的。
这是三月初的一个阴寒、冷清的清晨。一团团的雾气,不时地被阵阵的西风吹逐到地面上。有时平原会为一团浓密的灰雾所笼罩,在这块田地上看不到另一块田地;顷刻,那风又会把雾气吹走,只留下圈圈薄薄的雾气氤氲回旋于那些犁沟上面。偶有一二道苍白的日光缓缓地穿透过乌云,在那些田地上闪耀。
阳光照射的当儿,从那位居高处的牧师属m那里,人们可以看出整个教区的轮廓来,教区朝着远处菲尔德河边那座教堂延伸过来;在雾气里,那座教堂看起来就像个苍白的鬼魂似的。稍为近一点的地方,介于两座山之间,可以隐约窥见水沫泞湿的菲尔德河本身。西边是斯奇倍莱的三座山,山脊上——个亮亮的红点显明了新建的会议厅的瓦顶山形墙。
伊曼纽太过于全神贯注在他自己的思想里,并没注意到周遭景象的移易变化。甚至在他停一下步让他的马喘口气时,他的视线漫无目标地瞥着,也是视而不见的。他践踩、行走于这些起伏不平的山地上已有七年的岁月;这里的事事物物在他看来都已顺眼悦目了,纵使耀眼的阳光消匿,阵雨倾盆而下,他也不会注意到它的变化不定的。将近中午的时候,他在沉思中为一阵声音所惊醒——那是循着田间路径朝他趋近过来的一小伙人所发出来的。
最先出现的是一个体格壮壮的小女孩,年约四或五岁,她用一条跨过她肩膀的绳子,拖拉着一辆放有一个婴儿的老式篮车,由于轮子深陷泥中她得用力在前拖拉,因而她的兜帽滑离了她那被风吹扬起来的头发,每隔一会儿她不得不把绳子放开一下,以便拉起她那不断地在她的木靴上掉落的红袜子。后面还有一个小孩子在推那篮车,是个小男孩,他戴着一顶毛绒编织的帽子,两边的帽缘紧紧地在下系结,盖住他的双耳,并有一团棉絮塞在一边的帽缘里,掩住了他的半个脸颊。
殿后的是一个身材亭亭的年轻妇人。她稍微落在另外那几个人的后面,在那条路的边边上走着;头上有一条花围巾,围巾的缘角随风飘扬;她一边在前走,一边嘴里哼着,有时她大声地唱出来,眼睛却抬也不抬,只顾着手里的编织。她的一双手是褐色的。
那是汉姗和她的三个孩子——伊曼纽的整个家族。那个小小的旅行队伍快要抵达伊曼纽正在耕耘的田地边端时,那两个孩子松手放开了那辆篮车,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父亲,而这时他正从田地的另一头朝他们这边犁过来。由于寒冷,他们的脸给冻成紫蓝色,鼻子垂着鼻涕。他们坐在那儿,脚穿的是磨损破旧的木靴,身着的是绽补过的衣服,这光景看起来和别的村子里衣衫褴褛的小流浪汉们并没两样。住在宏伟的牧师公馆里的人家当然不会是这副样子的:他们所住的公馆的红色屋顶和两旁植有白杨的路径,是高出农家的石板瓦的屋顶上的。
伊曼纽从老远的地方快活地朝他们挥舞他的帽子,等走到了那陇脊的尽头处他拉住了那冒着热气的马匹,喊叫说:
“有没有什么事情,汉姗?”
汉姗依然站在路边,用她的一只脚把那篮车一下子前一下子后地推来推去——篮里的小婴儿由于车子停下来而显得不安静。
她径自数她手中编织物的针数,然后以她那单纯的农家妇女的腔调回答说:
“没有,我没听到什么……啊,对了,那个织工来找你,他说他有事要跟你谈。”
“当然啦,”伊曼纽说,心不在焉地回头望那一片田地,看看自己把田犁得怎么样了。
“他打算怎么样呢?”
“噢,他没详细说。我是来告诉你三点钟时要去参加教区会议的集会的。”
“那么我想大概是有关贫穷救济的事。”他打断了他妻子的话,“也可能是关于教区委员会的事。他什么都没提起吗?”
“没有,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坐下来朝四周张望了一下,然后就走了。”
“噢,是啦,他是个古怪的家伙……喂,汉姗!”他中断了原先的话,换了种不同的声音,“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农耕报》上读到一种新的施肥方法,读后我曾跟你谈起的。这个新方法我越想就越觉得喜欢它。在肥料新鲜的时候就把它们施撒到田里,并立刻犁翻到泥土里去,比起把它们一堆一堆地堆积起来,让那滋肥的功能蒸发掉,而且一直使空气恶浊难闻,岂不是更合乎自然之道。你不觉得吗?你还记得不?照报纸上说,用旧的施肥法那些土地每年约损失三百万的收入。我想不通为什么以前没有一个人来想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相信这些粪堆纯然是农奴制度的产物。农夫们在照料他们的事务之前,必须随时准备侍候他们的主人,所以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工作一天又一天地往后挪延,并把那些粪便废物一堆又一堆地堆积在那里,直到他们能抽出个空当才把那堆肥加以清理一番。这样堆积废物的缘由慢慢地被遗忘了,于是农人们竟然认为堆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总之,这些发恶臭的一堆堆废物,跟今天那许许多多,我们正要设法从其中解放出来的腐败事物一样,都是农奴制度的遗迹。啊——汉姗,这是个要我们生活的光辉灿烂的时代!做一名教导文明的见证者,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方面的皆然,并且眼见那使人觉醒的真理与正义的思想,怎样一步步地解除奴役的羁绊束缚,而使人类能够进入更光辉更幸福的时代!”
汉姗抽移了一根织针,一面报以她丈夫一个心不在焉的微笑。她知道现今的一切新思想多么容易激起伊曼纽的热情,她早已习惯于静静地听他说明他所期待的那些伟大远景。以一种道地的农夫样子,他取出一个大银色手表来,先拿近耳边听了听,然后看了看时间,“好了,该是把马轭犁具卸下的时候了。”他说。
“雷谛啊,你能不能过来帮爸爸一下忙!”
那男孩子仍然挨着他妹妹身边坐在那块石头上。他正出神地注视着那些在不远处那块刚犁过的田地上,忽而飞起忽而掠下的乌鸦,并没听到他父亲的叫声。他动也不动地坐着,覆着棉絮那只耳朵支靠在他的一只手上,脸上露着庄重的表情——孩子们想起过去的种种苦难遭遇时,脸上常可见到的表情。
以他的年龄来说他是稍微小了一点,虽然大一岁,比起他的妹妹,他的体格却显得纤弱些。他妹妹的四肢强劲有力,脸颊光润,双眼具有乡间孩子特有的那种灵活神色。他是伊曼纽的影像。他具有同样高的、蕴含智慧的前额,以及同样温文的神情;他也继承了伊曼纽的柔软、卷曲加波浪的褐色头发,以及大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双眼睛在阳光下几乎是澄澈无色的。
“孩子呀,你没听到吗?父亲在叫你呢,”那男孩子没动静,汉姗就说。
听到他母亲呼唤的声音,他把他的手移开了他的耳朵,脸上勉为其难地想要露出个小小的微笑;他这种模样引起了她的注意。
“我的孩子,你的耳朵还会疼吗?”她小心地问。
“不,一点都不痛了,”他急急地说。“现在我一点都不觉得怎样了。”
“喂,雷谛,你来不来呀?”伊曼纽从田里那边再次地叫喊。
那小男孩立刻站起来,以整齐的步伐跨越那一条条的犁沟,走到拖犁的马匹那里,开始给它们解下挽缰来——就像个马车夫那般的郑重其事,尽忠职守。
这个孩子是伊曼纽的心肝宝贝,村子里引以为傲的宠儿: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有个不像农家子弟的外观,另外则是由于他的性情极端的好。他是以汉姗父亲的名字安得士?哲根命名的,但是在家在村子里人家也叫他“雷谛”——他诞生时伊曼纽给他取的一个名字,大家从前很喜欢叫他这个名字,所以受洗时所取的名字反倒给忘了。
看到了那覆在他耳朵上的棉絮,伊曼纽呼叫道:
“喂喂,那是怎么回事?孩子,你耳朵的毛病又发作了?”
“是的,有一点。”那男孩温柔地回答,像是害羞似的。
“那只耳朵很讨厌,但是并不怎么严重,是不是?”
“是不严重,现在全好了。我都不觉得怎样了。”
“孩子,那好;你要做一个勇敢的少年人,不要为一些芝麻小事在那儿大惊小怪。你知道,弱者在这世界上是不好过日子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知道。”
“那么,你要记住,今天下午我们必须赶到磨坊那边去。我们俩没时间生病。”
汉姗的织针抽换的比原先更快,当父子俩停止谈话时,她说:
“伊曼纽,我想雷谛今天最好待在家里休息。整个早上他并不怎么好。”
“对啦,但是呀!你听到他刚才说现在全好了。而且我相信新鲜的空气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一如古老的格言所说,清新的空气是全能上帝的良药……雷谛一直都抑郁不乐地闷在家里,这样使得他的脸色会更为苍白。事情不外乎是这样!”
“伊曼纽,我还是认为要是我们对他小心一点的话事情会好一点。我真希望你打定主意去跟医生谈谈雷谛。他的耳朵有这种毛病已经快两年了,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
伊曼纽并没立刻回答。这是个过去他们常讨论的话题。
“嗯,当然啦,汉姗……要是你果真希望这样,我当然是不会想要反对的。但是你知道,我是不怎么相信医生治病这种事的,而且你也知道我对哈辛大夫的印象怎么样。再说,耳痛是小孩子常有的事,只要你给予时间、让它休息,让自然去治疗,那毛病会自行痊愈的。你母亲也是这么说的,她的话是多年的经验之谈。孩子,拉住那条缰绳。每次人们生一点小病,马上就要请医生来治疗以使他们复原,有必要这样吗?我绝不相信全能的上帝会把人创造得这么不完美。马仁?奈连在思材因岛上从老格瑞特那拿的那种药油,我们又拿到了一些。以前那油对孩子的耳病有效。不管怎么样,等到有什么真正的不对劲时再说吧,我们不要为一点伤风感冒而大惊小怪、寝食难安好不好?好了,小家伙,过来这边。”说最后这几句话时,他双手挟握那孩子腋下的部位,把他放在较靠近的那匹马背上。
汉姗默然不做声。在这些有关孩子问题的小争执中说最后的话、占上风的总是伊曼纽。除了他的理由充足、意见繁多之外,她觉得他太能言善辩,又很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即使她并不同意他的见解,在他的滔滔雄辩之下她经常是陷于默然无语的。
在那一小队人马拖拖拉拉地回村子里去的时候,那一团团柔如羊毛的雾气重新又弥漫于那一片田地上了。
小男孩骑着马连同另外的马匹走在前面,伊曼纽和那小篮车跟随于后,他一手推拉着那辆小车,而肩上驮着他的女儿希果丽。她的小名叫甜饼。她拿下了他的帽子挥来舞去,欢愉地小声逗弄那个婴孩,而那婴孩也从篮车里咿咿呀呀地回应着她。
汉姗稍隔着一段距离走在后面,手里继续打她的毛线。
她保持着同她少女时代一样美好的亭亭身材,并且踏着同样坚定、整齐规律的步伐向前走。但是她肤色黝褐的脸上,多少有了些沧桑变化,甚至是变得喜好沉思、反省,有一点郁郁然的。自然地,她七年的婚姻生活和养育三个孩不会丝毫不影响她昔日的年轻美丽的。她的双颊显得瘦了,她神色庄重的双眼甚至显得更为深陷了。但是她依然是个非比寻常的漂亮妇人;而且照种田人家的标准,她是带着不平常的美好名声度过她的二十五年青春年华的,所以在斯奇倍莱,她生长之地,人们十分地以她为荣,当然是不足为奇的事。是有几个人不喜欢她的谨慎、冷漠——他们认为那是骄傲——而对于伊曼纽在聚会的公众场所里找对象时竟然选择了她,暗中感到深深的惋惜。
伊曼纽和他的孩子走进牧师公馆的拱形大门时,农场工人尼尔思正坐在抽水帮浦下的大水槽边缘上,忙着阅读摊在他膝上的报纸——《人民新闻报》。他是个黑发的汉子,年约二十左右,中等身高,有着方方宽宽的肩背,朝天鼻子,红润的脸颊,以及初长成的胡须。
在阿奇迪康?田内绅时代,那个大庭院总是井然有序,一片宁静安详的,这情景和它是附属于教堂的场所这一点是相称的,而现在看起来它和其他农家的庭院没有什么两样了。各式各样的器具和一束束的干草乱糟糟地丢在地面上。几扇门都敞开着,牲口嗯坶地鸣叫,等候着它们中午那顿干草,凡此种种都可看出工作之繁重急迫。在那不平坦的铺道上到处撒着腌青鱼用的盐汁,用来咸死铺道上的杂草,而酿酒房外面有几只鸡在一堆厨房的器物上挖寻它们的食物。
“尼尔思,你那么专心一意地到底在读什么啊?报上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吗?”伊曼纽边问,边放下希果丽,同时把雷谛从马背上抱下来。
那个人放下报纸抬起头来望他,以一个大大的咧嘴笑容来回报问话。
“噢,哲学家先生!你又在打仗了吗?那么,今天你的矛头又指向谁了呢?好了,尼尔思,让我瞧一眼吧!”他说,一面把马具从马身上卸下来。
那个人移动了一下把报纸递伸过来,于是伊曼纽便开始阅读,而那小男孩这时把马带到大水槽那里让它们喝水。
“你写的东西在哪里?噢,在这里!《中学与道德责任》。说的是,说的是,开头写得不赖……真是棒极了……说得好,的确!那些话你说得对。啊,尼尔思,你可不是个懦夫呢!”
那个人坐在水槽边角上,眼睛注意着他主人脸上的表情变化,而每当伊曼纽表示同意地点点头或发出赞许的呼叫时,他那几乎陷埋在面颊里的、一双小小的黑眼睛就发亮起来。
“这篇大作会让你名声响亮,”最后伊曼纽说,笑着把报纸递还给他。“你一步步地使自己成为一名作家了。很好,很好,只是朋友啊,可别让你自己溺死在墨水瓶里喔。你要舞文弄墨,墨水有时候是危险的毒药呢。”
他的话被汉姗的叫声打断了,她经由花园的小径走过来,这时站在石阶上,叫他们进去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