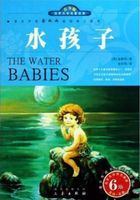“这会儿该付账了,”那人紧接着说,“我的账是多少?”
他望了一眼那张账单,不禁一惊。
“23个法郎!”
他看着那店婆又重复了一遍:
“23个法郎?”
这两句话的声调,可以辨出惊叹号和疑问句的区别。
德纳第夫人对这一质问早有准备。她沉沉稳稳地回答:
“啊!圣母!是这样,先生,是23个法郎。”
那外来客人把五枚各值5法郎的钱放在桌上。
“请把那小姑娘领来。”
正在这时,德纳第出现在厅堂的中央。
“先生付26个苏就行了。”
“26个苏?”那妇人喊起来。
“房间20个苏,”德纳第冷冰冰地接着说,“晚餐6个苏。至于小姑娘的问题,我得和这位先生谈几句。你去吧,我的娘子。”
德纳第夫人的心头一亮。她觉得那里仿佛有灵光在闪动。她明白,主角登场了。她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厅堂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德纳第给客人搬了一把椅子。客人坐下,德纳第站着,他脸上显出一种天真而淳朴的怪诞神情。
“是这样的,先生,我来向您说明:那孩子,我喜爱她。”他说。
那陌生人盯着他说:
“哪个孩子?”
德纳第接着说:
“真是滑稽!谁会喜欢这几个钱?这几枚值100个苏的钱,您请收回吧。我所喜爱的是这个女孩子。”
“哪个女孩子?”那陌生人问。
“啊,我们的这个小珂赛特嘛!您不是要把她带走吗?可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不能同意。这是真话,它真得就像您是一位正人君子!我们离不开她。我是看着她长大的。我们为她花了许多钱,那是真的。她有许多毛病,那也不假。我们不是有钱人,那也千真万确。她常生病,看一次病我们就得付400法郎的药钱,那也是事实,人总得替慈悲的上帝做点好事嘛。这孩子既没有爹,也没有妈,我把她养大了。我赚钱买面包,填饱她和我们一家四口的肚子。的的确确,我舍不了这孩子,您明白吗,彼此有了感情。我是一个傻好人,我;我爱她,这孩子,我也不晓得什么道理;我女人性子躁,可她也爱她。您看到了,她好像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我需要她待在我家里,叽叽喳喳,有说有笑。”
那陌生人一直用眼睛盯着他。他接着说:
“对不起,请原谅,先生,不见得有人肯把自己的孩子就这个样子送给一个过路人吧?我说得不错吧?再说,您有钱,也很像是个诚实人,我不晓得这对她是不是有好处,因此,总得搞搞清楚吧!您懂吗?如果我让她走,割爱牺牲,我得知道她去了哪里,我不愿她一走就永远见不到她,我希望能知道她在谁的家里,好时不时地去看看她,好让她晓得她的好爸爸还在想着她、监管着她。总而言之,有些事是不能办的。我连您的姓名还不知道呢。您带着她走了,我说:‘好,百灵鸟呢?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至少也总得先见到一张令人讨厌的破旧纸片,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什么的吧?”
那陌生人一直都用一种似乎能看透他的心底的目光望着他。这时,又用一种坚定沉稳的口吻对他说:
“德纳第先生,从巴黎来这里,才5法里的距离,不会有人带身份证的。我打算带走珂赛特,我就一定带她走。事情就是这样。我不会让您知道我的姓名,不会让您知道我的住址,也不会让您知道她将来住在何处。我的意思是说,您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剪断了拴在她脚上的这根绳子,让她远走高飞。这合您的意吗?行,还是不行?”
有时,魔鬼和妖怪会从某些迹象上看出有个比他们法力更大的神出现在他们面前。眼下,德纳第就遇到了这种情形。他认识到,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对手。这是他的直觉,同时也是靠他的机敏和精明得出的结论。表面看昨夜他一直在陪着车夫们喝酒、抽烟、唱黄色小调,可他的心思却一直用在了这个客人身上。他没有一刻不在像猫那样注视着他,没有一刻不像数学家琢磨数字那样算计着他。他这样做,是为了弄清楚一个“究竟”,同时,也是出于兴趣和本能,就像有人出钱要他这样做似的。那个穿黄大衣的人的一举一动,都没有躲过他那双敏锐的眼睛。即使是在那个身份不明的人还没有对珂赛特那样明显表示关切的时候,德纳第就已看破了这一点。他早已察觉到,那老年人的深沉的目光总是投在那孩子身上。为什么对她如此关切?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他腰缠万贯,穿得却如此寒酸?他向自己提出了这些问题,却没有答案。这使他感到愤懑。他对这些问题揣摩了整整一夜。他不可能是珂赛特的父亲。难道是祖父一辈的吗?如果是那样,又为什么不立即说明自己的身份呢?当人有某种权利的时候,总是要表现出来的。显然,这人对珂赛特是没有什么权利可言的。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德纳第沉迷在种种假设之中。他感到了一切,但却什么也还没有看透。不管怎样说,在和那人谈话的过程中,他深信其中有一种秘密,并深信此人不敢揭示这种秘密,从而觉得自己是强的一方。可是当他听了这陌生人的那种干脆而坚定的回答、看到这神秘的人物竟神秘到如此简单的时候,便又感到自己实际是弱的一方。这是他以往从未遇到过的。他的判断出了毛病。于是,他汇集了自己的全部主意,在一瞬间他就权衡了这一切。德纳第原本就是那样一个能一眼便可看清形势的人。他估计,单刀直入的时刻到了。他正像那些独具慧眼当机立断的伟大将领一样,在这关系成败的紧要时刻,突然揭开了他的底牌。
“先生,我非得到1500法郎不可。”他说。
陌生人听完,从他衣服侧面的一只口袋里取出了一个黑色的旧的皮钱包,打开后,取出三张钞票,把它们放在桌上。接着,他把大拇指压在钞票上,对那店主人说:
“去把珂赛特找来。”
发生这些事时,珂赛特在干什么呢?
珂赛特早晨一睁眼,便跑去找她的木鞋。她在鞋里发现了那枚金币。那不是一个拿破仑,而是王朝复辟时期的那种全新的、面值为20金法郎的硬币。币面上,一条普鲁士的小尾巴替代了原来的桂冠。珂赛特看花了眼。她乐得不得了,感到自己转了运。她不知道金币是什么?她还不曾见过。她飞快地把它藏到了自己的衣袋里,好像它是偷来的。她同时觉得,这金币是属于她的,也猜到了这礼物来自何处。她快乐,然而,这快乐之中又充满了恐怖。她感到满足,而又感到特别惊恐。在她眼里,东西到了如此富丽、如此漂亮的程度,好像都不是真实的。那娃娃让她害怕,这金币也让她害怕。她面对着这些富丽的东西胆战心惊,惟有那个陌生人,她是不怕的,正相反,她一想到他,就心安了。从昨晚起,无论是在她惊喜交集时,还是在她的睡梦中,那个好像又老又穷,而且那样忧伤,但又那么有钱,那么好的人的影像,一直在她那幼弱的小脑袋里闪动。自从她在树林里遇见了这位老人后,她似乎觉得自己的命运改变了。以前,她连飞鸟的快乐都未曾有过,甚至从来不曾体验过母爱。五年来,也就是说,从她记忆能够追忆的最远的岁月起,她是经常在哆嗦和战栗中生活的。她经常赤身露体、痛苦地忍着刺骨的寒风,可是现在她仿佛觉得自己已经穿得暖暖的。以往,她的心总感到寒冷,现在却感到温暖了。她对德纳第夫人也不再那么害怕了。她感到,自己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人和她在一起。
她立刻去干她每天早晨该干的事。她身上带着那枚金路易。它是放在围裙袋里的,也就是昨晚曾遗失了那枚面值15个苏的那个口袋。它使她分了心。她不敢去触它,但不时地看它,每次都得看上五分钟。必须指出,看时,还老是伸舌头。她扫一会儿楼梯,便停下来,站着不动,看一阵子。她把她的扫帚和整个宇宙全抛在了一边,一心只看着那颗在她衣袋底部闪闪发亮的星。
德纳第夫人找到她时,她正在凝视着那颗星。
德纳第夫人是奉了丈夫之命来找她的。说也奇怪,这次她没有打她,也没有骂她。
“珂赛特,过来。”她尽量把声音放低。
不多时,珂赛特便走进了那矮厅。
这时,那个外来人解开了他带来的包袱。包里有一件毛料小上衣、一条围裙、一件毛布衫、一条短裙、一条披肩、一双长筒毛袜、一双皮鞋,一套7岁小姑娘的全身装束,统统黑色。
“我的孩子,快去穿上这些衣服。”那人说。
天渐渐亮起来,孟费梅的居民,有些已经开了院门。他们在巴黎街看见一个身穿破旧衣服的汉子,领着一个全身孝服、怀里抱着一个玫瑰色大娃娃的小姑娘。他们正朝利弗里方向走去。
这两个人正是我们所谈的那个外来客人和珂赛特。
没有人认识这个人,珂赛特已经脱去了那身破衣服,因此,很多人也没有看出是她。
珂赛特离开了。跟她在一起的是什么人?她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她也不知道。她所知道的,就是她已离开德纳第客店,走她的路了。没有人同她告别,她也不曾想到要向什么人告别。就这样,她离开了那个她痛恨它、它也痛恨她的人家。
这个可怜的、柔弱的小生命,直到现在才解除掉被压抑的痛苦!
珂赛特表情庄重地向前走着。她睁开一双大眼睛,仰望着天空。她已把她那枚金路易放到她新围裙的口袋里了。她不时地低下头去看它一眼,接着又看那个老人。她仿佛觉得,眼下,自己是在慈悲上帝的身边。
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德纳第夫人已经习惯,一切由丈夫做主。现在,她正等待着一桩大事的发生。那人把珂赛特领走足足一刻钟以后,德纳第才把她拉到一边,拿出那1500法郎。
“就这些?”她说。
这是她结婚组成家庭后头一次对家长采取批评行动。
这一下起到了作用。
“是这样,你是对的,”他说,“我是个傻蛋。把我的帽子取来!”
他把那三张钞票折好,放在衣袋的最下面,匆匆出了大门。但是他弄错了方向,出门后转向了右方。他向几个邻居打听后,才闹清楚,百灵鸟和那人是朝着利弗里方向走的。他顺着这些人所指的方向,一边迈着大步向前走,一边自言自语。
“这人虽然穿件破旧的黄衣,很明显,却是个百万富翁,而我,竟是个畜生。他先拿出20个苏,接着又拿出5法郎,接着又拿出50法郎,接着又拿出1500法郎,全不在乎。也许他还会拿出15000法郎呢!我必须追上他。”
事先替小姑娘准备好了衣包,这也是奇怪的,里面可大有文章。抓住了秘密就不应该松手。有钱人的隐私是浸满金水的海绵,应当晓得如何挤压它。所有这些想法都在他的脑子里回旋着。“我是个畜生。”他又骂自己。
离孟费梅不远便走上了通往利弗里的公路。这条公路在高原上蜿蜒曲折,很长。他来到岔路口,走上公路,估计能看到那个人和珂赛特。他极目远眺,在目力可及的地方,什么也没有。他向人打听,人们告诉他,他们朝加尼方向的树林那边走去了。他赶紧追过去,因为打听他们去向已经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他们走在他的前面,由于孩子走得慢,他走得快,并且熟悉路途,这样,他也就能赶上他们了。
忽然,他停了下来,拍了拍自己的额头,想必是忘了什么极重要的东西想要转回去取。
“我应该把我的长枪带来!”他自言自语道。
德纳第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那种人有时混在我们当中,没有一定的气候便一直不露真相。有许多人就是这样半明半暗度过一生的。德纳第在平静、平常的环境下完全可以当——我们不说“是”——一个诚实的商人、好的士绅。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当某种动力拨动他那隐藏起来的本性时,他便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恶棍。撒旦也会时而蹲在德纳第生活的那所破屋的某个角落,并在这个丑恶的代表人物面前做梦的。
犹豫了一阵以后,他想:
“唔!来不及了,这样他们或许已有足够的时间走掉了!”
于是,他便继续快速地向前奔走,一副极有把握的神气,动作敏捷得如同一只凭嗅觉猎取鹧鸪的狐狸。
果然,他走过池塘,斜着穿过美景大道右方的大片旷地,走到那条长满杂草、环绕一个土丘而又延伸到谢尔修院古老水渠涵洞上的小径,这时,有顶帽子从丛莽中露了出来。是那人的帽子。对这顶帽子他曾多次琢磨过。那丛莽并不高。德纳第判定那人和珂赛特是坐在那里的。那孩子小,他看不见她,可他看见了那只娃娃的头。
德纳第没有错。那人果然在那里坐着,因为珂赛特需要休息一会儿。他绕过丛莽,突然出现在这两个人面前。
“先生,请原谅,这是您那1500法郎。”他气喘吁吁地赶上去说。
他边说,边把拿着那三张钞票的手伸过去。
那人抬起眼睛,问:
“干什么?”
德纳第恭敬地回答:
“先生,这意思,就是说,我要把珂赛特带回去。”
珂赛特浑身战栗,紧紧偎依在老人怀里。
他呢,目光直刺德纳第的眼底,一字一顿地问:
“你——要——把——珂——赛——特——带——回——去?”
“是这样,我要把她带回去。我告诉您。我考虑好了。我没有权利把她随便送人。您知道,我是个诚实的人。这小姑娘不是我的,她有母亲,她嘱托我照顾这孩子,我只把这孩子交给她的母亲。也许您会说:‘孩子的母亲死了。’那好,那我就只能把孩子交给她母亲托付的人。我要看到她母亲亲笔签字的委托书。这是明摆着的理。”
那个人没有说什么。他把手伸进衣袋,随后,那个装满钞票的钱夹又一次展示在德纳第面前。
客店老板高兴得浑身颤抖起来。
“好了!”他心里想,“我要站稳脚跟!他又要来腐蚀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