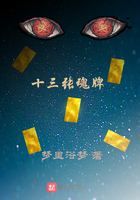“好吧,”他说,“你们替我们把床垫撕烂吧,我们需要绷带。”
古费拉克讥讽霰弹不中用,他对大炮说:
“伙计,你也太不顶用了。”
战场犹如舞会,人们在互施诡计。街垒的沉默令进攻的一方摸不着头脑,为了防止意外,他们觉得有摸清街垒内部情况的必要,想看看这默不做声的家伙究竟在干什么。起义者忽然在邻近的一个屋顶上发现有一顶消防钢盔在阳光中闪烁。不错,在高烟囱旁,好像一个岗哨,正向街垒这边观察着。
“一个可恶的监视者。”安灼拉说。
冉阿让已经把卡宾枪归还了原主。他有自己的枪。
他不动声色,瞄准了那个消防队员。砰的一枪响后,那人的钢盔不见了——它落在街上,响声很大。那失了头盔的士兵吓走了魂儿,逃掉了。
一个军官接替了那士兵的岗位。冉阿让又是一枪。那军官的钢盔也被打落。那人大概明白了射击者的用意,悄悄走掉了。对街垒的侦察随即放弃。
“您为什么不打死他?”博须埃问冉阿让。
冉阿让没有说话。
十二混乱中的秩序
博须埃在公白飞的耳边低声道: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
“可能是个慈悲为怀之人。”公白飞说。
对过去若干的事进行记忆的人都想到了,在镇压起义军的战斗中,郊区国民自卫军的表现是十分勇敢的。尤其在1832年6月的那次事件中,他们既顽强又无畏。好些酒店的老板,如庞坦酒店的老板、凡都斯酒店的老板、古内特酒店的老板,见酒店无生意可做,统统变成了狮子。为了维护酒店的安全,他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推而广之,在这具有市侩气息又具有英雄气概的时期之内,各种思潮都涌现了自己的骑士。私利都不例外。别瞧动机平凡,它并没有减小它在运动中的胆量。见白银堆降低了,银行家会唱起《马赛曲》。为了钱柜,人们可以表现牺牲的勇气,不吝惜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了护卫自己那极其渺小的酒店,使酒店成了国家的缩影,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斯巴达人的狂热。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这就是社会。各个成分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平衡是未来之事。
无政府主义进入政府至上主义(这是正统派的一种怪称),这是那个时代的另一特点。人们用纪律在维持各自的秩序。某一国民自卫军上校的指挥棒一挥,就可突然莫名其妙地擂起集合的战鼓;某一个上尉一时激动,就率众冲锋;某个自卫军为了“主义”,自己就可以投入战斗。在这些日子里,人们采取行动,并不一定得到上级的指示。在治安部队里会出现真正的游击队员,有的可以像法尼各那样拿起武器,投入战场,还有的可以像亨利·方弗来特那样拿起笔来,撰写檄文。
那个时代的不幸,在于文明不是某些原则的代表,而是某些利益的汇合。它不时地处于危急之中,不断地发出紧急呼吁。每个人都自作主张,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对它加以维护。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在拯救社会。
这种情况便出现了暴政。国民自卫军的分队中设立了军事法庭,处死一个起义者就像杀掉一只鸡。5分钟之内即可解决问题。让·勃鲁维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处死的。没有办法对对方这一行为提出指责。这是残酷的林奇裁判林奇裁判,美国的一种刑法,抓到罪犯后当场判决,立即执行。。美国的共和政体像欧洲的君主政体一样,都是这样行事的。私刑加误会,任何事情既变得很简单,又变得很复杂。有这样一个故事,暴动时期,有一个叫保罗-埃美加尼埃的年轻诗人,在王宫广场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手持尖刀的人追逐着,他只得躲进6号大门的门洞。他犯了什么罪,他们要杀死他?有人对他高呼:“一个圣西门主义者!”原来,他腋下夹着一本圣西门公爵圣西门公爵,著有记述当时宫廷及显贵琐事的《回忆录》。此处指人误认为他拿的是空想主义者圣西门的著作。的《回忆录》。一个国民自卫军军士,只看到封皮上“圣西门”这个名字,就大叫:“杀死他!”
1832年6月6日,一名叫法尼各的上尉,他指挥下的一连郊区国民自卫军在麻厂街便制造了血腥杀戮。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此公。杀戮出于怪癖和一时的兴致。1832年起义结束后,法庭审理了这一案件。原来,法尼各上尉者,乃是一个性情急躁的小市民,他喜欢冒险。在维护秩序的队伍中,他扮演的是一个类似雇佣兵那样的角色。这类人的特征我们已经进行过描绘。这是位政府至上主义者。他狂热,无法无天。他的冲动没有什么人可以制止。他还有野心,打算由他的部队单独攻占街垒。当他看到街垒上红旗倒下又重新挂起旧衣时,简直怒不可遏。他破口大骂那些开会时认为进攻时间尚未到来的将军们和军团长官们。他讨厌这些人总是重复着这样的一句话:“让造反者煮在由他们自己调制的肉汁中”。法尼各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夺取街垒的条件已经成熟。熟了的苹果应该落地,他要上去尝一尝苹果的味道。
他和他的被当场见证者称作“一群疯子”的同伙,足足有一连人。他们是驻扎在那条街拐角处的一营中的第一连。是他们枪杀了诗人让·勃鲁维尔。夜间向街垒发起进攻是少有的。但这位上尉这样干了。这说明他仅凭狂热的意愿行事而没有任何策略考虑。结果,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还未到达这条街2/3的地方,便吃了街垒一排排密集的子弹。四名胆子最大的士兵冲在最前面。他们应声倒下。这些国民自卫军好汉们是英勇的,但是缺乏军人应有的顽强性。面对起义者的子弹,他们犹豫了。在街心留下了15具尸体之后,他们凄然退了下来。犹豫给起义者提供了重新装子弹的时间。第二次射击威力很强。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躲回街角掩体里的人被击中。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处在双方火力的夹击之中,还受到大炮的轰击,因为大炮没有接到停止射击的命令。这位英勇而不谨慎的法尼各,就这样成为霰弹的牺牲品。他被炮火击毙,就是说被他的秩序击毙。
安灼拉对这种进攻感到异常的愤怒。“蠢材!”他说,“他们打死了自己的人,还惹得我们白白浪费了子弹。”
这番话,安灼拉是以暴动行列里一个真正的将军身分说出的。起义者和镇压者之间力量对比悬殊。子弹盒空了,没有办法填充;人员伤亡了,没有办法补充。然而,镇压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有整个军队,有万塞纳兵工厂,弹药用之不竭。他们的联队数比街垒中的人数还要多,他们的兵工厂的数量,不比街垒中子弹盒的数量少。这是百对一的战争。这注定,街垒最后必被摧毁,除非革命突然爆发,在倾斜的天平上,天神的火红利剑加在起义者这边。因为只有那样,只有每条街都沸腾起来,街垒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只有这些异乎寻常的因素齐备,巴黎才会震动,一个神妙的东西才会出现于大地,才会再次出现一个8月10日,再次出现一个7月29日。那神奇的光辉出现后,张着血盆大口的权威才会退却,军队,这只狮子,也将望着镇定自若的预言者——法兰西,在面前站定,而束手无策。
十三一线希望当空掠过
街垒中,道义感,激烈的冲动,应有尽有。这里充满勇敢的精神、青春的朝气、美好的理想、坚定的信仰、赌徒般的顽强,特别是,断断续续,还有一线希望。
时断时续,一个模糊的希望突然颤动起来,它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掠过麻厂街的街垒。
“听!”一直戒备不懈的安灼拉突然叫起来,“巴黎像是醒来了。”
在6月6日清晨的一到两个小时之内,这些起义者确实勇气倍增。圣美里持续不断的警钟声使起义者的微弱希望再次复苏。梨树街,格拉维利埃街,一下子出现了两个街垒。在圣尔马丹门,一位青年,手持卡宾枪跪在林阴大道上,以肩抵枪,毫无掩蔽,单枪匹马在与一个骑兵连对峙。骑兵队长被击毙,那青年高兴地说:“又少了一个,他不必再给我罪受了。”最后,那青年死于马刀之下。在圣德尼街,有个妇女,躲在百叶窗后,向警察射击。百叶窗帘每动一下,就意味着有一颗子弹射出。在高松纳利街,有一个14岁的孩子被警察抓住。他口袋里满是子弹。若干个岗哨受到了攻打。卡芬雅克·德·巴拉尼将军带领的装甲联队在贝尔坦·波瓦雷街口,突然遭到排枪的扫射;在卜射什·米勃雷街,过路的军队被从屋顶扔下的破坛烂罐和家用器皿打伤。这是不祥之兆。当有人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苏尔特元帅时,这位拿破仑的老上尉沉思起来。他想起了絮歇絮歇(1772-1826),法国元帅。元帅在萨拉戈萨时讲过的一句话:“什么时候老奶奶用尿壶往我们头上倒尿,失败就逃不脱了。”
人们以为暴动的局面得到了控制。谁想,新的怒火又重新燃烧起来。巴黎像堆干柴,骚动的情绪像颗颗火星,它们一旦落在干柴上,便会燃起熊熊大火。对于这种形势,军事长官们甚为忧虑。他们不放松任何起事的苗头。在此情况下,对莫布埃街、麻厂街和圣美里街街垒的进攻被推迟了。他们想集中兵力,一举全歼。
有些联队被派往有骚乱迹象的街道,进行肃清工作。大街左右的一些小街小巷,也成了扫荡的对象。这些联队有时蹑手蹑脚,小心提防,有时则加快步伐,迅速推进。从暗处射来的冷枪使他们防不胜防。与此同时,骑兵驱散了林阴大道上集会的群众。这些行动激起了骚乱,酿成了军队和市民的冲突。在炮轰和排枪之间安灼拉所听到的就是这些声音。另外,安灼拉还看到,街的另一头有人用担架抬走受伤的人。他对古费拉克说:“那受伤的不是我们的人。”
希望之光没能持续多久,微光很快便消失了。不到半个小时,萌芽状态的暴动犹如一道闪电划过长空,顿时消失。冷漠的民众将铅质的棺罩扣在这些不屈不挠的起义者身上。
总暴动流了产,尽管它曾显出雏形。现在,陆军大臣陆军大臣,指苏尔特元帅。和将军们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街垒上。
旭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一个起义战士问安灼拉:
“大家饿坏了,难道我们就这样饿着肚皮等死?”
安灼拉的手肘支在胸墙上,注视着街头那边的动静。
听了那问话,他没有改变姿势,只是点了点头。
十四从这里看到了安灼拉情人的名字
古费拉克坐在安灼拉身旁,一刻也没有停止咒骂那尊大炮。每次,炮响并射来霰弹时,他就道出一连串的讽刺话。
“可怜!老畜生!我替你难受,你大叫大嚷,可吼不响了。这哪里是开炮,简直是在干咳。”
他的话总会把周围的人逗乐。
古费拉克,还有博须埃,他们的英雄气概与乐观情绪随着危机的加剧在增强。他们像斯卡隆夫人斯卡隆夫人,路易十四的情妇。那样,用玩笑来抵御饥饿。没有葡萄酒了,他们就向大家灌注欢快。
博须埃说:“我佩服安灼拉。他沉着,有胆识,这令我叹服。他生活孤独,这可能使他变得有些抑郁。这安灼拉,为了他的伟大事业过着鳏居生活。他也在抱怨。我们这些人,为情人而疯狂。为了得到猛虎的爱,我们会与狮子决斗。我们便是如此让那些给我们颜色看的女人们看看我们的颜色。罗兰罗兰,指意大利诗人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他热恋着安杰丽嘉。为了使安杰丽嘉烦恼,不惜让人将自己杀死。我们的大无畏精神是女人送给我们的。男人离开女人,就等于手枪没有撞针。催男人奋进的力量是女人。可安灼拉与众不同,他没有女人,也不谈恋爱,可他顶天立地。冷若冰霜,可又猛如烈火,真是不可思议。”
安灼拉似乎根本不理睬别人在谈论他什么。如果谁靠近了他,就会听到他在用拉丁语念叨着:“祖国。”
博须埃继续谈笑着。古费拉克却突然大叫起来:
“看哪,新角色登场!”
随后,他模仿看门人通报的语调,又说:
“八磅炮阁下到。”
不错,第二门新式的火炮登了场。
炮兵们在快捷而费劲儿地操作着。第二尊炮架在第一尊炮旁边,在做射击的准备。
看来,大戏要落幕了。
不一会儿,两门火炮同时向街垒开火。正规军分队和郊区国民自卫军分队在发放排枪,与炮兵配合作战。
稍远的地方同时传来炮火声。在这两门炮猛烈轰击麻厂街街垒的同时,另外的两门炮,一门对着圣德尼街的街垒,另一门对着奥白利屠夫街的街垒猛轰。圣美里街垒被打成了蜂窝状。
四门炮相互间的回声在巴黎上空激荡,凄厉而哀怨。
警犬的阴郁吠声在与枪声相互呼应。
轰击麻厂街街垒的两门炮,一门使用的是霰弹,另一门使用的是实心弹。
那门发射实心弹的炮口瞄准点高些。它的目标是街垒的顶部。他们企图把它削平,把铺路石打成碎片,使碎石像霰弹那样击伤起义者。目的在于迫使街垒里顽强抵抗的战士们尽快撤出。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把战士从街垒顶上轰下来,霰弹则把小酒店窗口的起义者驱散。这之后,突击中队就可以冲进街道而免遭射击,甚至不一定被发觉,可以像昨晚那样突然爬进棱堡。也许,奇袭是拿下街垒的最有效方法,谁能说不成呢?
“必须减轻这两门炮带来的麻烦,”安灼拉说,接着他大声喊道,“向炮兵射击!”
一声令下,沉默已久的街垒再次射出密集的子弹。街上一片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几分钟过后,大家透过浓烟看到,大约半数以上的炮兵倒在了大炮轮子之下。剩余的人镇静自若,顽强反击着,可火力已大大减弱了。
“好极了,”博须埃向安灼拉说,“非常成功!”
安灼拉摇摇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