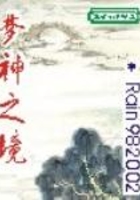与他并排而行,这到不是头一次。
她能明白他对自己的情感,不算太喜爱,男人说是娶妻求贤,可第一条件还是取貌的,她只是有些特殊,因为她不会谄媚于他,兴许这是对他的大不敬,但也顺利让她与别人有了些区别。
她无法去设想他与其他女人相处的场景,即使再淡然的人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假想,所以她什么也不想,这样才能保持平静。
很巧,在宫苑的转弯处他们遇上了带着孩子的赵又欣。
只有在面对他的宠妃时,比较才会明显——他对她是不错,但这个“不错”与“很好”、“极好”叫爱是相差甚远。
前些日子,他一直冷落着赵又欣,也许是各方面都闹得太厉害,他故意要她知道失去他的宠爱将会一无所有,于是赵又欣只能屈服,慢慢的,宠爱又恢复了,赵又欣还是之前的赵又欣,宠爱依旧是之前的宠爱。
可能他会是个专情的人,但很抱歉,那个女人不会是她莫蓉,她是很特别,但现在的地位已经足够能证明她的特别。
这就是现实,她必须面对的。
“乳母说这几日泰康不大愿意吃东西,臣妾就想带他回去一起吃顿饭。”皇家的女人都是可怜的,即使是自己的亲骨肉,也只能看着他们在别人的怀里哭笑。
赵又欣向他福礼,而莫蓉向赵又欣福礼,这繁冗拉杂的规矩每天都在这圈宫墙里上演千百次。
莫蓉悄悄地抽身,人是要懂得进退的,尤其在这种地方。
望着那一家三口,是该这么说吧,一家三口——那画面很温馨,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以及他们的孩子,编成一个叫做家的东西。
他说过要她给他生个孩子,孩子……
她有这权利把她(或他)带到这个世界来吗?来面对这样一个家族。
梧桐树下,积雪飘飘洒洒,犹如下沙。
张开手,雪在手心化成水珠,望着手心上那点点的水珠,良久后抬头,隔着朦胧的细雪,他正驻足回身,因为她没有跟上。
要她一起走?与他们一起?她不想破坏那么温馨的画面,她的想法里,那画面中是只能有一个女人的,微微福身,攥紧手中的水珠,转身踏上了另一条路。
如果这偌大的后宫里只能有一个女人幸福,她非常愿意祝福那个女人。
也就是当天傍晚,王太妃让宫人来传了话,说是让莫蓉去她那里坐坐。
王太妃是王氏家族的嫡女,先皇五十大寿时入得宫,当时年仅十六岁,一入宫就得先皇的宠爱,到如今还能住在内宫,并受到悉心供养,多是因为是她与尉迟南的生母李氏有恩,当年王太妃深得先皇的宠爱,而尉迟南的母亲却因后宫争宠中落于败势,差点丢了品级,幸得王氏在先皇面前的良言,才不至于被降,以致后来尉迟南也有机会继任大统,因此她算得上功不可没,自从太后过世后,她俨然占据了太后的一切尊崇。
莫蓉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她知道王太妃找她是为了什么。
早上本来是想问尉迟南对这件事的打算,但因为碰上了赵又欣母子,便再也没机会了。
“到是个清秀的人儿。”王太妃仔细打量过一番莫蓉后,给了这么个极高的评价,说实话,之前她可是连正眼都没瞧过她。
莫蓉笑着低下眼睑。
“哀家听说你们莫家在东省也是个书香门第。”翘着尾指,用茶碗盖轻轻拨开茶上漂着的茶叶,那颗硕大的翡翠戒指随着她的动作上下晃动着,着实惹眼。其实王太妃的年纪并不算老,认真算下来也就四十多岁,只不过早早丧夫而已,“其实这文武百官哪一个不是从小吏做起的,只要对皇上忠心,能为皇上解忧的,那都是好官,不过呢,这金子再亮,染上了乌尘仍旧不能被人识得,得有人时不时地擦拭。”这话言外之意很深远,既是指莫蓉,也是指莫家。
这就是所谓的拉帮结派吧?
莫蓉笑着点头。
王太妃对她的点头十分满意,就是嘛,这女人还是要灵慧一点,既然都已经进了宫,那就得为自己的将来好好打算,背后没有一个有势力的家族,皇上再喜欢有什么用,哪天出来个更漂亮、更年轻的,失宠还不就是一转脸的功夫,“哀家这记性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前几天卫妃还跟哀家提起来你的年岁,这一转脸我就给忘了。”事实上根本不曾谈过她,又何来的忘了?
“回太妃,过了春上,就满二十二了。”
点点头,“不大,卫妃不也是二十二才遇喜的。”饮下一口茶,“咱们这位皇上重国事,整日忙着操理国家大事,至今这后宫也没个掌事的,子息也不够旺盛,哀家一直为这些事发愁,就希望你们能为皇上多添几个小皇子,这么一来咱们这宫里不就热闹了嘛。”
莫蓉望着她手上那枚翡翠戒指笑意融融,是会“热闹”的,皇子越多,闹得越凶。
“对了,哀家记得你娘家还有兄弟吧?”这才谈到正事上来。
“是,一个兄长,两个弟弟。”
“你那两个弟弟都在军中吗?”
“是的,蒙皇上恩宠,之前在御林军效力,后来都调去了西北。”
放下茶碗,王太妃瞅着她笑意盈然,“千金难买的就是年轻人的上进,你这几个兄弟听说都是得皇上喜欢的,今后定然会大有作为。”
“谢太后夸赞。”
莫蓉本以为她会提起平奴,可她猜错了,她只字未提,两人谈得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
从王太妃那儿刚回到崇华苑,赏赐便也到了——王太妃让人送来了一张药方,舒经络的,庞朵见过,说是后宫妃嫔们用来求子的药方。
就是因为这张药方,才有了后来的诸多事,而这诸多事改变了莫蓉的一切。
药方被莫蓉随手夹在了一本《铭文录》当中,她没打算用。
一年多了,被召幸的次数不多,但也绝对不少,可始终没有消息,想来是上天根本就不愿给她做母亲的机会。
可庞朵不这么认为,硬是照着药方把药配了个齐全。
“娘娘,您就喝了吧,这药特别,不能用一般的药壶,奴婢可是求了半天执事的公公,才借过来的。”
拗不过她,莫蓉勉强喝了下去,结果当天夜里吐了个半死。
生孩子并不是一个人的事,如果靠喝药能生出皇子来,那还要皇上做什么?所以莫蓉觉得这求子的药方堪称无稽。
这段日子,尉迟南再没来过崇华苑,一方面朝廷事忙,另一方面,最近赵又欣低下了身段,他去凤阳宫的次数增多,显然目前还是赵又欣的时代,别人莫与争锋。
“最近换香料了吗?”莫蓉从桌案上抬头,一不小心把墨汁蹭到了画纸上,一副快完成的山水就那么白画了,不禁怨叹。
“没换啊。”庞朵纳闷,她怎么会突然问这事,“是不是闻着不舒服?”
“就是觉着最近这香料似乎清淡了些。”折上画纸,有些不甘心,画了一个晚上的山水就让那几滴墨汁给毁了。
“这香料是前几天执事公公们刚发放给各宫的,说是今年新配制好的,兴许是新配的,所以闻着不够浓,娘娘要嫌清淡,奴婢这就去多放一些。”
“不用了,就是偶然这么一问,时辰不早了,睡去吧。”
“娘娘,时辰还早,要不再等一会儿?”
“还等什么?这会儿皇上还在凤阳宫,难不成他还能过来?”清洗好画笔,挂上笔架,顺手拔了发髻上的步摇,既然等不来,那就不要硬把自己的闺怨勾出来,否则这漫漫长夜如何过?
蜷缩在被褥里,捂了很久,被子里仍然是冷冰冰的,也许她天生就是个凉薄的女人,血跟心一样。
坐起身,突然觉得呼吸不畅。
拉开帐子,赤着双脚踩在冰凉的地面上,吧嗒吧嗒的。
呼吸不畅——每隔一段时间,这种窒息感就会如噩梦般降临一次,她需要更大一点的空间。
“你这是在干吗?”尉迟南盯着她踩在雪地上的双脚,这女人发什么疯?大半夜竟赤脚踩在雪地上!
没想到会撞上他,莫蓉有些不知所措,“刚想起来好像丢了什么——”手在空中划了半圈后垂下,她实在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
回到内殿,莫蓉从床角勾过鞋子,回过头,他就在跟前。
不知因为什么,今天有些排斥他的碰触,也许是那天他跟赵又欣的画面太温馨,让她有些……是的,她可能是有些嫉妒,但也只是一点点。
所以,她才会有一点点排斥他。
“知道吗?今天有人在大殿上赞扬你。”一根一根掰开她的手指,让两人的手掌紧紧相贴。
有人在大殿上赞扬她?这就是他还能记起她的原因吧。
“不想知道是谁吗?”
摇头,她能猜到是谁,能在大殿上提到她的人,除了那些匈人的使者,还会有谁,她二十二年的生命中,只出过那么一次风头,怎么,想看她欣喜若狂吗?可惜她现在没心情表演给他看,因为他压在她身上的重量让她呼吸不顺。
“生气了?”他当然看得出来,那天她掉头就走时,他就猜到了会有这么一幕,女人的这些小脾气他很了解,赵又欣也这么使过脾气——不过最终却乖顺的很,因为她懂得了一个道理,失去了他,对她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咬着手背,忍受着他制造出来的痛楚,这种事对男人来说也许只是一种纯粹的征服——
尉迟南眉头蹙紧——她竟会咬他。
轻拭嘴角,指肚上是一抹轻浅的血痕——长这么大,这是第一次被女人咬,还是在欢 爱的时候。
莫蓉的胸脯起伏不平,努力吸收着新鲜空气,实在被他吻得喘不过气,而且她讨厌被吻唇,那会让她有种恶心感。
尉迟南盘坐起身,被褥滑至腰腹,激情的残余让他呼吸还略显急促,这女人骨子里透着一股怪异的泼辣,“有药粉吗?”伤害龙体是大罪,这伤口当然不能让人看到,他还不至于因为这点小伤让她受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