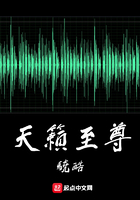闫夫人那边,医师来把过脉,开了药方,命仆人前去抓药。所幸并无大碍,只是上了年纪,身体本就虚弱,又因一时大悲,急火攻心所致,刘皛同两个丫鬟伺候闫夫人。
拓跋褚温带向如到前院正堂,这里离闫夫人那边比较远,若是有什么谈话,或者即便是有争吵,后院那边也不是很听得见。
拓跋向如自知理亏,一进正堂,便跪倒在地上。
“爹,是孩儿的错,孩儿考虑不周。”
拓跋褚温背着手,出了一口长气,压住心中的怒火,随后轻声询问道:“错在哪儿?不周又在哪儿?”
“一来,没有安全护送妹妹到达长安,二来,何不该当娘的面,说玥儿的不幸。”
“难道就这两点吗?”
拓跋向如甚为不解,爹是几个意思呢?难道他哪儿还有不周或者差错的地方吗?一番仔细寻思后,终究是想不起哪儿还有过错。
拓跋褚温道:“你且给我仔细说来,玥儿被山贼劫持,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听旁人说起,你走出洛阳城没有多远,又返了回来,这是为何?”
向如一惊,当时这事,没有别人知道,他离开时更是特意交代过朋友,此事说不得,又是谁将此事传到爹的耳朵呢?莫不是刘皛也知道这件事?
“爹有所不知,那日,我本快马加鞭前去,奈何在路上听见有女子呼救声。”
拓跋褚温打断道:“玥儿在路上还不知好歹呢!你倒是菩萨心肠,反倒担心起别人的安慰来了,若不是你在半道上耽搁,能迟去吗?玥儿能出事吗?”
向如扶在地上,委屈说道:“爹,且听我说。”
“休得多言,来人,给我拿棍棒与长椅来。”
拓跋向如一听这架势,暗自叫苦,在他印象中,小时候被这样打过一次。看来今日的一顿皮肉之苦,在所难免,只是他现在的身子也是比较虚弱,这一顿棍棒,可是叫他吃不消。
“爹爹,且听我说,打我是小,伤者娘亲的心是大,娘亲现在身子较虚弱,我还得孝敬娘亲老人家呢!”
拓跋褚温道:“放屁,不要强词夺理,我还没有死呢!全家上下如此多人,不需要你来照顾你娘亲,先吃我一顿棍棒再说你的不是。”
仆人站在两旁,没人敢去取棍棒。
拓跋褚温呵斥道:“你们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老爷,不想一并挨打的,去给我拿棍棒与长椅来。”
仆人无奈,只好去拿东西。
老爷看着厅堂之上,眼泪打转,强忍住心中的悲痛之情。
须臾后,仆人拿着棍棒与长椅走了进来。
拓跋褚温夺过棍棒,呵斥道:“你们几个,愣着干嘛?把这不争气的畜生,给我按到长椅上来。”
拓跋向如趴在长椅上,偏着脖子说道:“爹爹,手下留情,孩儿已知错,何必打了我的身子,伤了你跟娘的心呢!”
“知错?知错能让玥儿回来吗?知错能让我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回来吗?还不撅起屁股?”
向如嘟囔道:“爹原来是心疼那些银子?”那些银子,拓跋向如一点也不知情,拓跋褚温在那些骡马身上,个个披着红妆,红妆里边藏着三十两银子,一共加起来,差不多有大几百两银子呢!
“逆子,休得多言,尔等给我按好了畜生,不然小心合着你们一起挨打。”
拓跋褚温举起棍棒,照着向如的屁股上打去。
起初,向如的屁股还能左右晃动,十几棍棒下去后,他嚎嚎大哭。
“闭上你的嘴,再乱叫,看我不打烂你的嘴。”
拓跋向如疼痛难忍,突然从椅子上倒了下去,再看拓跋褚温丝毫没有要停手的意思,居然照着向如的大腿打去。
说时迟,那时快,向如在地上一个旋转,一把握住棍棒,怒目狰狞的看着爹。
“逆子,逆子难不成要造反?”
拓跋向如道:“你还知道,我是你儿子,为何下如此重手,我真怀疑旁人所说,我究竟是不是你亲生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