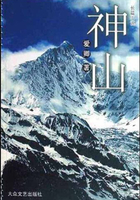一九三八年,陈树仁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取名锦汉。这是陈家第三代的长孙,陈斗升因此颇为欣慰,在神主牌前双手合十、鞠躬,向祖先报喜。与此同时,广州沦陷。日军的飞机不时从古老的广州城上空呼啸而过,砖瓦横飞、血肉模糊,给原本美丽、安定的城市带来惨烈的灾难。有条件的人家往乡下避难去了,没法走的穷苦人,只得守在家里等死。无线电里仍是一派抗战之声,然而南京失守,抗战军队节节败退,广州城守不住,整个中国便几无可退之地了。陈斗升决定带领全家往山区逃,先是去了四会,后又迁到广宁。
乡下的天地似乎比省城开阔许多,乡路阡陌交错,屋舍之间疏离有致,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已收割的稻田显出一片绿意盎然。山风清冽,阳光温暖,冬天最引人注目的是甘蔗,仿佛一日比一日高,每个枝节都在生长。菜地里亦是一片新鲜颜色,一畦畦的生菜长势喜人,层层菜叶包裹着豆沙绿的嫩芽,是丝线里需要特殊浸染才会呈现的颜色。
陈斗升略弓背,抄着手,与树仁在田埂上缓缓散步,脸上露出些许笑容,说:“这个地方不错吧。”树仁顺从地点点头。空气中依稀飘散着菜香、果香,清新沁人——这一点比状元坊好,状元坊里总飘荡着一股呛人的衣浆味。
村里的老人每天聚在村口的榕树下聊天,有人说已经看到日本兵了,有人说炮车都运进来了,说得人心惶惶。然而,人们依旧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仿佛这宁静的生活,不会因任何事而受影响。
陈家租的是远房表叔的房子,只有主屋是完整的,陈斗升带着树仁用泥坯砖砌了两边的侧房。院子里平了土,陈师母说要养鸡。徐宁对此强烈地反对,房前房后常有邻居家的鸡来串门,留下的鸡屎已难以铲除。陈师母很怕这个新抱的脾气,不敢十分坚持,翠凤也不是很热心,只得作罢。陈斗升指挥着树仁,在院外搭起竹篱笆架,学习了乡下的传统搭法,用细藤缠绕了,交错打结,用来种些蔬果。屋前屋后亦松了土,种了青菜,用以帮补一家人的伙食。
家里的重担渐渐转移到了树仁身上。徐宁生完孩子,身体娇弱,每天斜躺在床上不愿意挪动。陈师母全力照看着小孩,力有不逮,常在一家人面前扭腰捶背,埋怨说:“顶唔顺[39]。”陈斗升到了乡下,仿佛水土不服,渐渐地失去了精锐气。他整日整日地蹲在院门槛上,不停地抽着水烟,或者站在田垄上,望着宽阔无际的田野出神。树仁制了个家庭数簿,每日计算吃穿用度,上边的数字有减无增,每每想添些家庭日用,总要犹豫半天。
这一天,是乡里的墟日。树仁早早便提醒了翠凤,与黄柳一起,三人一早去赶墟。乡下地方小,只到墟日东西才齐全,也便宜些。不料一大早,徐宁突然发起了脾气,说树仁丢下她和孩子不管,自己趁热闹玩耍去了。树仁亦是急,说:“赶墟是为了省钱,家里现在有进无出,省一厘是一厘,你以为还是以前做有钱小姐的时候。”这话一说,却是勾起徐宁的伤心,她摔了枕头,又将被子扯开,将所有歇斯底里都发泄出来了。
树仁怕吓着了孩子,一时不敢走。陈师母唉声叹气,说日子怎么过到这个地步了。陈斗升似乎什么也没听到,只顾蹲在门口抽烟。翠凤一早便起来给菜地浇水,准备妥当,在大门口等着,等了许久,仍听到树仁夫妻俩吵闹不休,终于忍无可忍,走入正屋,对着徐宁大声说:“大嫂,我们正在逃难,家境困难,你为大哥着想些好不好!”
徐宁自嫁入陈家,从来没见过翠凤发脾气,第一次见她如此发怒,竟是反应不过来。树仁趁机离开,临走前不忘嘱咐母亲,让她算着钟点给孩子喂米糊。
山路崎岖,三人一路跋涉,走了很长的山路,到了镇上。墟日人多,短短的一段土路,两边摆满了地摊,堆满了土货,中间人流如水,挤得无法向后转。在墟街上绕了半天,陆续买入了米、油、盐,看到五花八门的日用杂货,又忍不住买了许多,其中有乡里人自制的酸梅,可以做下饭菜。
同样的钱能买到比平时多一倍的货物,大家都很高兴。回去是上山的路了,三人都背着沉甸甸的背包,比来时更累。翠凤咬牙切齿,不时停下抬头看天,说:“日头真毒!”她佝偻着身体,走得吃力,一步三歇的。黄柳已累得满头冒汗,忍不住说:“我总得找个教书工作,上次去问乡中学,不见答应。听村口那几个老伯说,旁边村子也有个学校,我明天去看看。”
翻过一座土坡,翠凤已累得浑身发抖,腿脚怎么也迈不开,只好在路边就着几块石头坐下。她脸色惨白,呼呼地喘着气,说:“朝不保夕的时日,学校全关门了,哪里还能找到教书工作?”树仁背靠着一棵树休息,微蹙了眉,说:“我们再商量看,一家人做点小生意,或许能过活。”
三人正说着,冷不防从旁边杂草丛里冲出一个人,大喊一声:“留下买路钱!”来人穿一身精简布衫,蒙着面,只露出眼睛,手里举着一根手臂粗的木棍。翠凤吓了一跳,第一反应是护着米袋。不料强盗一眼看见了,立刻向她冲去,手中的木棍狠狠敲下。翠凤眼见棍子下来,立刻缩手,还是被砸到了,痛得惨叫一声。树仁虽然害怕,但见对方一人,身量不高,便想以力气搏一搏。他立刻跳到翠凤面前,张开双臂阻拦。不料草丛里又跳出一个人,同样是蒙着面,身量不高,看身形约莫还是少年。两个强盗挥舞着棒子,一个去抢了翠凤的米袋,另一个捡起地上的杂粮袋,跑得飞快,转眼便消失在树林里。
这一变故来得突然,三人都不知如何反应。黄柳缓和过来,先是查看妻子的伤势。树仁见强盗的背影单薄,想拔腿去追,翠凤立刻喝住他,说:“不要追,危险!”
树仁本能地停下来,仔细一想,人生地不熟的,确实不能乱跑。这强盗虽然是孩子,附近也许有人接应。“我们是外地人,被盯上了也不出奇。”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翠凤挨着石头慢慢坐下,抹去眼泪,淡淡地说:“都是苦人家,要不是穷到无路可走,也不会昧了良心做伤天害理的事。”自己卷起衣袖查看伤势,又乐观地说:“好在人没事。”
黄柳给翠凤按揉伤处,感叹说:“乡野之地,又是混乱时势,全凭武力说话,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不要轻举妄动。”
本想着墟日购买物资便宜,不料遇上强抢的,不但没省下钱,反而损失了好大一笔,全家上下都很难过。陈斗升翻着数簿,唉声叹气,说:“俗语有话,衰开有条路[40],果然是没错的。”黄柳闷声不吭,翠凤是个外柔内刚的性格,虽然挨了一棍,却没有留下太多阴影,缓过了不快的情绪,立刻重新去购入米、油。
这一年的气候十分温和,乡下视野开阔,一眼望去是平坦的田地,极目都是绿色,仿佛一幅精心设计的、以绿为主色调的绣品。院子旁边辟出来的菜地,刚入冬时种了些生菜、小白菜,到了冬日便能收些。表伯公亦送了腊肉来,吊在屋檐下。陈家居住在广州多年,虽算不上大富大贵,好歹是有份家业,衣食充足。如今却是举家困顿,有一技之长却无法谋生。然而时局艰难,人命在乱世中无能为力,只能求上天保佑,合家平安,勉力生存。
熬过了冷且贫苦的冬天,到第二年春分,兄妹俩便商量着,在乡下开个成衣小铺。陈斗升对此并不看好,说自己早打探过,乡下人一年到头统共唱不足十场,哪里需要订戏服。树仁却觉得并不是毫无希望,说:“这里既不用铺不用租,日复一日,慢慢地卖,总会有所收获。”陈斗升仍是摇头,说:“做了一辈子戏服,只明白一点,这个行当发不了财。”
一个院子里三间房,左侧的土坯砖房是翠凤夫妇住着的。用纸糊住的四方窗,总映着她细眉细目的侧影。翠凤闲时便做些绣活,金丝、银线舍不得用,只能用简单的彩线绣个金鱼、绣只蝴蝶。锦汉眼看着一天天长起来了,浑身上下都是绣花衣服,裤脚上一只五彩斑斓的虎头,看着格外精神。连徐宁都对着他拍手,说:“你看你姑姑,把你打扮得像有钱少爷了。”
翠凤把心思全放在锦汉的衣服上,变着法儿绣花样,除了喜庆的兔头、虎头,还有整幅的云鹤图,看着十分贵气。陈斗升心疼物料,说:“太费事了。”看着孙子打扮贵气,心里也是欢喜的。
树仁与翠凤日夜忙碌着,筹划着将摊档开起来。一部分是从汉记带出来的存货,还有便是翠凤近来的出品。又想办法请人收了两台旧的缝纫机。翠凤极力劝服黄柳,先是教他做剪裁——不料,黄柳虽有绘画基础,于此却极难上手,仿佛在布上画便不是画似的,翠凤只好教他踩缝纫机。没想到这个活上手倒快,没几天他便将缝纫机踩得隆隆响。于是家里三个人分工合作,做了一些简单的布袋、婴儿襁褓。
这摊档就摆在小院的门口,几块砖头摞起来,上面搭一块旧床板,便能摆卖了。虽然简陋,却也方便展示,田头常有人经过,多少有些布料货物的需求。这样经历了几回,倒也赚了些钱,总算是有了些收入,不至于只靠种瓜果度日了。
陈斗升蹲在门口,一口口地抽水烟。他自嘲不是做手艺活的料:“老了,眼花了,丢了的手艺捡不回了。”偶尔望天长叹:“好不容易将汉记经营成大铺头,如今又回到我阿爸那时的样子,再过几年,怕是要上人家的门当学徒了。”陈师母好言安慰,说:“你平时不是常说,有黄金万贯,不如一技傍身,只要一家人齐整,做手艺活有什么不好?”树仁能体会到父亲的郁闷之情,却不知如何安慰,他向来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日日的不是做缝纫,便是守摊档。
这用硬纸板糊着“汉记”的小档口,坚持着开了下去。每天由树仁守几个钟头,换翠凤守着;中午翠凤去做午饭,又是他顶上。终日守着,生意却不见得好,乡下人习惯了简朴,家中衣物大多是自己缝制的。档铺摆了数月,生意额少得可怜,连以前汉记一个月的零头都没有。翠凤便有些灰心,说:“如此苦耗着,还不如养鸡呢。”树仁于毅力上向来胜于妹妹,坚定地说:“既然决定开了,便要坚持开下去。”
这一日,正是树仁守在摊档前,百无聊赖,时而望着远处青翠的竹林,时而回神盯着档口,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慢慢走近。树仁惊讶不已,看了好半天,才确定地叫:“笙哥!”
黎宝笙穿一身粗筒长袍,全身上下都是极灰的颜色,只有仔细看,才能看到袖子里藏着一串晶莹剔透的红珊瑚手钏。黎宝笙拉着树仁,一副故友久别重逢的样子,激动地说:“没想到真是你们!”
原来,几个有名的粤剧团在怀集、梧州一带盘桓许久,终于还是没有方向,各自散了。剧团里的演员,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回了老家。黎宝笙不愿意再奔波,便辗转落到了广宁。
黎宝笙立刻请了树仁去认门,说自己租了一处很好的住所。那房子是个石砖围成的大院,房屋上有彩色的花鸟灰塑,大概过去是官家住的,显得气派非凡。再好的房子,在战争年代也是残旧缺修,树仁随黎宝笙进了门,只见三间灰砖小屋摆成品字,地方宽敞,但摆设不多,显得有点凋落。
黎宝笙热情地向树仁介绍:“找了许久才租了这间,是村子里最好的……”又略顿了顿,显得意犹未尽,说:“一直在老广州城居住,偶尔换换环境,倒很有新鲜感。”他越这么说着,越显得不淡定。树仁不知为何,突然颇能体会他的心情,友好地笑笑,说:“没想到我们离得这样近,今后要常去我们家啊。”
从此,黎宝笙几乎每日都到档口坐坐,或与陈斗升一道抽着水烟闲聊,或陪着树仁守档,甚至饶有兴致地看翠凤做绣活。看着一幅幅鲜艳的绣样,他像久饿的老虎见了肉,满眼里是发馋的光。陈斗升看出了他的心思,忙摆手说:“做戏服太费丝线了,这些都是用作小孩衣物的。”
黎宝笙的出现提醒了树仁。他们本来是做戏服出身,以精工见长,如今却是做着简单的缝作。汉记累积了十几年的制衣经验,便要从此湮灭了吗?想想那苦心经营的老招牌,当然十分不舍。战乱时期,物料珍贵,便是用来教授黄柳的用料,亦是能省就省,更不用想花大量物料去做一件衣服了。树仁只好按捺住心中的愿望,用心兜售档口的小商品。
这困顿之际,孩子便是唯一的希望。锦汉像是农田里长势良好的作物,一日日见风而长。他刚生下来便不怎么哭,后来更学会了笑,每日在陈师母怀里转动着眼睛,看到新鲜画面便咯咯地笑。一岁以后,虽还不太会说话,却走得很勇猛,常常一个人顺着墙角,踉踉跄跄地蹭到大门口,看父亲摆档。树仁一边守着档口,一边翻看戏服样本,给锦汉指着,一样样地认识。锦汉当戏服样本像公仔画一样,睁大了眼睛,看得入神。树仁又教他认识各种花纹水纹。说来也奇怪,锦汉于识字上不甚精通,于戏服却是不点自通。往往一看纹样,未等树仁说明,已咿呀作声。树仁十分高兴,忍不住对太太说:“我们家锦汉,将来说不定比他姑姑还要会呢。”不料徐宁立刻泼冷水,说:“就一份吃不饱、穿不暖的手艺活,有什么好高兴的?那戏服远远看着金啊银啊,说到底都是假的!”树仁听她说得有理,不知如何反驳,只得长叹一声。
生活虽然穷苦,却是一天天勉力维持着,靠着辛勤刻苦,总算维持着一家齐整。转眼又是新年,眼看着一家人平安齐整,陈师母甚感安慰,一面敲着发痛的腰,一面说:“一家人齐整就好,日子过得这么平安,真应该多谢菩萨保佑。”树仁忙点头说是,嘱咐妹妹年末之前多省点,好歹留着过年的花费。翠凤说明白,每日在窗下做绣活的时间更长了。只有徐宁一蹶不振,徐家回连州后便没有任何消息,她想尽办法打听,却始终打听不到。
这一年的春节,虽是在抗战时期,还是保持着相对的安乐。陈斗升带着全家大年初一去陈家祠堂烧香,给表叔公等本家亲戚拜年,将存储已久的银钱换了米和麻油,送给族里的长辈。
年初七是人日,族里众多叔伯父几次商量,决定凑足演员唱一天酬神戏。镇上已驻扎不少日本兵,但很少到村里来。陈姓人在人日这天请大戏已是多年传统了。汉记档口决定从年初一休到初七,陈斗升便让年轻人去看戏,说看看乡里的戏服做工如何,有机会与领班、正旦打个招呼,说不定能揽到生意。
乡班给乡亲们唱的这台戏是《帝女花》。这也是省城大班向来爱挑的大戏,其中人物众多,情节紧凑,演到高潮处,总有痴男怨女为之感动,哭得稀里哗啦。过去村里常常将这折子戏唱个大半,从早上唱到晚上。如今为条件所限,只唱一场,便只唱最催人落泪的一场《香夭》。
乡下条件简陋,高胡、二弦、扬琴、箫、笛一一摆开,乐器上算是凑齐了。锣鼓一响,那久已荒废的戏台便聚集了许多人。长平公主穿一件湖青色的穿云锦绣小宫装,下配棕色长摆镶金宽边襦裙。她身材敦实,动作却很灵活,上了戏装之后,凤眼微泡、眼风频送,还算活泼美丽。乡下开戏向来是图个热闹,只见这公主像只蝴蝶一样飞来飞去,一头错落有致的珠翠随风摇摆,风姿绰约,台下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省城里的长平公主,随着剧情转换,能换好几套衣服,飞袖、细袖、水袖各有讲究,凤帔也随之更换相配衬。到了乡下便是一衣到底了,这姑娘自始至终都拉着一对长长的水袖,一到要紧处便抓着乱甩。
树仁拼命挤到台前,试图找到领班,却看到黎宝笙站在台下第一排,夹在拥挤的人群中,抬头看着眼都不眨。他看到此景,莫名有一种心酸感,忙挤过去,笑着说:“这乡戏就是凑个热闹,笙哥您要是在这里开唱,一亮相便是镇住了场。”
黎宝笙略微得意地笑,却摇摇头,说:“我隐名埋姓躲在这里,本来就是走难的,要想出名,早就跟着他们到大后方去了。”
树仁虽不爱看戏,但为了戏服生意,一直在台前待到戏散,直到太阳下山,风吹着戏台一阵阵地冷。正如陈斗升所说的,乡下人俭省,不会花大价钱做好戏服的。那乡戏领班想也不想就拒绝了树仁,只好作罢。
不料第二天,黎宝笙一大早,便来敲陈家的门。见开门的是树仁,立刻拉着他的手,说:“走,到我家去,有人急着找你。”
树仁随黎宝笙去了他的乡下大屋,一进门就吓住了。屋子里有个抱孩子的妇人,一眼便能认出是于莺莺。
于莺莺此时身材臃肿,动作缓慢,头上包着个头布,怀里抱着个婴孩。那孩子白白嫩嫩的,是个小肉包形状,十分可爱。
黎宝笙长叹一声,说:“上次你来,不敢让你看到,才生完没两个月。”
树仁原先想不到是怎么样一个情景,一时倒不知怎么反应了。于莺莺见到他两眼放光,冲上来,摇着他说:“这不是陈家老板仔吗?笙哥请你来给我做衫?”说着便笑起来,又冲向房间,边跑边说:“现在的尺寸不准,你照先前的尺寸做。”
黎宝笙望着她的背影直摇头,说:“带了孩子一阵时日,整个人都有些痴痴呆呆的。昨日她听说野台子有人唱戏,迷得差点要冲出去,我们为此吵了一架,好在看仔婆把她留住了。”
于莺莺从房间冲出来,手中拿着一张旧的尺寸表,树仁只好接了。她立刻又欢天喜地,说:“我要粉色的,就做个小宫装吧,不,一件梅香装就好!”孩子突然啊呜啊呜哭起来,看仔婆忙去抱,于莺莺也急着去看。
“她唱戏唱惯了,许久没登台,闷得难受。”黎宝笙请树仁帮忙,给她做一身新的戏服。于莺莺带着孩子不甚耐烦,没事就做个云手,走个碎步,过过瘾。请了个乡下妇人照顾,孩子在一旁嗷嗷啼哭,于莺莺自己哼着小调,在客厅中自顾演着上香拜月,步步生莲。
档口开了半年,慢慢地有了名声。树仁请了一个会木工的村人,帮忙搭起了个杉木棚子,四方周正,算是能挡风挡雨,比之一块床板搭起的档口又好看了许多。棚子上方有了一个木板,上边用毛笔写着“汉记”两个大字,挂在用杉木板做成的门楣底下。档口主要卖翠凤手做的一些孩子的鞋袜,还有一些布艺制品。这成了乡下的一件大事,引人围观,特别是乡下的孩子,盯着绣品好奇地张望,或围着棚子转圈玩。摊子的角落里摆着戏服货版,锦绣华丽,安静地散发着光芒。
除了做小孩的鞋袜、襁褓,翠凤又开发了些精细绣品,如带绣艺的挎包、布袋,慢慢地引来了一些年轻姑娘驻足,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生意虽有,盈利却是困难。乡下人向来平实简朴,于衣服上的需求量不大,且大都是自己缝制。汉记的做工虽然精致,可精致当不了饭吃,乡下妇人总是能杀价便杀价,到最后以很微薄的盈利卖出。那些用心制作、标价稍贵的精绣品,却是卖不出去,只有极少的爱美的姑娘,舍得把钱花在华丽的绣面上。
许多省城大户在广州周边的县市避难,偶尔还能回广州老宅看看,陈家亦是如此。开店需要物料添补,树仁便有些跃跃欲试。不料正要走,又听说广州城再次遭轰炸,状元坊附近也不能幸免,许多铺头都被炸得七零八落。陈斗升收到消息,一直坚持经营的荣记,被炸个正着,荣记的老板兼伙计,十几个人一齐在房子里被炸死了。
陈斗升听说这消息后,先是吓得变了脸色,接着闷声不吭地坐在门口,连着抽了几袋烟。他虽恨过赖荣,还咒过赖荣早死,可听到这样的消息,还是难过的。荣记的出品有他自己的特色,于绒绣、盘绣上十分擅长。想到此,他更是难过,让树仁买了一瓶乡下自酿米酒回来,自己一个人喝了,喝到酩酊大醉。
又过了一段时间,树仁见物料已经见底,便果断提出要回去取。陈斗升坚决不允许,说:“要回也是我回。”
此时的陈斗升,看上去俨然是六七十的糟老头了。精瘦的脸更不见肉了,黑黄的皮色皱得像橘皮一样。身子依然硬朗,却是喜欢弓着背,微缩着头,仿佛时刻要跟人讨价还价似的。他很久没过问汉记的营生了,关键时刻,却振奋了精神,严肃地说:“我已经是半辈子的人了,就算万一大吉利是了,无非是不能陪你阿妈到最后。你是后生人,孩子才丁点儿大,你若出了事,老婆孩子怎么办!”
树仁心想自己身强力壮,要是遇上空袭,总跑得比父亲快些。这话是不能说出来的,他只好生硬地说:“要去我去,你去我们都不放心!”
两人争执不下,其他人更无法做主。这一趟远行充满了风险,谁去都是心疼。然而,生意既要开下去,箱子里的绣线、珠管便会越用越少,再不回去,物料缺乏,断了货,档口再开起来又是个难。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走不了。这天一早,陈斗升趁着天色微明,树仁还未起床,自己去村口拦了去省城的烧炭车,一个人走了。
陈师母早上醒来,看到他留的字条,急得立刻哭出来。树仁追到村头,早已不见了车子的踪影。
那几日,陈家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每个人都在煎熬中度日。陈师母每天必走到村头榕树下,站一整天张望。树仁、翠凤亦是十分担心,每天一早便在神台前烧香,祈求祖宗保佑父亲平安归来。
眼看着日头升又落,榕树头的村民聚了又散,省道上还是不见陈斗升的身影。陈师母默默地站了一日,眼里含着泪,说:“叫他不要去,偏要去,是钱要紧,还是命要紧!”树仁怕母亲又出问题,把档口关了,陪着母亲一起站在村头等。
这一天,已经是到了傍晚,几片浮云遮着夕阳,在榕树间洒下点点金光。只见在那略显阴暗的省道上,突然出现了一辆烧炭车,缓缓地在乡路上颠簸。到了榕树底下,车头喷出一股白气,像个喘息未定的恶兽似的。树仁闻到一股浓重的烧焦味,忍不住后退,好在车门突然打开,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车上下来了。
陈斗升摆着两件大行李,吃力地从车上跳下。看到树仁,他挥了挥手,笑容淡定,仿佛只是心情好时外出旅游一趟。未等他走近,陈师母便忍不住号啕大哭,树仁激动地冲上去,紧紧拉着父亲的手。
陈斗升这一趟回来,不仅带回了三箱丝线珠管,还带回来了一个年轻的姑娘。
那姑娘长得眉清目秀的,仔细看十分美丽,只是一身的衣服破破烂烂,俨然是个乞丐的样子。陈斗升闷不作声地抽了几口烟,说:“这是赖荣的妹妹小红。”他这次回去,本是趁着夜晚偷偷摸摸地潜入后院,想打开库房取物料了事的。不料一进后院便撞到了人,差点没被吓死。仔细审问,才发现原来是赖荣的妹妹小红。赖小红告诉他,当时一颗炮弹空投下来,正落在荣记的屋顶,顿时“轰隆”一声,连房子带人全没了。她是外出送货,恰好躲过了一劫,荣记里正在干活的十几个工人,没一个活着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流落,又不敢回老家,只好有一日是一日的,当流民在城里乱窜。白天靠捡拾垃圾为生,晚上躲在陈家宅子里睡觉。
一家人将陈斗升接回了家,均是眼角含泪。吃饭前先给祖先位上了香,感谢祖宗保佑。只有陈师母很不高兴,眼光总是不自主地落在赖小红身上。晚上安顿好小红睡了,才扯住陈斗升,态度厌恶地说:“眼下我们差点连饭都吃不饱了,你还领个姑娘回来,到底想打什么主意?”
陈斗升听了太太的话,简直哭笑不得。他自觉已是风烛残年,哪里还会对年轻姑娘打主意,无非是恰好遇着了,不想眼睁睁看着一条人命湮没于乱世。他望了望自己的一对儿女,淡淡地解释:“她一个大姑娘,躲在我们家后院,每天靠着在废墟里扒东西变卖为生,实在可怜。”
陈师母完全不接受这个解释,懊恼地说:“当年荣记怎么对我们,你都忘了吗?”
陈斗升略顿了顿,摇摇头,说:“事情过去了,很难再计较,赖荣也不在了。眼前这姑娘,孤零零一个人,我们不收留她,不知道明天会变怎样。”
树仁兄妹俩亦不希望收留赖小红,然而人已经来了,一时不忍心赶走。翠凤拿出自己的衣服,给她替换,说:“她一个小姑娘,总还是好养活。”
晚上,徐宁对树仁一通嘲笑,说:“你阿爸以前是很精明的,现在真是老了。虽然是特殊时期,有钱人都趁机讨小老婆,可你们家是什么身份!”
汉记的生意慢慢做开,在此地有了名声,远近邻居想要买精致布艺的,总是喜欢先到汉记转转。树仁待人耐心和气,翠凤心灵手巧。这一家人虽是暂时避难,却仿佛已经在此地生活了几辈子。
黎宝笙不时在村子里走动,最爱到祠堂边的戏台上走台步。乡里的戏台,当然不像大戏院般光鲜亮丽,粗糙的砖沿里夹着荒草,台上灰扑扑一片,许久没人打扫。黎宝笙倒不在乎,每日在上边练习着,有些乡下孩子好奇地围观,甚至打趣,以为他是个疯子。树仁偶尔经过,总会停下驻足。他虽不爱听戏,却爱看黎宝笙走台练功。黎宝笙每天在上边唱着,唱词都是一些“人生如朝露”“梦碎泣江山”。这戏文反而让树仁重生希望,他觉得战争总会过去,人总需要太平日子,不管世道如何艰难,只要黎宝笙还在唱着,翠凤还在绣着,那便不算彻底的绝望。
这一日,黎宝笙大概心情好,唱了许久都不停。树仁听他唱的是《隋唐演义》,瓦岗英雄征战归来,倒是很爱,一直听着痴了。从下午一直听到傍晚,直到太阳落山。
正是黄昏时分,戏台上一片黯淡的灰色,几点草影随着风四处摇荡。黎宝笙长叹一声,说:“我的大箱子托人带到乡下,现在也不知流落到哪里了。”
树仁便逗笑着说:“戏服是你的,总有一天会找回你。”黎宝笙长叹一声,默然不语。树仁亦是摸摸脑袋,想自己不会说话,不要多说了,惹他伤心。
到了晚上,又见黎宝笙急急地跑来。树仁吓了一跳,想自己有哪里得罪他了。黎宝笙从怀里掏出一只翡翠扳指,说:“我拿这个做抵押,你们能替我制一件新的宫装么?”
原来于莺莺对戏的情结又与黎宝笙不同,她是不化装不会上台的,平时躲在家里练习,一上台,不管下面是什么人,总要正正经经地开唱。有一日她突发奇想,说:“不是土地节快到了吗?村里要唱酬神戏的,我便在此地唱一场,算是答谢乡亲们对我的照顾。”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农历二月二是初春时节,春雨初下,万物生长,乡下很重视这个节日,也常有祭祀聚会活动。乡下祠堂已经开始忙碌,有妇人清洗地板,擦拭牌匾,落满了灰的戏台子也有人打扫了。
黎宝笙一听自然是不同意,夫妻俩为此争吵了几回。于莺莺犯了脾气,执意要唱。黎宝笙却觉得乱世之下,哪里还有花红柳绿的舞台。然而吵也吵了,骂也骂了,夫妻俩始终不得和解。
除此之外,于莺莺说要去秽气,不能穿过去的旧戏服。黎宝笙只好来求陈家。抗战时期纸币没有数,黎宝笙只好忍痛,用玉扳指来换一件新的。
陈家人一时不能答应,只能关了门慢慢商量。树仁能体会黎宝笙的苦心,想凭着自己的缝制技术,一件总是能做出来的。翠凤却极不愿意,说一件戏服要费多少彩线,这要做成小孩衣物,总够十件八件的了。又细想了想,仍是摇头,说:“即使笙哥付得起钱,可我们是打开门来做生意的,总不能三天两头地告诉别人,货没有了。”
陈家打定了主意,便这样告诉了黎宝笙。然而于莺莺是个任性的脾气,说了做便一定要做的。黎宝笙只好去找乡长,将此事说了。乡长对于黎宝笙一家的事是帮忙隐瞒的,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抛头露面。黎宝笙只好感慨:“我也不知道自己娶了个不唱戏便要死的老婆。”
乡长再三犹豫,终于还是答应了。二月十九是观音诞,也是大节,到时一定给于莺莺唱一场。
这样决定下来,翠凤也无可推托了,从带来的衣箱里凑齐了布料,就此裁剪、绣制。短短时间内,自然无法做得很繁复,只得画了个简单的样式,绣了金凤、萱草,件料上减了些,却是用平常难得用的轻纱补足。又在身上多做了几根飘带,显得飘飘欲仙,别具一格。
观音诞这天,许多乡邻都到庙里祭神,也到祠堂烧香,祭完了便挤到旁边的戏台听戏。于莺莺唱的是《鱼篮观音》,用的是乡里的乐队。开场时箫声悠扬、琴声清越,她“咿呀”一声,从戏台左侧款款走出,衣袂飘飘,仿佛瑶台仙子从天而降。那戏服虽然简单,却是脱尘飘逸,正合了观音的化身之态,凝神处,一步三叹,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黎宝笙也看得赏心悦目,忍不住对树仁说:“你们为她赶制的这套,比她以前穿过的所有剧装都好。她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在乡班上唱,然而,十分好,唱得好,舞得也好。”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树仁眼见戏台上的戏服如此惊艳,觉得很欣慰,只是想到翠凤这几日都熬到半夜才睡,又隐隐有些心酸。
于莺莺果然是许久没上台了,不但唱得用心,表演亦一丝不苟。乡下人罕见听到这样好的声音,喝彩声不断,闹腾得越来越响。到高潮处,琴声急促、鼓钹齐鸣,于莺莺的身子震动了一下,口中唱词亦顿了顿,仿佛被这壮烈的情绪感染了,无法自持,眼角一滴眼泪缓缓掉下。黎宝笙站在台下,也发现了这细微的变化。他原本欢笑的脸色变得凝重,一时若有所思,又望了望旁边的树仁,不动声色地抹了抹眼睛,低头说了一句:“我很感激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