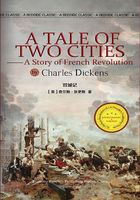自1914年以来我们听到许多有关威胁文明的东西的议论。首先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然后是普遍的德国人;然后是战争的延续;然后过一阵是凡尔赛条约;然后是法兰西军国主义——一直伴随这些的还有这么些较小的威胁,如美国的禁酒法[1],诺思克利夫子爵[2],尼布赖恩先生[3],康姆斯托克[4]思潮,等等。
文明,无论如何,已经对这些敌人联合起来的进攻进行了异常出色的抵抗。因为,在1923年,它依然屹立在离九年前“洪水还没有泛滥的那个伟大的时代”[5]所站立的地方不很远。倘若一头为尼安德特人[6],另一头为雅典,就如此这般的距离来衡量,那时它确切地站在什么地方,倒是一个各人根据自己的感受会做出不同回答的问题。重要的是,对我们文明的这些威胁——包括历史上我们所知的最大的战争和最愚蠢的和平——直到如今在大多数地区还是局限于仅仅是威胁,不过如此而已,与其说它真的咬人,不如说它叫得凶。
不,我们的文明所面临的危险,其更为严重的还不是外在的这些——狂人啦,战争啦,以及战争所造成的破产。最令人惊惶的是从内部威胁它的,是威胁当代人的精神的,而不是威胁当代人的肉体和财产的危险。
在现代文明的内部,通过自我陶醉过程而孕育出来的不同毒品中,照我看,极少比在技术上被认为是“娱乐”这种古怪而吓人的东西更致命的了(同时在表面上却显得没有什么比它更无害)。“娱乐”(我打上引号以表示我指的是非真正的娱乐而是被正式认为具有同一名称的有组织活动)——这个词产生的是什么样的梦魇式的幻景啊!像每个有头脑和感情的人一样,我讨厌工作,但我宁愿一天八小时给放在政府机关的办公室里而不愿给人责备过“娱乐”生活;我甚至宁愿,我认为,一年写一百万字的新闻稿件。
现代“娱乐”的可怕,是由于种种有组织的消闲每每愈来愈流于愚蠢。从前有个时候人们迷上需要使用一定智力的消遣。在十七世纪,比方说,王室人员与朝臣对听渊博的讲道和神学以及形而上学的问题的辩论感到真正的乐趣(比如堂恩博士[7]的讲道)。在巴拉丁[8]王子与詹姆士一世[9]的女儿的婚礼期间,招待来宾的部分娱乐是一场和蔼可亲的掌玺大臣威廉斯与一群剑桥大学的逻辑学家进行的三段论法的辩论,我忘记是什么哲学主题的。想想倘若一所忠于王室的大学打算给他相似的招待,一位当代的王子会有什么感觉吧。
欣赏智力乐趣的不单是王室成员。在伊丽莎白时代,具有普通文化的每位绅士淑女,你可以相信,一经请求,都能来一首小曲或圣歌。那些知道十六世纪音乐高度复杂微妙性质的人会明白这意味什么。要对他们偏爱的消遣入迷,我们的祖先得耗费他的精神,达到非比寻常的程度。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俗人也对需要花费一定的智力,发挥个性和个人的积极主动精神的娱乐感到兴趣。他们听戏,如《奥赛罗》、《李尔王》、《哈姆雷特》——显然既含有欣赏也含有理解在内。远在偏僻的乡村地区,农民年复一年地举行传统的仪式,春夏的舞蹈,冬天的假面哑剧,秋天庆丰收的典礼——种种适合于每个相继递嬗的季节的活动。他们的乐事是智力上的也是生气勃勃的,他们自己想办法来自娱。
我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代替过去需要智力与个人积极性的娱乐,我们现在有了足够多的单位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消遣——不要求娱乐者任何个人的参与和智能方面的努力。对世界上几十亿民众,一百万座电影院给他们带来听厌了的废话。总是有第四流的作家和戏剧家;但他们的作品,在过去,没有越出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与国境就迅速消亡了。今天,电影剧作者的作品从洛杉矶传播到全世界。数不清的观众消极被动地沉浸在废话温水浴里。对他们不要求付出智力,也没有参与;他们只要坐着把眼睛睁开就行。
是不是民众需要音乐呢?在旧时代他们自己创作,如今他们只要把留声机打开,或者说倘若他更现代化一点,则他们可以把无线电话调到适当的波长,聆听马可尼剧场圆润的女低音歌唱《拾穗者的催眠曲》。
如果他需要文学,那有出版社。名义上,出版社的存在是为了提供信息,这不假。然而它的真正功用,像电影院一样,是提供消遣,让读者的精神有所安顿而不要求他花一点精力思考劳神。这一功用,必须承认,它格外成功地达到了。人们可以多年来在每个工作日阅读两种报纸,星期天一种报纸,除转动眼睛外,一次也不用动脑筋思考,可以随随便便地一栏一栏地读下去。
社会的某些部门仍旧靠一些要求个人参加的体育运动,大量的高等与中等阶级的人士亲自打高尔夫球或网球,如果他们够富有的话,则去打鸟、猎狐或上阿尔卑斯山滑雪。但在社会上广大的群众甚至对体育运动也采用代替的方式,他们愿意看球而不愿感受亲自下场的疲累和危险。所有的阶级还跳舞,这不假,可是全世界都按同一步法、同一曲调去跳。跳舞已经严格地使任何地方的色彩和个性不起作用了。
这些不花力气的乐事,这些现成的消遣,它们在整个西方,世界的表面,对每个人都是千篇一律的,肯定是一种比德国人对我们的文明更可怕的威胁。一天的工作时间,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被毋须花脑筋,没有个性,没有个人创造的纯机械性的任务所占据。如今,在闲暇的时间内,我们去寻求像我们的工作一样机械刻板、不要求有多少创造性的消遣。这样的闲暇加上这样的工作,总数等于一天,到头来这就是有福地松一口气。
按这种方式,自己让自己中毒,文明看样子好像会容易陷入未老先衰。由于缺乏使用而几乎萎缩的头脑,它不能娱乐自身,对外界提供的现成的消遣逐渐感到如此厌倦冷漠,结果除以日益增加的暴力和粗野作为最恶劣的刺激物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推动它,存这种头脑的未来的民众,将会对长期而要命的烦闷感到厌恶。那就会走罗马人走的道路。恰好像今天我们做的一样,罗马人最后终于丧失自娱的能力;像我们一样,罗马人靠现成的他们没有参与的娱乐而活。他们极度的烦闷不断要求有更多的职业格斗士,更多的走钢索的大象,更多的从远方运来的珍禽异兽以供杀戮。我们要求的也不会少,但由于存在一些理想主义者,不会得到所要求的一切。形式最为暴烈的娱乐只能非法得到,要满足杀戮与残忍的口味只好成为三K党成员。不管怎样,让我们别绝望。我们也许能活着看到血流马戏表演场。大声嚷嚷地要求减轻烦闷压力的势力对理想主义者可能证明是他们对付不了的。
注释
[1]美国禁酒法,1920至1923年间执行,但由于私酒猖獗,收效甚微。
[2]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第一代诺思克利夫子爵(1865-1922),英国报业大王,《每日邮报》的创立者,对英国当时的舆论影响甚大。
[3]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60-1925),美国律师,曾任国务卿,思想顽固保守,反对达尔文主义,曾对在课堂进行进化论教学的田纳西州教师约翰·斯科普斯加以迫害,引起公愤,本人亦身败名裂。
[4]安东尼·康姆斯托克(1844-1915),美国社会改革家,走向极端,主张禁止一切人体艺术。
[5]本文作于1923年,九年前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里的洪水指这次史无前例的大战。
[6]一种史前人类,生活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因其化石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谷而得名。
[7]约翰·堂恩(1571/1572-1631),英国神学家与诗人。
[8]巴拉丁为神圣罗马帝国属下的一个小邦。
[9]詹姆士一世(1566-1625),继伊丽莎白一世后的英国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