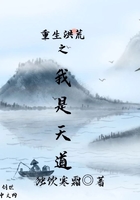从此处一直往前走,大约四分钟,街道的尽头以一堵墙的形状将你拒绝。城堡式的庭院错落在幽暗的夤夜里。退出街道,是一条更宽更长的街道。更宽更长的街道外,是一条还要宽还要长的街道,它们像彼此放大或缩小的水泥带子存在于稀疏的脚步声中,有人摔了一跤。
昏睡的街道阒无声迹,呻吟的跌倒者扶住墙壁,摔跤擦破了手掌上的一块皮,她感觉到自己出血了,把手放在嘴边,舌头含一下伤处,将脏兮兮的细泥吐掉,拐进了曲折的街道。
这是一家医院,漆黑的夜里,她消失了。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她躺在草地上,手上的伤处已不再出血。她长着精致的五官,肮脏使她的美貌大打折扣。晨起锻炼的病人走过来,围在草地上的美人旁边。过了一会儿,医护人员也来了,和病人们一样,他们并不认识草地上的美人。她发梢上有水珠和草叶,穿着白色的宽大裙子,倒下的姿势如同仰泳。这时阳光已挂在一片樟树叶上,少华在五楼走廊上出现了,凭栏相望,他看见了草地上的这一幕,下了楼。
少华经过回廊时,侧身朝地盂吐出醒后的第一口痰,他看见草地上的人群漏出了一条缝隙,一老一少两名担架工朝自己站着的方向走来。
“真倒霉,一大清早就要搬死人。”年轻的担架工道。
“人死难道还要分时辰?”年长的担架工用训斥的口吻道。
少华没听见这些对话,用目光迎接着正在靠近的担架。
“凭什么让我来搬死人,凭什么我干这差事?”年轻的担架工道。
“这差事多好,让人知道该怎么好好去活。”年长的担架工道。
“恶心,”年轻的担架工道,“除了恶心什么也没有。”
“人就是一件衣裳,用完了扔掉。”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人活着就是用来证明时间,世上任何东西都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证明时间的存在。你看这姑娘不过活了二十多岁,可就能证明世上曾有过这二十多年。”
“那样的话,只要有一个跟她年龄相同的人活过就行了,何必要有那么多人存在?”
“时间是个贪婪的加法,需要很多很多陪葬品。”
“你这样说,人岂不是很可怜?”
“所以活着的时候更要好好过。”
两个担架工从少华身边走了过去,少华看清了担架上头发凌乱的美人。她已经死了,少华跟在担架工后面,门廊敞开着,后院栽满了枝秆纤细的向日葵,黄色的花瓣烘托着圆形花盘,像一个个大头少年夹道而立。笔直的小径终点,是一座孤单的灰色小楼,担架工正往那里去。少华心里很不舒服,一大早遇上这种事的确是有点晦气,少华嗅到了向日葵散发出来的淡淡苦味,心想该回病房去了。抬腕看了看表,吃早餐的时间刚过。他返身踏上台阶,回到楼上的病房。
早餐一如既往,单调、乏味却可以维持营养的均衡。少华三下两下就把两只馒头、一碗菜粥外加一块煎蛋吃完了。他拿起了晨报,外部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种规范或规范外的事件。他对这一切并不感兴趣,不过他还是知道美国刚换了总统,知道中东格局发生了巨变,知道金三角的大毒枭已被击毙,知道好莱坞层出不穷的桃色新闻,想到自己知道的还真不少呢,就咽下了最后一片蛋皮,似笑非笑地动了动嘴角。
晨报头版,比较显眼的消息是一种叫“我爱你”的病毒大肆侵入电脑,使全球金融信息业损失惨重。少华把报纸翻到社会综合版,一则寻人启事使他一愣:“安波,女,26岁。身高1.67米,波浪型卷发,脸廓瘦长,大眼睛,右眉间有一痣,爱穿宽大衣裙,知其下落者,请拨打电话6974526,联系人楼夷。面酬。”
启事旁还附有肖像——一张五官秀丽的女人面孔。
少华之所以惊奇,是因为报纸上的肖像并非别人,而像是方才担架上的那个美人。少华是个漠不关心的人,他的注意力对外界很麻木。可这一次有点不同,人终归是要有一点好奇心的,少华忽然觉得有必要探究一下这件事,他的这个决定可说是人之常情,也可说对世事的冷漠并不彻底,于是在这一瞬间,人潜在的猎奇本能被唤醒了。
少华站起来,走到窗边。落地的长帷幔遮住了一部分摇晃的阳光,少华的眼睛起来,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见那座著名的电视塔。少华望了一会儿,或者,只是站了一会儿。早餐令肚子胀鼓鼓的,他需要消化一下。他眉头紧锁的样子像是在用来下定决心,他好久没能为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来一次哪怕是小小的冲动了,这确实是一次例外,他转过身迈出了病房。
少华下了楼,从敞开的门廊进入后院,夹道而立的向日葵延伸出一条两米宽的小径,少华知道那个美人就在那栋孤独的灰色小楼里。他脚步迟疑了一下,接下来便不再犹豫,走进了楼中。沙子般的灯光弥漫在充满腐败气味的房子里,少华的胸膛不适应地阻塞起来,目光也同时很不适应。室内虽然有灯,仍显得昏暗。他辨认了一下,几具遗体被随意搁置着,他禁不住回抽了一口冷气,在他脚下,正是那个香消玉殒的美人。少华蹲了下来,仰卧在担架上的美人是那么年轻,她凌乱的波浪型卷发盖住了瘦长的脸廓,使少华看不真切,而要证实她是否晨报启事上所寻的那个女人,只须轻轻撩开她头发,看看右眉间是否有那颗痣。少华的手慢慢抬起来,指尖伸向美人的额头,把她的头发从面门分离开来,他看见了那颗隐在右眉间的痣。他想就是她了,尝试着又去撩了一下美人的发梢,手掌上有一种奇怪的飘逝感。少华忽然害怕起来,觉得手里的接触一丝分量也没有,面前只是一个画在纸上的人,顿时魂飞魄散,跳起来朝外跑,他像被一阵风刮出了小屋,恐怖使脸上的每一块肌肉夸张地聚在一起,许多人听到了少华的大声尖叫,然后看见他抱着头冲出了门廊,他确实被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