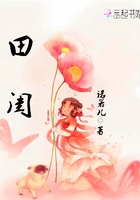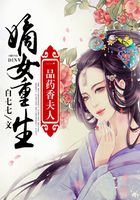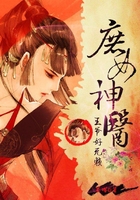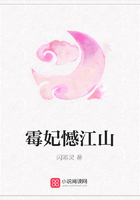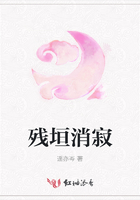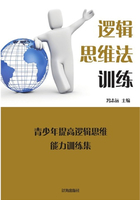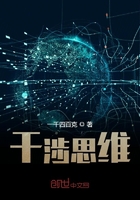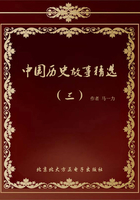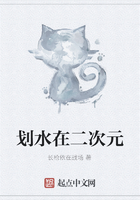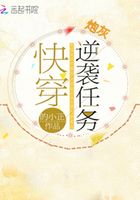亥时,两岸边的山野一片寂静,只听得到那偶尔的几声蛙鸣声。
“哈哈,咱们俩这样,颇有驾一叶扁舟,遨游仙境的感觉呀!”沈彧青笑着席地而坐在甲板上,侧过头对一旁的凌梅子说道。
“嗯,你这么一提,好像的确颇有这番意味哦!”凌梅子一边拉紧了披在肩上的锦袍,一边说道。
夜深了,有些微凉。
群山环抱着江水虚无缥缈,若隐若现,置身其间,让人心旷神怡,遐想连连。
蒙蒙迷雾中,一切是那么不可捉摸,一切又都是那么耐人寻味;万籁俱寂,只偶尔从远远的江水另一端传来一阵悠长而尖厉的气笛声,划破这令人窒息的寂静的夜空,更是增添了无穷的宁静。
幽幽江水,在习习秋风中,在江对岸的灯光还是头顶的点点星光的映照下泛起粼粼波光,好一派静谧的秋夜图。凉风令每一根神经都感受到不可言喻的抚慰。
静静地仰卧于冰凉的鹅卵石上,畅想那无边而神秘的故事。月亮在蒙蒙迷雾的遮掩下躲躲闪闪,散发出清丽的光,泻在江面,让人神情恍惚,仿佛置身于仙境,象是神仙躺于轻柔的云层,在江风的吹拂中游弋。
凌梅子闭了眼,放空自己的思想,悄然聆听大自然沉默的韵律,陶醉于这一片宁静。
漠然,凌梅子心中激灵灵一阵震颤,怕那宁静的一江清水,会猛的发怒扑卷而来,吞噬了她的躯壳,那松懈而驰的神经顿感惊悸,心里一阵莫名的恐慌。
她睁开了眼,那一江清水仍静静地悄悄地流淌,再远处,几个隐隐的黑点在缓缓地移动,是真实还是幻觉?只感到脑子里一片空虚和迷惘。
水上夜总会这时也悄无声息,这难得的宁静,赶走了周身劳顿疲惫。
“梅子?你在想什么呢?”沈彧青刚欣赏完四周的景色,回头时发现凌梅子正在盘坐,紧闭双眼,不知在想些什么。
“啊?我没有在想什么,只是放空自己,去感受着空旷宁静的夏夜。”凌梅子看着沈彧青说道。
“哦……我还以为你在思考什么问题呢。的确,这样宁静的夜晚也是十分少有的。”沈彧青看了一眼凌梅子,又转头看了看对岸的景色,欣然的说道。
“梅子,你可知前朝的陶渊明吗?”沈彧青向凌梅子问道。
“知道啊,风郢师父可喜欢他了,整日无论去到那儿都要揣着他的那本《陶渊明集》!”凌梅子摆弄着裥裙嘟囔道。
“哦?”沈彧青疑问道。
“是呀,我还能骗你不成?!”凌梅子一脸认真的看着沈彧青说道。
“那你应该也跟着风郢大哥看了不少关于陶渊明的诗文集吧?你觉得他如何?”沈彧青紧接着问道。
“我觉得……他除了有些憨憨的显得有点笨之外,其他的都挺好的。其实吧……陶渊明是个大智若愚之人!陶渊明是个赤子,我是这么认为的!”凌梅子抬头望着远方的天空,望着那没有尽头的黑夜,仿佛在回忆着些什么似的。
“哦?是吗?何以见得?说来听听。”沈彧青故意引着凌梅子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想听么?”凌梅子转头看坐在一旁的沈彧青问道。
“想,想听听梅子的看法。”沈彧青一脸正经的说道。
“那好吧……我便随便说说自己对陶渊明的看法吧。”凌梅子小声的说道。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赤子之心是最纯洁的,它剔除私心杂念,远离欲望纷争,只容纳人间最美好、最真挚的感情,所以“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赤子的现实生活也许境遇不佳、缺少知音,身边的世界让他孤独;但人类最纯洁最美好的感情与思想,是相通而永存的,普天下的赤子都将成为他的知音和朋友。就是这些心灵的朋友和美好的情感,成为赤子创造的博大宽广的精神世界。这里的“赤子”,放在陶渊明的身上,出奇的契合。
陶渊明是个孤独的赤子,但他并不害怕不害怕孤独,相反,他很享受孤独,他在孤独中去创造、去体会世界,他在孤独中创造了宁静、质朴、纯粹的田园诗
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那东篱下的那一簇菊花、南山间的一只飞鸟、田野间的草木虫鱼或是一阵清风,都是他心灵间最亲近、真挚的朋友。在混乱的东晋时期,陶渊明必须要做时代给他抛下纷的一个选择题,即社会与个人生命之间的选择,这一个选择题,他用了一生来思考和选择。
公元365年,浔阳郡柴桑县的东晋大司马陶侃的孙子家降生了一个新娃娃,陶侃的孙子给这个大胖小子取了个名叫渊明,取字为潜。此时,到了这一代,这个曾靠着武功擅世的陶氏大士族已经逐渐走向没落,且陶渊明并不是陶侃的嫡系子孙,所以,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生活尽管贫困,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陶家留下的一点田地产业还是能勉强支撑起全家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不幸的是,陶渊明八岁,父亲去世,十二岁时,庶母去世,《祭妹文》中“慈妣早世,我年二六”,接二连三的意外让他家的境况雪上加霜。陶渊明的少年时代,家道衰落更加明显,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少而贫苦”,《自祭文》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这些诗文记录了他年少时贫苦的生活。
矛盾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纵观陶渊明的一生,他所做的选择都离不开一个矛盾——社会与个人生命之间的矛盾。他从小受曾祖父、母亲和外祖父孟嘉影响很大,他不仅学道家《老子》《庄子》、学儒家《六经》,而且对《史记》或是其他文学、史学著作也有过深入的学习,这些儒家、道家经典,史学、文学著做,极大的丰富了陶渊明的学识和内心。儒家经典的入世思想教他要有所作为,从而有了《杂诗》中大济苍生的梦想“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道家文化的出世思想教他有所不为,从而有了“击壤自欢”的态度,这些相互矛盾的哲理让他在人生的道路的选择上有所踌躇和迷惘,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徘徊彳亍在寂寥又悠长的雨巷里转圈圈,幸运的是,他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方向,那便是他的赤子之心。
陶渊明热爱自然,这是他赤子之心的源泉。他从小生活在邻近长江、鄱阳湖、庐山的浔阳柴桑的乡村里长大,每天目之所及皆是绿草蓝天碧水红霞,耳畔常绕着清风蝉鸣、鸟啼狗吠声,身体所触之处皆为山水田园、禾苗稻叶。在这样一种美如画卷的环境里,陶渊明自然而然的就融入了其中,并与其完美的融合了起来。
同时,老、庄的经典有着许多崇尚自然的隽语,《诗经》、《楚辞》中蕴藏着许多由语言描写的关于自然的唯美画面,让他更加的深爱着自然之美。《归园田居》中他说道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并给自己取了一个“五柳先生”的别号,这样的他,着实可爱。
二十岁时,陶渊明结了婚,但他的第一个妻子不久后就去世了,从他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可以了解。不久之后,他续娶翟氏,翟氏很贤惠,“能安勤苦”,后来陪他度过了较长的一段躬耕岁月。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陶渊明初为人父,这在封建时代是颇为看重的大事。于是他在《命子》诗的开头就说:“悠悠我租,爱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想以陶家历代的光辉事迹来激励后代,奋发有为,光宗耀祖。此时的陶渊明,还未开始入世,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思想对他产生较大的影响。他为父后,所需要的开支越来越多,家庭经济愈加拮据,所以,二十九岁时,他不得不出仕,谋个一官半职,补贴家用。此时世道混乱,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把握政权,恒玄也正在酝酿等待时机谋反。起初,陶渊明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但他做洲祭酒没多久,就“不堪吏职”辞职回家了,此次出仕的时间很短暂,不过几十天。
他辞职不久后,州里又召他去做主薄,被他辞谢了,这次辞官之后,他在家里安静的生活了六、七年。从这次出世大概可以看出,陶渊明性情刚直坦率,他的内心是属于田园的,是清新质朴、纯洁如水的,这决定了他必定会看不惯官场中那谄上骄下、故作飞为的种种黑暗现象,也无法融入其中,与其同流合污,他能做的只是转身离开,因为他是一个内心纯洁的、有自己的尊严与原则的赤子。除此之外,从此处还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跟随内心、富有判断力的独立之人,他对外部世界有着清晰的自我判断,这样的品质成就了他。社会上,他有自己的尊严和立场,思想上,批判吸收儒道佛的优质思想为自己所用,个人生命上,忠于内心,保持纯洁的赤子之心,剔除私心杂念,远离欲望纷争,只容纳人间最美好、真挚的情感。
公元400年左右,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处于白热化阶段,王恭反晋被杀,桓玄入江州阴谋谋反,孙恩农民起义,桓玄杀殷仲堪,入据荆州。浔阳在地理上位于荆州、江州扬州的中间,属于枢纽,身处浔阳的陶渊明清楚的感受到这其中的混乱给社会带来的伤害。此时,人间的疾苦又击起了他心中大济苍生的理想,鉴于他的外祖父孟嘉曾经做过桓温的长史,并且有所作为,使得他对桓玄也产生了一些幻想,所以他就去到了桓玄手下做事,想以己之力,或是改变社会乱象,或是为个人立功。从这儿可以看出,陶渊明并不是颓废的,也不是浑身静穆的,他有追求。可是,在荆州做官的日子里,他看到了桓玄的血腥与野心,看到了他们的不义与黑暗,陶渊明的率真正直的性格让他无法认同桓玄做法。此时,陶渊明奉桓玄之命出使京都建康(今南京市),完成使命后,返途中路过江西,准备顺道回家省亲,然而被风阻在途中,写了《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中有两句诗,表达了他对母亲、兄弟的思念,“归途漫漫行不止,计算日头盼家园。将奉慈母我欣欢,还喜能见兄弟面”,质朴、深沉的语言,包含了陶渊明赤子之心中最纯洁、真挚的感情,相对于黑暗的官场,他想转身离开,回归乡里“道桑麻”的真,回归家中亲情的暖。
不久之后,公元401年冬天,陶渊明母亲去世,他辞去了桓玄的官职,回到了家中,他的那一顆漂泊的心,在田园中得到了安定。在这一次出仕之后,他彻底的对当时的官场失去了期盼,他明白他大济苍生的理想能实现的机会十分渺茫,一己之力难挽狂澜,他兼济天下之心无处安放,只好回归田园独善其身,或许还能保留他一颗赤子之心,且说道:“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陶渊明心中潜藏的梦想的芽儿,沉寂了三年,在公元404年,被一阵春风再次吹醒,此时东晋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桓玄的暴虐无道遭到了各方势力的讨伐,此时,刘裕这位出身下层的军人以其颇有不平凡的作风,使得“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这样的人物让不甘心“四十无闻”的陶渊明,对刘裕抱有了幻想,刚好,刘裕也对他有些好感,一拍即合,他进入了刘裕的幕府。只是后来,陶渊明发现刘裕也是个滥杀滥伐的
人,死灰复燃的心再一次被一盆现实的冰水浇灭,他看清了这些政权阶级的争夺,都是同一类的黑暗。
这一年,他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用极为微妙曲折的语言,“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他说,我此番仕途行程岂不远?艰难跋涉千里有余啊,异乡风景已看倦,一心思念园田居,道出了他这次出仕后的思想变化,此时,在社会与个人生命这道选择题中,他心中有了清晰的答案,他开始坚定不移的离开官场,走向田园,去创造自己的田园精神世界,追求自己心中的赤子之心,他写到“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这两句诗,这是他坚定内心的开始。虽然后来他又担任了彭泽令,但这一次的任职,是因为“余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而不是因为心中的那一把隐藏的火炬,而后不过八十余日,一是因为不堪杂事,二是因为程氏妹去世,他就辞官归家了,这一次的辞官给他的十三年仕途生活画上句号,并且他用行动回答了那道关于社会与个人生命的选择题,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仰天长叹过后,陶渊明欣然地开始了他向往的田园生活。每天扶朝阳而起,伴落霞而归,甚是开心,在大自然里,他找回了真实的自己,他可以自然的放出住在他心中的那个赤子,就着窗前的一支菊花,饮一杯新酒。喝着喝着,他想起了归来时的情景,想象未来的美好生活,唤书童拿来笔墨纸砚,挽袖下笔,写下了《归去来辞》,心中所感所想跃然于诗篇之上,说道: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心境如此明了!后来,他又相继写了《归园田居》五首,这一年他四十二岁,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他只有在自然中才是最快乐、最欣豫的,经过十三年的犹豫徘徊,他最终选择了“种豆南山下”的田园生活。虽然没有殷实的物质,但是他的精神得到了净化和充实,得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怀揣着一颗纯白忠贞的赤子之心,欣欣然地回归了自己的世界,在这里,他的心情开阔清明,身体放松自然,最快乐不过如此。
快乐的日子总是如此短暂,波浪起伏的生命达到一定的极致后,就会开始向着低落的趋势发展。公元408年六月,他归田后的第三年,他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被火烧光了,“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房子都烧完了,没地方住,一家人就寄居到了船上,一直到秋天还没有找到新的居所。
这一场忽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他较为舒适闲静的生活,他的生活开始变得艰难困苦,穷且益坚,不失赤子之心,他用内心的尊严气节鼓励自己,要挺过去啊!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衣食短缺的情况下,他向往有衣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这就是他创作《桃花源记》的倾向,他在他的脑海里,创造了一个桃花源的新世界,这正所谓是赤子辜负了,便会去创造一个世界。两年后的一次稻谷丰收,他忽而有所感慨,故写了《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其中有“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他凝望着这收获的早稻,想起之前的缺衣少食的生活,总结说,人的生计归结于一种不变的道理,衣和食固然是这种常道的发端。穿衣吃饭,是人类生存的最起码的条件;无衣无食,生且不能,何谈追求?这是他回归田园遭遇第一个困难后的总结,即使归田园之路有困难,他也不动摇融身于大自然,坚守自己赤子的精神世界。
生活慢慢地回归了正轨,虽然比以前贫苦,但是总归是最好的安排,陶渊明每天顺着自然,“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与贤妻一块儿耕织、教子,偶尔喝喝小酒,写写抒情小诗,或是乡亲邻里聊聊家常农事。这一段时光里,他写了《饮酒诗二十首》和《杂诗》,就是他除了影子以外的知心朋友,在酒杯里,他才可以全然地放松自己。
人经历得越多,就会越孤单。陶渊明的晚年生活,在生活上愈加的贫困,当收成好时,他偶尔还可以“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可若是遇到天灾,就会落到断粮的境地,得靠朋友接济或是赊借,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去乞讨了,从《乞食》一诗中的“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可以感受到诗人生活上的贫困和精神、尊严上的纠结。在精神上愈加的孤独、寂寥,很少有人真正的了解他,他无法容忍乱世中的血腥杀伐,所以选择回归田园,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的纯洁宁静之所,可他的心始终是在静穆中牵挂着社会,在他听
到刘裕用毒酒逼杀晋恭帝的消息后,他的心中被激起了波澜,这不仁不义的做法让他感到愤怒,他认为他“该有写些东西的必要了”,为此写了《述酒》诗,控诉政权争夺的黑暗。
晋室被推翻后,陶渊明的孤独变得更加突出,孤独到只能和燕子讲话,他寂寞的询问那一双来到门庭寻觅旧巢的燕子:“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内心的苦闷无处诉说,只能说与燕子,这是多么孤独的一个人。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更加频繁的拷问人生的意义,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徘徊之后,他找到了最终的答案,他将其写入了《形影神》一诗中,即神的回答: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多疑虑。顺应自然、顺应常道而活,在这其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并为之坚守,就是人生的意义。
陶渊明一生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而他并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就存在于他心中的那一颗赤子之心里,但因为他是戏中人,所以一直难识戏中意。直到在生命的归处,他才蓦然回首,那其中的真意,其实就在那结庐人境处的那一刻纯然的赤子之心,既而他叹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寻觅途中,他是孤独的、寂寥的,虽然曾有所犹豫、彳亍,但他心中一直都存留着最真、最纯的情,心中始终有自己的判断和坚持,最终成为了历史潮流中的一位不受乱世纷扰、不受杂尘侵染的孤独的赤子,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充满田园诗情的世界。”
凌梅子一直细细的说着,一会儿看向远方的江面,一会儿看向近旁的水岸,娓娓道来。
说完自己的看法,凌梅子朝沈彧青看了看,示意自己讲完了。
沈彧青听完,觉得凌梅子对此的确是下了功夫的,十分有自己的见解。
“嗯,梅子说的东西,有许多是彧青大哥之前也未曾注意到的,不错。”沈彧青由衷的赞叹道。
“元立,去沏一些茶来!”沈彧青对杨元立吩咐道。
“好,我这就去!”杨元立得到吩咐后便朝楼里走去。
二人静坐着,看水中的倒影。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凌梅子喃喃道。
清风阵阵拂来,水面波澜不起。明月在斗宿与牛宿之间来回移动。
白茫茫的雾气横贯江面,水光连着天际。
芦苇一簇一簇的伫立在岸边,随着风的轻抚,芦苇叶轻轻的掠过过茫茫的江面。
“公子,茶来了。”杨元立端着茶盘从后面走了过来,打断了凌梅子的思路。
沈彧青和凌梅子都分别往旁边挪了挪,留下一个人的空间,给杨元立放茶,杨元立很自觉地把茶放在了他们两人的中间。
“喝吧!”沈彧青为凌梅子斟了一杯茶。
“谢谢彧青大哥!”凌梅子双手接过茶杯说道。
二人默默地喝着茶。
“小姐,你待会儿要唱曲儿吗?”紫灵摇着凌梅子的肩说道。
“你想听吗?”凌梅子回过头看着紫灵说道。
“是呀,我想听!”紫灵兴趣高涨的说道。
“哈哈哈,看着你们兴致这么好,我的兴致也来了。来吧!我们和唱一曲!”沈彧青边说着边放下茶杯,拿起了放在一旁的玉箫。
“好,我也准备好了!”凌梅子从甲板上站了起来,做好吟唱的姿态。
沈彧青那边萧声一起,凌梅子这边也跟着吟唱了起来。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我已去世的父亲字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岁星在寅那年的孟春月,正当庚寅日那天我降生)。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父亲仔细揣测我的生辰,于是赐给我相应的美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父亲把我的名取为正则,同时把我的字叫作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天赋给我很多良好素质,我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我把江离芷草披在肩上,把秋兰结成索佩挂身旁。)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光阴似箭我好像跟不上,岁月不等待人令我心慌。)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早晨我在大坡采集木兰,傍晚在小洲中摘取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时光迅速逝去不能久留,四季更相代谢变化有常。)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惟通:唯)
(我想到草木已由盛到衰,恐怕自己身体逐渐衰老。)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何不利用盛时扬弃秽政,为何还不改变这些法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乘上千里马纵横驰骋吧,来呀,我在前引导开路!)
……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既然不能实现理想政治,我将追随彭成安排自己。”)
一曲唱罢,凌梅子觉得酣畅淋漓。
沈彧青的萧声也在那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停罢后戛然而止!
“好!真的是听得我的心也跟着一上一下的!”紫灵在一边拍手叫好道。
沈彧青手里握着玉箫,缓缓地从另一边走过来。
吹了这一曲《离骚》,沈彧青心中也久久不能平静。沈家一路的艰辛,凌峰一家的惨状,都一一的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伴君如伴虎,朝政的风云变幻,谁都无法预测。前朝的阮籍嵇康,战国时的商鞅、李斯……
“彧青大哥,你在想什么呢?”凌梅子看着沈彧青呆呆的注视着自己的样子,不禁有些不自在,便拿手在沈彧青的眼前晃悠道。
“啊?没有,没在想什么。”沈彧青从自己的沉思中惊醒了过来,忙回答道。
“公子,现在已是子时,夜深了,该回去休息了。”杨元立在身后提醒道
“小姐,你也该回去了,夜深,凉。”江川本来是坐在船的另一端看风景听萧声与吟唱的,见乐声停了,他便从那边走了过来。
“嗯。”沈彧青毫无波澜的答道。
“哦,好的,我这就回去啦!”凌梅子笑着朝着江川说道。
“既然夜深了,梅子也该回去休息了,以免着凉。”沈彧青转头对凌梅子说道。
“对了,待会儿我会派人煮一碗姜汤,送到你那儿去,驱驱寒。今晚真的是谢谢你,为我吟唱了两首!”沈彧青顿了顿,接着说道。
“嘻嘻,好的,彧青大哥喜欢便好!”凌梅子颇为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
“好了,今晚便到这儿了,明日还得赶路,回去睡吧!”沈彧青带着哄小孩儿的语气说道。
“嗯,好的。”凌梅子便答应着,边一起随着沈彧青朝船楼走去。
夜凉如水。
沈彧青的房中,床上,一人已经盖着薄被睡下了。
十分安静的书案上,一卷白娟上,密密麻麻写着好几行字。
另一边的房中,一碗剩余的姜茶还散着余温,躺在那竹子做的圆桌上。
而床上的女子,已经沉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