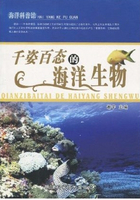宋初统治者对历史上曾经严重妨碍官僚制度运行甚至威胁皇权的其他因素也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例如,对外戚“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以下简称《诸臣奏议》)卷三十五《外戚下·上徽宗论郑居中除同知枢密院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成为此后宋朝的一项国策。对宗室也是只授予虚衔,不给予实权,所谓“赋以重禄,别无职业”《诸臣奏议》卷三十二《宗室·上仁宗乞令宗子以次补外》。,“藩邸之设,止奉朝请”[宋]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二十六,甘肃人民出版社点校本,2005年。。对此,南宋学者吕祖谦曾盛赞道:“宋朝之待宗室、戚属,其以大公之道守天下乎?虽三代未有及此!”《吕祖谦全集·历代制度详说》卷十四《宗室》,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08年。宦官虽然参与军政事务,但也没有发展到凌驾于外朝之上的程度。如《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八《宦官下》所云:“国家所以统属宦官者,盖枢府任其权。夫尊以临卑,则卑有所摄;外以属内,则内无所隐。此防微杜渐之深旨,我祖宗其得之。”
二、“祖宗家法”的利弊得失
从宋朝“祖宗家法”的实施结果来看,除弊和防弊的确都大见成效:一是彻底铲除了因武将拥有禁军大权而对皇权构成的最大威胁,也就是去掉了“腹心之患”;二是彻底扭转了一百五十年来藩镇自立、外重内轻的政治局面,重新建立起统一而巩固的中央集权;三是通过一系列分割事权的制度设计,确保了皇帝能够大权独揽,使君主专制体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四是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为士大夫政治奠定了基础,也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契机。后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唐宗”、“宋祖”相提并论的。
尽管如此,“祖宗家法”也埋下了诸多隐患。这中间既有太祖创制立法时即已造成的,又有太宗等后继者一味因循或妄加改作所导致的。这些隐患在以后的历史中渐次展开、日益凸显,终于引发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危机。例如:军事指挥效能低下;军队素质下降;“内重外轻”所带来的弊端;财政危机初显端倪;因循之风逐渐形成,等等。
宋太祖着意于收兵权、削藩镇,并在军队的统率、训练、调动和指挥等方面实施分权,以防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军事指挥效能的削弱。但当他面对具体的军事行动和边防事务时,又往往能够根据实际,加以变通,在将领的控制与使用、防范与信任以及军事指挥上的收权与放权等方面都处理得较为妥当,因而尚未造成重大的弊端。正因为如此,太祖虽然解除了许多禁军宿将的兵权,但北宋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削弱,新任用的将领也多能胜任其事,发挥其指挥效能。
宋太宗对军事并不在行,也不像太祖那样对武将们有深入的了解,因而缺乏太祖那样的自信和魄力,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更加严重。为了进一步削夺武将的权力,他把“兵将分离”的政策推向极端,造成“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正月。的局面。
为了树立自己的军事威望,太宗常常表现得刚愎自用,不但在决策时昧于形势、草率从事,而且不遗余力地推行“将从中御”的政策,在将领出征时颁发阵图、授予方略,命令前方将领按照皇帝的“部署”作战,不得擅自更改。致使前线将领备受掣肘,无法根据战场的军情变化调整部署,以致屡遭失败。不少将领在太祖朝仗打得很好,可到了太宗时几乎不会打仗了。正所谓“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于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施,智谋无所用”(《诸臣奏议》卷三十七,朱台符《上真宗论彗星旱灾》)。
太宗以后的皇帝们,又都从小优养深宫,对于军事更加懵懂无知。可“将从中御”的政策却被作为祖宗家法,仍继续遵行沿用,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宋太祖实行“更戍法”,其主要目的是“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所以坏其凶谋也”(《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七《弭盗》)。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禁军难有固定的防地,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辗转迁移的道路上。加之统军将领经常调换、无法久任,也使得部队建设和士兵训练无人专负其责,最终导致军队素质难以提高。此外,募兵制下的军士,一旦被招募入伍,便终身由官府豢养,即使是疾病老弱也很少淘汰。随着这些人在军队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宋军员额冗滥、兵费浩大而战斗力却十分软弱的流弊也就越发严重。
宋朝过分强调“内重外轻”,势必也会造成地方脆弱、边备松弛的后果。此种弊端到后来变得愈发严重,不但边防脆弱,就连内地州县也十分空虚。一旦强敌入侵,很难组织起强有力的抵抗,致使敌军每每能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正如南宋朱熹所指出的:“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本朝法制》。
太祖立国之初,经济状况、财政收入均不如后代,但却能厉行节约,对各种财政资源加以有效的利用,因而终其一朝,财政问题并不严重。如苏辙所言:“艺祖皇帝创业之始,海内分裂,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鲜,诸王不过数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县,皆不能备官。士卒精练,常以少克众。用此三者,故能奋于不足之中,而绰然常若有余。”[宋]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元祐会计录序》,“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年。
但由于宋太宗改变了太祖对辽朝积极防御、保境安民的政策,轻启战端,致使北部边境无复安宁,战争开支急剧增加。加之推行募兵制所导致的兵员冗滥,财政负担更趋严重。到太宗末年,军费开支已成为宋朝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随着对外战争的多次失利,太宗更需要稳定内部,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对士大夫和官僚曲意笼络,滥施恩赏。取士之多、恩荫之滥,导致官僚队伍急剧扩大。加上种种分割事权的制度设计,更使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些因素均导致了行政开支的大量增加。
宋太宗经常对臣僚们宣讲:“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宋朝事实类苑》卷二。正是在这种“帝王用心”之下,朝廷内外的大臣官员变得越来越循规蹈矩,不思有为,甚至把“不生事”作为处世当官的准则。其结果必然导致官员循墨,士风萎靡,吏治腐败,人才日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弊端越发积重难返,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大社会政治问题。
第二节北宋初年严惩官员贪渎和经济犯罪的措施
宋初统治者惩治官员腐败的举措,经历了由崇尚严刑峻法到注重制度建设的发展变化,到太宗时期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防范型特征的反腐机制。
宋太祖注重以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他宣布:“若犯吾法,惟有剑耳。”《长编》卷十二,开宝四年十一月壬戌。
对于此项政策的实施背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经评论说:“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赃七十余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而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赃其一也。天圣以后,士大夫皆知饰簠簋而厉廉隅,盖上有以劝之矣。”《日知录》卷十三《除贪》。
清朝史学家赵翼也认为:“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四《宋初严惩赃吏》。
宋太祖曾言:“王者禁人为非,莫先于法令。”《宋大诏令集》卷二百《改窃盗赃记钱诏》。乾德六年(968年)十一月癸卯,改元“开宝”。在改元的赦令中规定:“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不原。”开宝四年(971年)十一月己未,南郊大赦,重申“十恶、故劫杀、官吏受赃者不原”。《宋史》卷二《太祖纪二》。所以史籍记载说:“皇朝自祖宗以来,所以绳赃吏者,其法甚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二百,绍兴三十二年冬十月丁卯。
建隆二年(961年)四月,“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宋史》卷一《太祖纪一》。。这大概是宋朝官员因犯赃罪而被处死的最早记载。在宋初的文献史料中,官员因犯赃罪而被处死者比比皆是,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执法之严、用刑之重。例如:
建隆二年五月,供奉官李继昭坐盗卖官船弃市。八月,大名府永济主簿郭坐赃弃市。乾德二年五月,宗正卿赵砺坐赃杖、除籍。《宋史》卷一《太祖纪一》。三年四月,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八月,殿直成德均坐赃弃市。十月,太直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四年五月,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五年九月,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开宝二年十二月,右赞善大夫王昭坐监大盈仓,其子与仓吏为奸赃,夺两任,配隶汝州。三年十一月,右领军卫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四年正月,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坐赃弃市。四月,监察御史闾丘舜卿坐前任盗用官钱,弃市。十月,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宋史》卷二《太祖纪二》。五年三月,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七月,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十二月,内班董延谔坐监务盗刍粟,杖杀之。七年正月,左拾遗秦亶、太子中允吕鹄并坐赃,宥死,杖、除名。八年五月,知桂阳监张侃发前官隐没羡银,追罪兵部郎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璘,杀之,太子洗马赵瑜杖配海岛;侃受赏,迁屯田员外郎。九年八月,太子中允郭思齐坐赃弃市。《宋史》卷三《太祖纪三》。
此外,针对中书堂吏擅权多奸赃的事实,太祖在开宝六年五月规定,中书堂吏“兼用流内州县官”(《宋史》卷三《太祖纪三》)。
宋太祖还经常法外用刑,严惩渎职和腐败的官员。例如:建隆二年三月“丙申,内酒坊火。……上登楼见之,以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纵其下为盗,并弃市。酒工五十人,命斩于诸门。宰臣极谏,上怒微解,遽追释之,获免者十二人而已”(《长编》卷一,建隆二年三月丙申)。建隆三年“八月癸巳,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坐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宋史》卷一《太祖纪一》)。
对于宋太祖的法外滥刑,宋人常持褒扬的态度。如南宋留正说:“艺祖皇帝惩五季之弊,凡赃吏一切弃市,艺祖岂好刑人哉?诚以不如是,则不足以行仁政于天下也。”《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八,高宗皇帝建炎四年(起七月尽十二月),“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年。
实际上,这些言论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宋太祖以喜怒而用刑,法外惩治某些官吏,又法外纵容某些官吏,无非是玩弄权术罢了。从是否有利于法治发展的标准来判断,并无值得称道的地方。
所以,《宋史》又说:“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宋史》卷二百《刑法志二》。宋太祖时在惩治官吏腐败方面虽然有法可依,但在实际执行中也存在立法与司法脱节的问题,太祖个人的主观态度,使执法过程中的任意性与擅断性十分严重。说明当时防治贪腐还没有完全走上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
这突出表现在,太祖时期对赃吏的处置既有严酷的一面,也有“宽纵”的一面。
例如:武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人在攻占四川后,作恶多端,抢劫、杀降、贪污、受贿,无所不为,“凡所取受、隐没,共为钱六十四万四千八百余贯,而蜀宫珍宝及外府他藏不著籍者,又不与焉”,以致“伪蜀臣民往往诣阙,讼全斌及王仁赡、崔彦进等破蜀时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诸不法事”。但宋太祖却网开一面,“特赦之”,“诸军将士有所受者,一切不问”(《长编》卷八,乾德五年春正月辛丑)。
再如:建雄节度使赵彦徽,“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巨万”。此人“与上同事周世宗,上尝拜为兄”。宋太祖虽尽知其贪赃实迹,“薄其为人”,却又对他“崇顾甚厚”(《长编》卷九,开宝元年五月丙午)。
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赵普“强占市人第宅,聚敛财贿”,宋太祖反“叱之”,曰:“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太祖宠待赵普如左右手》,中华书局点校本,1989年。)赵普“尝遣亲吏往市屋材,联巨筏至京师治第,吏因之窃于都下贸易”。然而当前右监门卫将军赵玭揭发赵普“贩木规利”时,宋太祖却“反诘责玭,命武士挝之”,并将他“责为汝州牙校”(《长编》卷十二,开宝四年三月丁巳)。
宋太宗虽然事必躬亲、大权独揽,但十分勤政,史称其“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昼日,亦未尝寝”《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太宗皇帝》。。虽然猜忌大臣,但对选拔官员十分认真,考核也较为严格。他强调“国家选材,最为急务”,“非材之人,不可虚授”,要求官员“勤公洁己,奉法除奸,惠爱临民”[宋]罗从彦《豫章文集》卷三《遵尧录·太宗》,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与太祖一样,对贪官惩治较严。他还亲笔写下“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命刻石立于各州官署大堂,以警诫官员,称为“戒石铭”([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一《戒石铭》,中华书局点校本,2005年)。
在严惩官吏贪赃枉法的同时,宋太宗也比较重视与惩治赃吏有关的法制建设。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乙卯,宋太宗继位后违背礼制,匆匆改元,在赦令中曾规定“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这是为了稳定政局、笼络人心的特殊举措。
到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六月,遂诏令天下: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来,“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宋史》卷四《太宗纪一》)。在此后的历次赦令中,都重申了这一原则。
赃罪的范围也十分广泛,除收受贿赂以外,盗用官钱官物、盗卖官船、假官钱籴粜、主库官擅变权衡以取羡余等等,都在赃罪之列。例如:太平兴国二年七月,诏诸库藏敢变权衡以取羡余者死。三年二月,泗州录事参军徐璧坐监仓受贿出虚券,弃市。四月,侍御史赵承嗣坐监市征隐官钱,弃市。六年十一月,监察御史张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钱籴粜,弃市。《宋史》卷四《太宗纪一》。雍熙二年(985年)十月,汴河主粮胥吏坐夺漕军口粮,断腕徇于河畔三日,斩之。《宋史》卷五《太宗纪二》。
官员犯赃罪受重刑,他们的“举主”(推荐人)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雍熙二年正月,朝廷下诏规定:凡举荐官员,“所举人若强明清白,当旌举主;如犯赃贿及疲弱不理,亦当连坐”(《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七之四)。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严惩官吏贪赃行为也作为祖宗家法的一部分,被后来的君主们谨守和奉行。正如王安石指出的:“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台北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正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