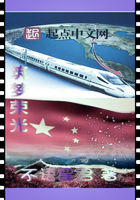水至清则无鱼——中国谚语
我从未想过要为中国做些什么。当世事难料的生活浪潮把我推送到中土帝国的沙滩上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自己应当记录下这一切。
1984年我第一次踏足中国大陆时,只是一个逐利的商人,为昂贵的西方国家生产的水力发电涡轮机物色一个廉价的替代品。在从成都机场到工厂的途中,我在窗外没有看到任何吸引我的地方——那是一个原始、粗糙、给人异样世界感的国家,似乎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炼狱苦难之后抖落身上的尘土。一个星期之后,我签订了采购合同,向对方账户打入了经过辛苦谈判后敲定的25%定金。之后我就离开了,当碎石铺成的飞机跑道在身后退入浓雾中时,我在想最终能否看到我的涡轮机,并且打定主意再也不会回来了。
回到美国之后,中国那种遥远的感觉压倒了我在旅途中浮现出的其它思绪。就好像是我刚刚去了一趟火星。的确,中土帝国在9000英里外,但是时间和距离尚不足以构成我一半的顾虑。其它困难在于当时蹩脚的通讯技术:几乎不可能打电话给涡轮机工厂的人了解设备生产的进度——那个公司只有一台供本地通话的电话机,而且他们的传真——堆在地板上的卷曲的纸张上全是不知所云的中国字——就像一个温暖午后飘落的雪花那样转瞬即逝、毫无意义。我在中国短暂停留了一个星期,我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和我一样。尽管签订的合同证明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时只有一个粗浅的合同法。他们会履行承诺吗?我交叉手指,甚至脚趾祈祷,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不断反省自己。
涡轮机最终还是送达了,基本上准时,而且感谢上帝,机器运行一切正常。我开始对我的中国同仁感到放心,他们和我是一样的。中国的商业发展刚刚起步,当这个国家的电力产业和其它产业需要外国投资的时候,我是一个首选的合作方,他们那些无处不在的术语可能意味着很多东西。作为福建闽江一家水力发电项目的合资公司的合作伙伴,以及作为帮助早期私有化企业进入美国股票市场筹集资金的投资银行家,我一头扎入了已经波涛汹涌的中国大河。我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我的那些中国同仁与我依然处于世界的两边,我对他们越来越了解,但他们给我的印象并不都是正面的。在每次前往中国的漫长旅途中,我总是充满了焦虑和恐惧,我一直无法让自己对9000英里外的那个国家产生一点亲密感。但是中国已经开始吸引世界的关注,在家乡,我的故事总是聚会上最吸引人的话题——所有人都想更多地了解那个金色、未开化土地上的希望和失望、幸福和悲剧。我开始思考要不要写下一些东西。
大部分人都说事不过三,更不用说是与中国有关的商业机会,但是当我迫切需要再打出一手好牌的时候,中国在向我召唤。这一次我已经有所准备,态度坚决、怀疑一切,毅然决然地进入这个现在已经洋洋自得的国家,最后一次攫取熔炉中的财富。我坚信,在中国面临的商业挑战无比严峻,任何超越生意伙伴的关系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这一次有所不同。作为中国的一名企业主,与我打交道的中国人都是我的合作伙伴或者雇员。他们都与我站在一边,尽管有的勤奋、有的懒惰,但我们都在齐心协力打造一项生意,都在有史以来最大的商业扩张背景下享受那些闪闪发光的商业机会。在搭乘一趟长途火车,并且经历了一些值得回忆的事件和人物之后,我利用飞往肯尼迪机场的12个小时的空中时间在电脑上做记录。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来到办公室,继续写作。这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感觉: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中国。
跨越了东西方的文化鸿沟,回忆自己的朝圣之旅后,我记录下这第一手资料。其中既有让我心碎的懒惰、腐败和表里不一的背叛,也有令我敬仰、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忠诚和无私奉献。把这样的经历作为一个故事呈现出来或许可以,但若是作为一个纪实类文学体裁则有欠公允。中国其实更好。
尽管《中国财富》这本书基于我自己的真实经历,但它是一部小说,其中大部分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如果与现实中的人物姓名、外貌和行为有任何相似,都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