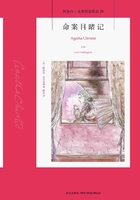水秀带回话,说乡里要罚于旺田三千元钱,交不上钱就回不来家。苏凤荣有些傻眼,三千元,大山一样压得死人的数目,这个家四角旮旯都见光,哪还有值钱的东西?除非抽梁撤檩卖房子。可没了房子一家人住在哪里?离婚时,自己倒是还带出三五百元钱,可给水强寄出生活费,再加给旺田掂对一日三餐,哪还有闲钱?旺田被囚在乡政府的院子里,咋说肚里也有火,如果再吃不下睡不安憋屈出病来,日后的药钱更吓人呢。吃喝上的钱不能节省,省也是零头巴脑的小数,不值。
思来想去,再一条道就是借。跟水秀试探,水秀说为给她妈治病,能借的都求过好几次了,于家本没有那种存闲钱的富亲戚。跟屯里人张口吧,她初进于家门,还没个正经名分,谁会借给她?再说认识的人也极有限,一个朱老九,就是因为他,旺田才被抓了去,朱老九也被整进去挨过打,俩人已作下大仇了,不比扔谁家孩子下井仇浅,还能再登门提个借字吗?再一个认识的就是村支书于水丰。可没出事时,于旺田在家跟她说过贴心话,说原先还以为于水丰是掏心窝子真为咱想事算计,没想到头来,把他自己的媳妇整到乡中学去教书,就再不提原先的话茬儿了。
人啊,还不就是那么回事!苏凤荣安慰他,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傻子还知下雨往自家门里抱柴禾呢,为自家老婆孩子谋点儿好处,也是人之常情。大大小小的当官儿的,只要不败祸别人往自己手里搂,就还算良心没叫狼叼去。你别想得那么多,话叫别人听去还说咱心眼儿小,挑小理儿。于旺田嘟咕说,这话我不就是和你说嘛,又没跟别人。反正我认了一个理,这辈子,自个儿的梦,终其了,还得自个儿圆,指靠谁也没用。想起这话,苏凤荣就把去找于水丰借钱的念头也放弃了。有借就得有还,三千呢,也不是十天八天打个周转的事,这个家的进钱道儿在哪里?真要让人家堵上门来讨债,反倒不如眼下另找个能长远些的辙了。
苏凤荣也曾想到去找县里的吕书记。于旺田没少念叨吕书记的好,耳朵听得都快磨出趼子了,说吕书记没架子,说吕书记懂得穷苦人的难处。找吕书记当然不是为借钱,只要吕书记能往乡里打个电话,那罚款的事就可风吹云散。开春时水秀交学费的事不就是这么解决的吗?当官的口里落下颗唾沫星儿,都值金值银的。可思来想去的,苏凤荣还是给自己打了退堂鼓,一是自己从没见过吕书记,要是冒冒失失地闯上门去,吕书记会把自己当成什么人呢?再说,这事虽说旺田屈,可咋说也是个偷,不像孩子念书或谁谁生病遇到了难处,好说不好听,吕书记能为“贼”赏脸说情吗?设身处地地想,咱要是当上那么大的官,怕是也有不好张口的事情吧。
于是,长远些的辙便只能往娘家哥那里想了。好歹是一母所生,兄妹俩自幼感情不错,亲妹子遇到了过不去的火焰山,当哥的还能袖手不管吗?跟嫂子的关系也还说得过去,虽说离婚后在哥嫂处住段日子,嫂子也给过她脸子看,但那也是人之常情,谁家小姑子能在哥嫂家长住不走呢?想起当初嫂子生他们家老二时,自己舍了家跑去侍候月子,分手时嫂子拉住她的手,说过亲姐妹也难比咱姑嫂的话。哥哥要是能借下这笔钱,想来总会给些期限,不会隔三岔五地跑来追债,到了明年这时候,兴许家里就不至于再像眼下这般难了……
苏凤荣便骑车去了哥哥家。哥哥住的地方没水田,养不了蟹子,但家里扣了蔬菜大棚,除了地里的收成,一年到头,大棚总还能进上几千元钱的。没想苏凤荣刚把来意吐出口,哥嫂的脸色就起了变化。哥哥一个劲儿地看嫂子,嫂子脸拉得老长,却故意扭到一边去,不跟哥哥对眼光。哥哥只得吭吭哧哧地说:
“你们……不是还没领结婚证吗?依我看,不如赶快拉倒。你没地方去,就还回这儿来。再进谁家门,总得看得长远点儿,不能剜到筐里就是菜。慢慢再碰嘛,我和你嫂子都帮你留意着,咋也找户比于家日子好过些的。”
嫂子接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虽说咱另走一家的人没指望进了门戴金挂银,总还得有碗饭吃有件衣穿吧?我没听说日子还没等过上,就四处先替他借钱堵窟窿的。他一个庄稼院的穷汉子,还拉扯两个孩子,这可啥时是个头?你拿钱打水漂儿啊?”
苏凤荣说:“于旺田虽说穷,可是个好人,这一点我看不走眼……”
嫂子打断她:“好人还偷?为这事,我和你哥脸上都挂不住,没法见人。还没等喝杯喜酒呢,他人倒先进去了,哼,还好人!”
苏凤荣说:“自古好人遭难的事多了……”
哥哥说:“他是不是好人,我不跟你争。你看是好人就算好人吧。可有一宗,他是好人也好,恶人也好,结婚前的抓瞎事,他总得自个儿扑腾平整了。可眼下,这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亲妹子的事,我当哥的若说不管,不禁讲究不够人性;可他,眼下我还八竿子打不着,不管不算理短。”
嫂子赞许:“这话在理。这钱要借给你,人们不光说你虎,还得说你哥你嫂加一块是五百,一对二百五!”
苏凤荣无话可说了。站在哥嫂的脚窝看,虽说不舍善财是真实想法,但也句句都叼在理上,换了谁,会傻狍子似的顶了饥荒去往穷窝子里跳呢?谁又能把辛苦攒下的血汗钱,借给八竿子打不着的犯了事的人呢?
苏凤荣坐在那里流泪。她还有最后一张牌可打,可从于家门出来时,她就一再提醒自己,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张牌是绝对不能出手的,一出手,就必伤了兄妹之间的情分,那往后还咋登哥嫂家这个门?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亲哥亲嫂,她哪还有什么可依靠的人呢?可事已至此,不打这张牌,她又去哪里张罗三千元钱?苏凤荣狠狠心,还是说了:
“哥,嫂子,有句话,我本不想说,可我也是被逼得实在没招了。话说出来,合适不合适的,你们可千万别怪罪妹子。”
哥哥倔哼哼地说:“有啥话,你说。”
苏凤荣说:“咱爹临死时,有句话,不知哥嫂还记不记得?”
哥嫂都怔了,对望一眼,再不言了,脸色如夏日里陡起的阴云,黑沉沉不见一点儿光亮。
老妈去世得早,老爹活着时,或住儿子家,或去闺女家住些日子。老爹最后病倒那次,是在闺女家。哥哥看老爹病情日重,便带了几个人,还备了担架,说把老爹抬回去养。苏凤荣不让,说爹都病成这样了,一路折腾着,怕没等到家就咽了那口气。儿子家是家,闺女家怎就不是家?还在这里养吧。那俩月,老爹炕上吃,炕上拉,都是苏凤荣侍候着。哥嫂有时来看看,不过带些药品或老人爱吃的东西,帮着料理一两日,就又回去忙田里棚里的活计了。
老人至死都清醒,那天,他把儿子和女儿叫到身边说,都说养闺女是赔钱的货,我不是也得凤荣济了?咱家的那房子院子是我一辈子一块砖一根木垒起来的,我现在说了还算数。我死后,房子院子还给你哥住,那两间西厢房归你妹子。你们亲兄妹,公平不公平的,知爹这片心就行啦,都别计较啦。爹说这话的时候,杜成林还没赌得不管天不顾地。苏凤荣当即说,爹,我哥我嫂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你老的心意我领了,可那西厢房我不要,就都归在我哥名下吧。那还是我的家,爹妈不在了,哥嫂比父比母,我还要常回去看看呢。老爹心里欣慰,老泪纵横,连着说,还是得从一个娘肚里爬出来的呀……就在那一夜,老爹撒手而去了。
苏凤荣见哥嫂好半天不吭声,又追了一句:“哥忘啦?”
嫂子说:“拉出的屎还往回坐呀?”
苏凤荣说:“我说过的话,到啥时都不反悔。我没说跟哥嫂要房子,我只是遇到了难处,请哥嫂伸手拉我一把。借下的钱我保证还,加上利息,一分钱不会少,立字据找证人都行。怕我还不上,村里有扣大棚的户,忙时少不了雇工夫,哥嫂帮我注意点儿,到时招呼我一声,活儿我干,工钱你们去结,啥时结完啥时算,算上利息我也没二话。”
既撕开了脸儿,苏凤荣便说了狠话。
哥哥说:“家里翻盖房子,那西厢房早拆了。砖石土坯算扔货,也就那房木还值俩钱儿,撑破天的价也就值一千。”哥哥给嫂子使眼色,“去,去屯里谁家跑一圈,给凤荣借两千,说等棚里菜下来就还。”
“只值一千,咋还借两千?”嫂子小声咕哝。
“少废话,借两千。”哥哥瞪了眼睛。
嫂子气嘟嘟地走了,把门摔得砰啪响。苏凤荣知道柜子里就有钱,可哥嫂不愿露底儿。唉,人与人在感情上生分,也快,种子入土就发芽,尿水落地就成泥。
苏凤荣揣着两千元钱,还有满腹的伤感离开了哥嫂的家,一路上热泪洗面,难止难歇。为这两千元钱,兄妹的情分狠狠一刀,从此断了,以后想接续上也难,中间有断茬儿了。哥哥说房木值一千,却借她两千,这里就含了另有一千元的情义在里面,可哥哥没说借三千,也含了自梦自圆就此了结的意思。哥哥念过高中,脑瓜活,是村里有名能算计的人,他如此行事,也算把不好说出口的话都说了出来,那意思让你自己琢磨,好好咂吧去吧。
还差着一千元钱,苏凤荣回到家里发呆。水秀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摇头,催水秀去写作业。再思再想的,就想到了卖血。她想起前些日子看电视新闻,说一个村子穷,那里的人以卖血为生,有人还用卖血钱供出了大学生,镜头上有口大缸的特写给人的印象特别深,播音员说有个老农几年间卖的血,累计都可装下一大缸了。
想到这里,苏凤荣不由打了个寒颤,发了好一阵呆,便起身去问水秀,一CC是多少?水秀似懂非懂又有些卖弄地说,国际代号K是公里,M是米,C是厘米,一CC大致相当于一立方厘米,用于容积,就相当于一毫升吧。苏凤荣问,那一百CC是多少?水秀说,那就一百毫升呗。苏凤荣又问,那咱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水秀说,书上说,好像有几千CC,我没记准。
水秀说到这里,就有些奇怪了,反问大姨你问这个干什么?苏凤荣掩饰说,这两天我腰酸,可能又要来事,心里就好奇,想知道一来事要出多少血?水秀越发卖弄起在学校里学来的少得可怜的生理卫生知识,说一般情况,是几十CC,但也因人而异,超过100的也属正常。
问过这些话,苏凤荣心里就觉有了底。身上的血几千CC呢,卖一点儿怕什么,就当多来了两次例假。再说,血也不是鼻子眼睛,去了还可以再生呢。
决心一定,第二天一早,打发水秀上学走了,苏凤荣便骑车再奔县里,特意踅摸到一个看样子有些学问的人,问:
“大哥,跟你打听个事,咱县里有没有卖血的地方?”
那人警觉了,问:“这社会哪还有卖血的,你是问献血站吧?”
苏凤荣忙点头:“对,对,就是献血站,献血站。我记错了。”
那人说:“献血站一般都设在市里,咱县里没有。哎,你怎么问这个?”
苏凤荣说:“我们屯里有个人要去献血,我家男人陪着去了。我怕他见钱眼开,也跟着撸胳膊,那地里一秋的活儿还谁干?这不,就追着找上来了。”
那人说:“那你还是去市里看看吧。也别把献血当成什么了不得的事,健康人偶尔献上一两次,献血适量,对身体并没有什么大伤害,增加点儿营养,多注意休息几天就恢复过来了。”
有了陌生人的这般指教,苏凤荣越觉心里有底,便将车子放进胡同中的一个僻静处,锁好,乘大客车直奔了市里,三打听两打听的,便找到了献血站。第一次献血还算顺利,只是报名登记时小遇了点儿麻烦。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让她出示身份证或户口本,她很吃惊,说我献血,又不是要用别人的血,还用身份证户口本干什么?工作人员很认真地看了她一眼,说你是头一次来吧?苏凤荣便点头。许是那天献血站正缺血浆,工作人员说,如果以后你再来,请一定带有效证件。请先抽点儿血检验一下吧。
坐在走廊里等检验结果的时候,苏凤荣见有一位刚献完血的人出来,便追过去,小声问:
“你献了多少?”
也是个女人,年龄要比她小些,答,四百。
又问,抽完血有啥感觉?
答,也没觉怎样,稍觉有点儿乏。
又问,他们给多少钱?
那人白了她一眼,只应了声“你这人,真是”,便有些厌烦地离她而去了。
苏凤荣体会到了,到了这儿,一别提卖,二别提钱,好比打渔船上别说翻,生日宴上别说死,都犯忌呀!
苏凤荣献了400CC血,站起身来的时候,果然觉得有些头晕,两腿软软的,发飘,有点喝醉酒的感觉。走出两步,还有点恶心,要吐。护士说,你先别忙着走,去长凳上坐一会儿,喝点儿水,观察观察。果然,歇一会儿就觉好多了。从付款窗口接下400元营养费的时候,她心里还是狠狠乐了一乐,她只知能给钱,却没想到会给这么多,旺田没黑没白地给别人养一个月的蟹子,还是在自家的田里,也才400元。照这么算,只需三次,三千元钱就可凑齐了,还有了车脚路费,怪不得电视里说的那个村以卖血为生呢。
走出献血站,外面的大太阳白白亮亮的很毒辣,正是秋老虎逞威肆虐的时节。在日光下一晒,苏凤荣又觉头晕目眩上来。看路边正有一个公园,树荫石凳上坐着许多人,有打牌甩扑克的,也有说说笑笑的,还有人在哼哼呀呀地学唱戏,基本都是中老年人。苏凤荣便踅进去,找了一处树荫坐下了。有卖雪糕的问到跟前来,她犹豫了一下,买下一根,慢慢嘬着,加之凉风习习,一股清爽甘甜霎时漫遍全身。唉,雪糕里有牛奶,也算补充营养了。还是城里人会活,吃饱喝足在公园里玩儿,活得滋润啊!
有个秃顶的男人坐到旁边来,五十多岁的样子,雪白汗衫穿的挺板整,下巴刮得挺干净,手里还抓把写着字的折扇,一会儿开一会儿合的,弄出嚓嚓的响。秃顶问:
“大妹子,不是城里人吧?”
苏凤荣说:“我家在乡下。”
“进城走走亲戚?”
“哪有亲戚,进城看看,散散心呗。”
秃顶点头:“来散散心好。看你年纪不算大,就没想进城做点儿啥?”
一句话提醒了苏凤荣。对呀,进城也不能光卖血,听说城里人有钟点工,还有保姆,洗洗涮涮照看病人啥的,都是挣钱道儿,来时咋没想到这一宗呢?她说:
“本也想做做看。可两眼一抹黑的,谁找咱?大叔要是有门路,就帮帮忙吧。”
秃顶笑了,又上上下下地看了苏凤荣两眼,说:“那就跟我到家里看看?”
苏凤荣问:“你家在哪儿?”
“出公园,过马路,十来分钟的路。”
“我晚上还要赶回去……”
“也就一会儿的活计嘛。”
“要我干啥?”
“你还能干啥,就进屋那点儿活计呗。”
苏凤荣心里算计一下,下大客车时顺便问过,最后一班回县里的车是六点,只要赶上那班车,再骑车快点儿蹬,上夜时总能到家。就是水秀放学回家时吃不上应时饭了,那她就自己做,家里还有一把挂面,加瓢水烧把火的事。十几岁的姑娘了,还能让自己饿着吗?
苏凤荣又问:“咱先说清楚,咋算账?”
秃顶说:“一把一利索,三十,不少吧?”
三十,当然不少。这活计真要能做得长久,入冬后进城做上一段也值,打工嘛。在乡下,进大棚驷马汗流累一天,撑破天也就给二十。苏凤荣便起身随秃顶走,走几步还回头看了石凳一眼,担心落下什么东西。这一眼,她就看到了旁边几个老头儿老太太怪怪的眼神,有人还撇嘴窃笑。她读不懂那眼神和那笑意,什么意思呢?
苏凤荣一路上都在揣测,他家里会是什么活计呢?秃顶的老太太卧床不起等着擦洗?家里攒下一堆脏衣脏裤盆盆碗碗?他要让我擦玻璃可得加小心,头还有点儿晕呢,不敢登高。这般想着,便跟秃顶登了五楼,又等他开了房门。屋里挺洁净,也挺安静,她探头往几个屋子扫了两眼,却哪里见卧床的病人。秃顶边换拖鞋边说,放心吧,啥人也没有。又将一双拖鞋踢到她脚下,说:
“你也换换。你没病吧?”
苏凤荣怔怔,忙摇头:“没,没有。”
秃顶说:“你脸色不好,真没病?”
城里人讲究,怕外人把传染病带进家里。苏凤荣怕人家信不着自己,忙信誓旦旦地证明自己,把不愿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我真没病。我刚去献血站献过血,脸色不好,不信,你看我有献血的单子呢。有病的人,人家要咱的血?”
怕别人有病的秃顶却自己到了茶几前,抠了一片什么药塞进嘴巴,又抓水杯将药送下肚里,回手指指一扇关闭的门:
“你去卫生间,快洗洗。”
苏凤荣越加发蒙:“我、我洗什么?有什么活计要干,你就说话吧。”
秃顶去把窗帘哗啦一声拉严实了,屋子霎时阴暗下来。转过身,他又脱衣脱裤,麻杆腿排骨胸便都亮在了苏凤荣面前。他说:
“洗什么还用我说?你还有什么?你们乡下人啊,就不知讲卫生,办事前都不知洗洗呀?”
一股血嗡地直冲头顶,苏凤荣陡地明白这秃顶把自己找来要干什么了。那种无比巨大的屈辱感大山样从头顶压下来,一时间,她张惶失措,呆立在那里不知怎么好。
几近赤裸的秃顶凑上前来,欲搂抱苏凤荣,嘴巴还驴样地噘噘着往前伸。苏凤荣清醒过来,也镇静下来,一掌推过去,喝道:
“你、你把姑奶奶当成了什么人了?”
秃顶焦恼了,说:“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苏凤荣道:“说好了的,我是来给你干活卖工夫。”
秃顶说:“对,说好了的,一把一利索,我买的就是你身子。想卖工夫,城里还轮到你了?”
苏凤荣转身就走,但防盗的铁门已经闩死了,那开关太复杂,苏凤荣又太慌急,竟是左拧右拧打不开。那秃顶从后面扑上来,抱住苏凤荣的身子,越发不知羞耻地说:
“我给你五十行不行?我的药劲都上来了。”
苏凤荣低声喝骂:“你个老秃驴!松手,把门给我打开!”
老秃驴却不松手,说:“五十可就顶天了,二十郎当岁的小姐也就这个价。你个乡下老娘们啥没经过,还在乎这一回?五十,你可是白拣啊!”
苏凤荣听他越说越不像话,挣又挣不开,便用胳膊肘重重往后一杵,这一下正捣在他的软肋部,老秃驴哎哟一声就闪开了。苏凤荣骂:
“别说五十,你拿出五万来也休想!老牲口开不开门?不开门我可要喊人啦!”
老秃驴红了眼睛:“你喊,你有能耐就喊!警察来了先抓你卖淫!”
苏凤荣气急了,一把抓挠过去,是那种乡下女人的惯用战法,老秃驴脸上登时留下几道重重的抓痕。就在他躲闪第二次打击时,苏凤荣已一步跨到茶几前,抓起了又重又大的玻璃烟灰缸,喝道:
“你开不开门?你再不开门,我就砸死你!我豁出不活了!”
回家的路上,苏凤荣又是一路热泪洗面,难止难休。昨天,在自家哥嫂那里惹了一肚子气,那还是心有准备;可今天这奇耻大辱,却是做梦也想不到,回去后,连委屈都没法对人说啊!这个城里的老畜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