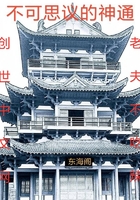这时迎面来了一位骑者。原来是他的女儿沙柳!老头儿默默地望着女儿。女儿脸上那股高兴劲没有了,不敢正视父亲那双眼睛,低下了头。缄默。
“他们在打猎……”
老沙头默不作声,望着她。
“…打咱们的野兔、山鸡……”
老头儿仍然盯着女儿的那张显得疲倦的脸。
“他们的枪法真准,该死的!坨子外边的人都这么坏吗?”
老头儿这会儿才冷冷地开口:“我派你去是真的陪他们游逛的吗?”
“我说了,我喊了……我冲上去夺他们枪了!”女儿急了,嚷起来,“可是大胡子不理睬我,秘书小杨冲我说:沙柳,兔子山鸡野生野长,也不是你家老爹养的家兔家鸡!承包给你们的是坨子,不是坨子里的兔子山鸡!”
听了女儿的话,老头儿愣住了。
半天,他才喃喃发问:“叫他们打中的……多吗?”
“三只山鸡,五只兔子,还有……”
“还有什么,快说!”
“还有那只沙狐……”
“那只沙狐怎么了?”
“他们发现了它的洞穴,正在追击……”
“啊,天呀!那你为啥回来了?混帐!不去挡住他们,不救救老沙孤,你为啥跑回来了!”老人愤怒了,举起了拳头,前额上的青筋暴起,血冲到脸上变得黑红黑红。
“他们进死漠了,追着沙狐进死漠了。我的毛驴跟不上他们的马……”沙柳不躲,站在原地望着父亲。她的嘴角流露出一丝凄惨的冷笑。“老沙狐,真是好样的。它从洞里跑出来,嘴里叼着两只崽子,后背上驮着另外一只,跑进西边的死漠里去了……”
“死漠?”老沙头举起的拳头垂落下来,塌陷的两腮抽动着,眼睛移向西方那白茫茫的沙漠深处,“死漠?进死漠了?”
从南头吹过来一阵风,坨子上的沙蒿、骆驼草、苦艾都急剧地摇曳起来。那股聚集在太阳下边的白色烟尘,已经向这边移动过来,驰进了莽古斯沙漠那是一股强烈的风暴。
“爸……”沙柳惶恐地朝东南望了一眼,但除了一道长长的模糊不清的波浪外,什么也看不见。这道波浪很快涌过来了,“爸,咱们快回家,咱们家水井还没盖!”
老沙头仍旧呆站在原地向西凝望。“死漠,他们进死漠了……”沙柳不由分说,拉上父亲的手向家跑去。那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迅速异常,在家门口赶上了他们。强劲的风打着转,把坨子上的沙子吹得沙沙地响,落叶和碎草被吹上了半空,四周顿时昏暗下来。太阳被这浑黄的一道魔墙遮挡后没有光热了,像一个染上暗黄色广告漆的皮球一样悬在那里,模模糊糊,毫无生气,失去了平时对沙漠的威慑力。
可是,风是热的。从沙漠里蒸腾出来的热气被大风裹卷过来,从背后喷射着,犹如火舌透过衬衫炙烤着他们的脊梁。尘沙吹进他们的耳朵和嘴,迷着他们的眼睛一风势越来越猛,大风摇撼着沙漠。
“该死的风沙!魔鬼,坏蛋娘的!”沙柳连连吐着嘴里的沙子,奔跑着,盖水井,赶鸡群,关门窗。
老沙头一言不发,皱着眉头站在窗前,向西凝望着。
“爸……”
“风暴,这罕见的风暴……在死漠里堵上他们了……”
“活该,这叫报应!”
“风暴会掩埋沙漠中的足迹,所有认路的标记都将消失……”老沙头脸色变得冷峻,“他们会迷路的,走不出死漠。”
“不是我们赶进去的,操那份心!”
“孩子,去把那个大塑料桶灌满水,往口袋里多装点干粮。”
“爸!”
“快去!”
“不,爸爸,你身体弱,有病!”
老沙头不理睬女儿,转身走到外屋,往那个塑料桶里灌起水来,并把所有的玉米面饼子和干炒面装进一个口袋。然后,回屋翻找出几件衣服,又找出布带了扎腰、扎裤腿。
“爸,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呀!”沙柳乞求着,扑过来,跪在父亲的脚边,抱住他的双腿。
“孩了,没有水,没有干粮,他们有生命危险,老沙妖盯上他们了。还有……那只沙狐……”
“可是你有病,风沙中走几步喘不上气,你这也是送死。不是救人!”
“我能挺得住。我有这个宝贝能压压哮喘”老沙头从怀里拿出一瓶老白干,“咕嘟”地周了一大口。
“不,那也不成。让我去吧,爸,你看家,让我去!”
“死漠里你也会迷路的,你不了解它,我知道这头妖魔,知道上哪儿去找他们。孩子,你起来,让爸快点走!”老沙头脸变得严厉,呈现出毫不动摇的铁般的刚毅。
“不,我不放你走,不放你走!”沙柳抱紧了父亲的双腿。
老沙头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劲儿,一脚踢开了女儿。沙柳滚倒在一边。老沙头背起水、干粮、衣物一头扎进门外疯狂肆虐的沙暴之中。
“爸爸——!”
沙柳从地上爬起来,从门后拿起父亲的拐棍,也跟着扎进风沙中。板门在她后边被风沙来回摔打着。
他们父女俩跋涉在昏天黑地的沙漠中。
已经走了一天一夜了,没有发现任何踪迹。而风势仍不减弱,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吞没着一切。沙柳叶子蔫了,低垂下来,好像一条条灰色的碎布。在沙洼地上,每丛沙蓬下部集拢了一堆像黑面粉一样的褐色细沙尘。那些艰难地生长在死漠洼地里的稀疏植物的叶子,都变色了,枯焦了。把叶子摘下来,可以用手指搓成粉末。风,转眼间把这些枯叶卷走了,光剩下光秃秃的枝。哦,大漠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世界!
老沙头像一头老骆驼般艰难地迈着步。他用左手挡在双眼的上方,以防猛烈的风沙击伤他的眼睛,右手拄着拐杖,走几步停下来歇一歇,咳嗽一下堵在嗓眼的痰。有时被迎面的强风灌得无法呼吸,脸憋得发紫,这时,他赶紧转过身,搁一口烈酒。沙柳背着水壶干粮等物,寸步不离地跟在父亲后边,有时搀着他把脚从软软的流沙层里拔出来。
第二天下午,风停了。沙漠一下子沉寂下来,那些曾经是跳跃的、活动的、疯狂的沙粒,此刻都变得温顺、安静,乖乖地躺在那里,似做错了事的淘孩子听候大人发落。这头恶魔是疲倦了,奔腾了两天一夜,该休息了。
老沙头举目搜索。黄沙起伏,茫茫无垠,四周都是一样的颜色,一样的物体,单调乏味,令人目眩,使你不禁疑惑:世界是不是都由沙漠组成?这里,找不到一株绿色植物,听不到一声鸟虫鸣。在这种时候,哪怕是听到一声苍蝇的嗡嗡叫,心灵上也感到一种宽慰和轻松,感到生命的存在和可贵,减轻不断攫住心灵的那个可怕的阴影。没有,没有任何生命的信息,除了自已烫手背的呼吸。沙柳恐惧地抓起父亲的衣角。老头儿嘴唇干裂,渗出血。女儿把水壶递给他。他摇了摇头。水消耗得不少,可人还没找到,谁知道在沙漠里还要跋涉多久。
一面很陡的沙坡下边,有一个小黑点。沙柳眼尖,跑过去看。这是从流沙层里露出来的马鞍桥的尖部。她伸手拉,纹丝不动,一挖开流沙,她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马鞍子下边连着一匹死马,完全被厚厚的流沙埋掉了。
“爸,快来看!”沙柳惊叫。
老沙头走过来一看,明白了。这是风暴中,受惊的马争脱了主人,倒在这里被流沙活埋了。
“那人呢?人哪儿去了?”沙柳着急地问。
老沙头不说话,环视着沙丘,仔细辩认着地形。
“爸爸,你怎么知道他们走到这一带来了?”
“我是猜的。老沙狐带崽子跑进死漠,证明死漠里有它能躲避的洞穴。狐狸是很精的。可是死漠里都是沙丘,根本不能挖洞筑穴,它能躲哪儿去呢?我想起,这片死漠里有一座被沙漠埋掉的古城废址!老沙狐的洞穴,只能在这古城废址里。有一年我领一支考古队探过古城废址,所以,一进死漠就奔这一带来了。”
“那古城废址在哪儿?怎么看不见?”
“一刮风沙,这里的地形变迁很大。咱们再往前走一走。”
他们继续前进了。
黄昏时候,他们终于发现了那两个人。一座光秃秃的高沙丘顶上,两个人东倒西歪地躺在那里。大胡子主任躺得很别扭,被沙子半埋住身子,茂密的黑连鬓胡子里嵌满了沙粒。他紧闭着双眼,脑袋歪向一边,由于渴,大概在幻觉中伸出舌头舔了一口干沙子,舌尖上沾满了沙子。那位秘书则完全伏卧在沙土上,脸和嘴贴着沙地,似乎进入了渴念己久的幻梦中,两手揪着胸门,大概那里烧得厉害。
老沙头舔了一下发干的嘴唇,长吁了一口气。
“你们呵,何苦受这份罪,为一只沙孤,值得吗?唉,地方选得倒不错,要是倒在沙坡下边,那就跟你们的马匹一样喽!”
老沙头把拐棍扔在一边,蹲下来,在女儿的帮助下把两人一一扶起来。他很小心地把水灌进他们的嘴里。渐渐,他们有了知觉。老沙头把干炒面和在水里,又喂进他们嘴里。
他们清醒了。
“哦哦,是你……老伙计,谢谢你……”大胡子苦笑着说。
那位秘书也连声表示着真心诚意的谢意。
唉,我要你们的感谢有什么用?老沙头默默地站起来,把带来的衣服扔给他们。“穿上吧,这死漠里一到夜里就贼冷贼冷,会把你们这些猎人冻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