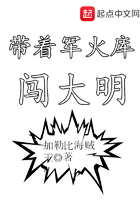河子谷,羽林卫甲营驻守营地南,一与其他营帐,并无太大分别的营帐外,两名羽林卫身披蓑衣,手持长枪而立。
他们警惕的环视四周,但凡有风吹草动,便会握紧手中长枪,时刻准备发出致命一击,纵使雨帘漫漫,亦难遮挡他们的凌厉目光。
营帐中人,身份太过尊崇,他们不敢有丝毫放松。
帐内,被保护之人正是风轩逸,此刻他却盯着案几之上的舆图,双拳紧握,额上青筋暴起,咬牙切齿的模样,好似随时会将那舆图撕碎一般。
“这!他喵的是富坚义博的草稿么!?”看着那令人头大的杂乱线条,风轩逸不由爆了粗口。
有点眼晕的闭上双眼,他抬手拍了拍脑袋,令自己放缓呼吸,好冷静些。
那舆图之上,已然发黄的纸张,被一条条黑粗线条分割成片片区域,依靠黄河那还未鲜明的几字形,勉强可看出这舆图的地点所在。
只是没了熟悉的经纬线,没了代表居民区、独立地物和矿产的点状标识,甚至连表达地势起伏的等高线和等深线都搜寻不到。如何将自己的方位定下,是一个逼死人的难题。
就在风轩逸想要下令,将那绘图之人拉来好好给他教授下高中地理学,关于地图的简单知识之时,门外警卫兵士禀报:“报,大王……呃,不,蒙奇……迪……路飞,”他拗口地结巴言道,“小丑巴基求见!”
风轩逸闻言,原本被那舆图搞得格外不爽的心情,登时好了几分。
他强忍笑意,言了句:“进!”
帐帘被兵士掀开,披着蓑衣的袁志成阴沉着脸,走入帐内。
就在门帘被重新覆上之时,他回头狠狠地瞪了那戍卫的兵士一眼。
那兵士登时变了颜色,苦笑不已。
将蓑衣脱下,置于帘帐一旁,褪下明光铠,身着幞头袍衫的袁志成,快步走上前来,冲风轩逸躬身拱手:“属下袁志成,见过大王。”
“免礼。”风轩逸摆了摆手,随意言道。
“谢大王。”袁志成刻意挤出几分笑容,谄媚言道,“行军营地,太过简陋,不知大王过得是否还适应?”未待风轩逸回答,他便接着开口,“大王放心,再过不到四日路程,我等便可到达怀远,到了那里,大王自可受到优等待遇。”
风轩逸自案几后跪坐下,虽是颇不习惯,却好在小逸原本应常如此跪坐,躯体的肌肉记忆下,习惯使然,倒也不觉难受。
他眉头轻挑,抬头看向袁志成,眼中满是疑惑:“吾何曾说过要去怀远?”
袁志成登时一愣,一时竟不知该如何言语,许久方才陪笑道:“大王您地位尊崇,便是贵人多忘也是应当。您可还记得今日晌午过后,属下与您言说前往怀远的好处?当时大王不是同意了此事么?”
风轩逸陷入沉思,右手手指依次在案几上弹响,那清脆的响声,令袁志成感到心神不宁。
良晌,风轩逸才面露恍然神色:“哦,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袁志成笑得眼睛眯起,连忙附和,“正是那时……”
“吾有答应过么?为何吾记不得?”风轩逸面色倏然阴沉,冷冷言道。
袁志成被这突然变化,弄得措手不及,顿时呆愣当场。
风轩逸不动声色,端起手边茶水,轻轻啜了一口。营帐外,滴滴答答的雨声,甚是清晰。
将茶杯重新置于案几,碰撞之声,甚是突兀。
风轩逸并未等待袁志成回神,便沉声言道:“另外,吾观方才,将军似是对于吾设下之暗语,甚是不解。吾便解释一番,那关于路飞与小丑巴基之称谓,为你我之代号。
为的么……便是你我安全着想。现今吾等安稳虽是无虞,却也需时刻堤防吐蕃斥候。若是被他们发现吾等踪迹,只怕鹰军便会不期而至。而若是,被对方得知你吾二人之所咋,只怕他们最先欲杀死的,便是你吾。
而以意义不明之绰号取代,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密你吾身份。吾如此言说,袁将军可明白?”
袁志成此时方才回过神来,品咂着其中意味,不由感到心惊——七大王对军事竟也有所涉猎,这等保密之法,着实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且这些,也绝非无的放矢,自古至今,大意之下,上将首级被轻易取走之事,并不罕见。
袁志成脸上慌忙堆砌谄笑:“大王深思熟虑,属下着实佩服。”他最是爱惜自身性命,此言出口,倒是诚恳。
风轩逸随意摆了摆手,表示此事,不过顺手拈来。
袁志成为缓和之前尴尬,刻意问道:“只是需请教大王,不知属下绰号,那小丑巴基是甚意味?”他仅知“丑”作地支、时辰或丑角之用,却不知这“小丑”一词是何意。
是笑话你如跳梁小丑一般,愚蠢却兀不自知,还自作聪明,惹人发笑。
心中如此想,嘴上定不会这般说。
风轩逸露出微笑,此等问题,他早有腹稿:“小丑,为可令吾欢笑之意。见到袁将军,吾不就常常欢笑么?”
袁志成听闻这“小丑”二字实为夸奖,脸上笑容愈发浓郁:“能令大王欢笑,实乃属下之荣耀。”
风轩逸微笑点头表示赞许。
袁志成眼见方才尴尬氛围一扫而空,便理了理思路,尝试着开口道:“大王英明,所下决策,皆是高瞻远瞩。只可惜属下愚笨,其中方策,听闻只觉精妙绝伦,却难明其理。故而想要在此厚颜请教,烦请大王指点。”
所谓请教,只怕是来质问的吧。
风轩逸心中如是,却也故作肃然:“不知是何事,令‘聪敏’如袁将军,尚且不解啊?”
袁志成慌忙拱手谦逊:“大王谬赞了,属下着实愚钝,却也因大王所做之事,过于高深。属下生怕会会意错大王方略,引发不必要之错事,方才厚颜前来。”
“嗯,你倒是个会说话的。”风轩逸表情渐趋和缓,口上如此言道。
只是心中如何看他笑话,恐怕仅有风轩逸一人自知。
袁志成喜笑颜开,躬身拱手道:“谢大王夸奖。”沉吟片刻,便开口道,“大王,这第一个令属下不解之事,便是那吐蕃人近在受降城,属下令兵卒昼夜警惕,却不知大王何以令他们轮换休沐?此中深意,属下着实不解。”
这便开始了么?表面说是请教,只是落入口中,便成了质问。
对一向谄媚行事的他来说,此时这般语气,显是对我之前,越过他直接对兵卒下令之事,甚为不满啊。
只是,这等事情,我身为七大王,有必要向你解释?
风轩逸心中冷笑,表面却是做出痛苦神色。大有——你身为吾之亲信,吾之苦心,你怎会不明的模样:“哎!袁将军此言,是怪吾逾越了不成?想来,吾也是唐突了,怎得就心直口快,直接僭越了呢?”
前半句话,风轩逸尚且言出自责之意,后半句话,却已是低沉冰冷。
袁志成闻言,只是片息功夫,便立时明了七大王语意,不由冷汗直冒,话语亦为之结巴。
大王言语之意,其实并不复杂。
归根结底,源于自身身份——身为大王亲卫——羽林卫统领,统兵之权尽皆来自七大王。
而自己方才质问,才是真正有着僭越之嫌。
大王之意,格外明显——你袁志成对此不满,莫不是觉得你手中兵权非我七大王给予不成?
念及于此,他后背衣衫立时被汗水浸湿,他慌忙拱手躬身,告罪道:“回……回大王,属下……属下并无此意。属下一切,皆是大王恩赐,怎敢忘本。”
“嗯?袁将军这般言语,吾便有些听不懂了。”风轩逸手指在桌面敲打,冷笑言道,“不过想必,你是理解吾之苦心了,如此甚好,甚好。你应该,不止这一个问题吧。”
不过一句话,便已如此犀利,纵使表面逃过一劫。袁志成却依旧心有余悸,心中将之前欲以质问之事,考量再三,方才再度开口。
“殿下仁慈,属下却愚笨。只是听闻大王下令,令我等连夜开拔,回返受降城。属下着实不解其中深意,烦请大王点拨。”
风轩逸心下冷哼,虽是不解这袁志成为何不断进言,想要前往怀远之意,但想必对于自己也没甚好心思。即是对方所愿的,那么自己便不可令他如愿。更何况之前猜想若是属实,只怕自己就算身在怀远,也难逃一劫。
他面露肃然之色,却并未直接回答袁志成所问,而是做出思索模样。
许久,方才开口:“这事可就说来话长了。”他抬起头,好似突然发现了什么一般,“咦?你怎得还在行礼?你吾之间,怎需这般?吾难道没让你免礼不成?”
袁志成心知这是七大王故意整他,却难将这话说出口,只得苦笑言道:“回大王,大王……确实未让我起身。”
风轩逸抬手拍打额头:“看吾这记性,来来来,免礼免礼,坐下坐下。”他抬手指了指那案几对面蒲团,言语之中,甚是亲和,“你吾二人,无需这般多礼数。便当作友人秉烛夜谈,你与吾好好说道说道。
对了,另有一事,不久前吾已下令,着令兵士们打点行装,准备回返受降城,此事,你便不必费心了。”
难怪一路之上,看到手下兵士正身披蓑衣,整理行装,原来是这大王再次越过自己下了命令,着实可恼!
袁志成心下恼怒,表面却依旧是喜悦模样。
连忙谢恩:“大王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着实为我等之楷模,还请大王受我一拜。”言毕,他便拱手长揖。
“哈哈哈,不过顺手为之,何以如此多礼。来来来,坐坐坐。”
袁志成再度谢恩,缓步行至案几前蒲团处,跪坐下了身子。
风轩逸心知今日调笑,是时候谈论正事了。
便郑重面容,抬手点指案几之上舆图,问道:“袁将军可识得这舆图。”
袁志成低头扫过一眼,点头言道:“此为我北地舆图,属下身为行伍,对此自是了解。”
“如此甚好,”风轩逸抚掌言道,“吾且问将军,这受降城在何处?”
袁志成心知七大王所说,为舆图上的标识,便抬手点指:“大王请看,我等现今身在这河子谷东南末端,而受降城在我等所在西北,便是这个位置。”他手指移动,落在了一图画为方块的位置,画了个圈。
风轩逸点了点头,记下方位,随即再次开口:“那御守长城又在何处?”
袁志成皱起眉头,这御守长城乃受降城北一防护屏障,用以冬季抵御回纥与东突厥的入侵。
只是这抵御北蛮之事,一直都是卫国公耿典负责,却不知大王何以对此地感兴趣。
袁志成并未多想,抬手指出长城所在。
风轩逸眉头登时紧锁,沉声问道:“不知现今是何年月,又有多少人在此时戍守长城?”小逸目不识丁,只懂听命行事,戍守长城倒是有过几次。只是对于年月,亦是不甚清楚。
“回大王,现今为九月初三,若是耿典那厮活着,此时会有数十勇胜军留守长城,若有异常,便会点燃篝火示警。此时,耿典新死,只怕那长城上人,还未接到他的死讯吧。”
“那么,回纥与东突厥,又大略是何月份入侵?”风轩逸皱眉问道。
袁志成疑惑地抬头看了风轩逸一眼,答道:“多为十一月,初雪之前。若是以往,到了十月末,耿典那厮便会率领勇胜军,并征用受降城中些许百姓,前去戍守长城。”
“那么,若是长城被人刻意毁坏了呢?”风轩逸一掌拍在地图之上,眉宇之间尽是戾气,他终于言出了自己担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