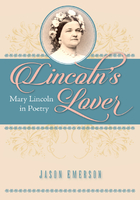冰雪封山,玟原的将士沿着山脉内侧的一处高地上一字排开,而山脉的另一侧,就是即将到来的北丘士兵。
站在瞭望台上的闻人越眺望着远处的景色,是结了冰霜不生一物的贫瘠土地,是没有植被覆盖的死寂的山峦。曾经靖州属于北丘,是玟原想要进攻却难以跨越的地方。如今靖州属于玟原,是玟原轻而易举就能将北丘百姓赶尽杀绝的地方。这片土地是春天都不曾光顾的地方,是没有生机的极寒之地,但因为独特的地形,成为北丘和玟原苦苦争夺的地方。
闻人越一改往日的习惯,换下了他那些花花绿绿让人眼花缭乱的锦衣华服,穿上了一身枣红色的战袍。明明是张扬的颜色,穿在闻人越身上却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庄重肃穆的感觉,带着一种赴死的决心、一种重生的渴望。这样一抹深红的身影孤独的点缀在苍白的空中,好像下一秒他就会一跃而下,携着他的绝望,又从这绝望中生出希望来。
顾越和夏夏守在瞭望台下,听到远处细微的马蹄声,顾越走上瞭望台对闻人越说道:“北丘的人来了。”
“我知道。”闻人越呢喃道,转身回望,好像他的目光可以望到靖州以外的土地,“你说我们会是怎样离开玟原的呢?”
“按照李将军之前给我们的地图,这座山不算太难走,只是约战是在这片高地上,这儿也还算开阔,并不方便我们脱身。”顾越也回首最后忘了一眼玟原境内的万里江山,又把目光放回到即将成为战场的开阔高地,仔细分析道,“我们可以用北丘士兵的衣服做掩护离开,但是很容易被自己人误伤。”
“顾越,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自己人和敌人的说法了。”红衣的男人将双手撑在瞭望台的围墙上,深呼吸了一口,呼出的气立马化为白气在空中飘散,“现在,只有我们两人可以相互信任,至于其他人,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仇人,一切都在一种变数中。你看那些北丘的将士,现在是我们的敌人,可当我们走到这一步时,他们也可能是我们的救命稻草。但是顾越,只有我们,是不变的。”
多年以后,顾越也许已经忘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战役,但他仍深深记得闻人越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但是顾越,只有我们,是不变的”。是的,很多年后,他们依然保存着那份初心,不论那份初心,是为了权力、为了地位、为了金钱,还是为了一份执念。
战争的号角在耳边吹响,顾越跟着闻人越走下瞭望台,夏夏紧跟其后。骑着马走在最前面的玟原太子,飞扬的枣红色衣袖盛着风,持着那杆黑金的、透着红光的长枪,冷冷地看向面前的北丘将士。而这冰冷的目光后,又藏着一丝兴奋,他马上就能得到解脱了,从玟原、立京、皇宫、闻人厉的眼皮子底下解脱出——他将得到救赎。
“顾越,跟紧我,不要和我走散了。”闻人越回头最后嘱咐了一句,然后挥舞着长枪一声呐喊冲进北丘士兵的方阵中去。
其实这样的骑兵阵列对于顾越和夏夏这样擅长双剑的人来说并不具有优势,但顾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左手握紧缰绳,右手从背后抽出一把剑,转首看了眼不远处的夏夏:“夏夏,保护好自己。”
顾越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沉重得就好像是在告别,听得夏夏心里咯噔一下,然后就看到顾越夹着马腹的双腿一收紧,跟着闻人越也冲进了敌方的阵对。而玟原的士兵见到己方的头领已经开始与北丘士兵搏斗了,号角的响声、激昂的鼓点、公子越的呐喊,让这些驻守边疆的将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也挥动着各自的武器,一起加入到这场战斗中去。夏夏看着混乱中又透着某种秩序的人群,也抽出右剑,那马鞭抽了下马屁股,冲着人群中那道月白色的身影去了。
飞溅的鲜血、高低起伏的吼叫和惨叫、不断倒下的马屁和士兵,闻人越杀红了眼,也不管长枪刺中的是谁的心脏,他只感觉到一种无言的爽快,让他忘记了自己是谁。殷红的血染在他的衣服上,与那枣红色融为一体,闻人越找到了自己嗜血的本性,在这一刻,他是和闻人厉一样的人。
精神早已麻木的男人曾一遍遍地问自己,是不是只有和闻人厉成为一样残忍无情的人,才能与他对抗?
“不是的,如果你成为了和闻人厉一样虚伪无情地人,你也会被世人厌弃。就像现在的我们,厌弃闻人厉、仇恨闻人厉。”
顾越曾是这么告诉他的,然后用一杯温茶,抚平了他躁动不安的心。这位孤独的太子回忆着顾越对他说过的话,眼前的景象都变得不真切起来。他停下了不分你我的杀戮,溅到他脸上的灼热的鲜血也渐渐冷却,闻人越平静下来。是啊,现在所有人都是他的敌人,但是他不是闻人厉,应该是天下人皆可为友才对。
“闻人越!小心!”
就在公子越发愣的一瞬间,他的马已经冲到了高地的边缘处,而从这边下去,就是不见底的悬崖峭壁。顾越大喊了一声,闻人越赶忙清醒过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勒紧了缰绳,强行让马匹调转。顾越没命似的驾马赶到太子的身边,气喘吁吁地“吁——”了一声,夏夏解决了身边的几个士兵,也跟着过去了。
他们三人就这么一道离开了战斗的人群,骑着马停在这悬崖的边缘。闻人越还看得过去,血迹在他枣红的衣服上并不明显,但穿着浅色衣服的两人早就全身污秽不堪了。但三人并没有就此脱离战斗,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士兵将他们团团围住,有北丘的人、也有玟原的人。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特点就是手上都拿着弓弩,与混战的其他的拿着或长枪或长剑的将士不同。而弓弩,因为造假昂贵,所以虽然射程远、伤害高,但并未在士兵中普及过。这些人的幕后主使,一定是家财万贯又权势滔天的人,而这些拿着弓弩的人,一定也是冲着他们而来的。
这些人与闻人越他们还隔着一段距离,所以武器上的优势就更加明显。枣红衣衫的男人横持长枪,挡在顾越和夏夏身前,冷笑了一声:“冲着我来的?”
从前只在顾越面前自称“我”的公子越此时舍弃了太子的名头。此情此景下,玟原储君的身份又能带给他什么呢?赤裸裸的伤害罢了!现在的他是闻人越,而现在的闻人越,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而已,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也不代表任何特殊身份。
最前面的、穿着北丘服饰的弓弩手将弓弩对准闻人越,嘲讽道:“公子越还算有自知之明。”
领头的有了动作,其余的弓弩手也纷纷将自己的弓弩对准在悬崖边上的三个人。顾越和闻人越本想就这样趁乱逃脱的,可是世事难料,谁知道会有这么一批人出现。那个人,就这样处心积虑想要他们死吗?而不知所以的夏夏看到这杀气腾腾的阵仗也是吓了一跳,偏头看到顾越握紧的拳和隐忍的面庞,深呼吸了几口,握紧了手中的剑鼓起勇气去看那些来路不明的弓弩手。
“那也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闻人越提着枪向那些人冲去,身体在乱箭中灵活地穿梭。深红的衣袂在寒风中就像一团火,可以在这冰冷的高地上燃烧起来。
但闻人越有这个本事躲闪这箭雨,他身下的马儿可没这本事。很快,那匹陪伴了闻人越数日的马匹哀鸣一声,终于在男人一跃而下后倒在了地上。而顾越和夏夏早就舍弃了他们的马,分心驾马会让他们无法施展最好的剑术。弩箭与剑身碰撞的声音渐渐靠近闻人越,三人紧贴着彼此围成一个半圆,抵挡着离他们越来越近的弓弩手。可弓弩手有十几人,他们三人到底是势单力薄,根本无法与那些弓弩手抗衡。
“嘶——”闻人越倒吸了一口凉气,顾越闻声猛地看向他,就看到他的左肩插着一根弩箭,鲜血渗出的颜色连枣红的外衣都无法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