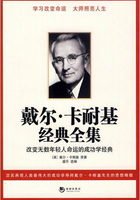织造许开门迎接,进门后,落了座,上了茶。织造许就看到一个大个子把礼物递了过来,也不落座,就直眉瞪眼的问了一句:“你们这个胡同叫猪粑粑胡同?难道这里有粪坑么?”你能体会那种寂静么?就是虽然周围很多人但是落针可闻。织造许很尴尬,李奶奶则因为年纪大,简单的一个后脑勺抽一巴掌:“这孩子也是一个直楞货,这组上这么叫的,那么你舅舅家是大羊毛胡同,你在胡同里可着劲可以给我薅出一把羊毛来?最多也就是薅你这个小兔崽子一脑袋黑毛!”一阵哈哈笑过后,众人也是尴尬尽消。织造许感激的看了李奶奶一样,一切就那么不经意的过去了。
在天津,其实金翺大师姐最近越来越焦躁了,这一天早晨,收到一个口信:事眉目,速来。金大师姐一拍大腿:“得嘞!”然后就收拾物件细软,攒了一个大车,就这么一溜烟儿直奔了北京。进了西便门内,就找到了大羊毛胡同口,就差人就近租院子,手下人也算得力,当金大师姐出门的时候,就已经租好了。
“舅舅、舅妈您好,”金大师姐用的是标准的拱手作揖,男人的那套,漆匠林和林大奶奶都面面相觑——这是找了个爷们?但是,这才开始。
“舅妈?您这是?”金大师姐看着有点真卓了:“被打了?谁打的?我不捶死那个不要脸的孙子!”漆匠林的脸色这会儿已经是黑的可以了,几乎快赶上包拯了。
“舅妈别怕,您说说,是谁?街坊打的吧?还是谁?您只要说出个门道,怎么都能开了这小子!没问题啊!”金大师姐已经在山响的拍胸脯了!这时候,党勉拉了拉金翱,金翱一甩袖子:“你拉我干嘛。”
“我舅妈那是摔得……”
“不能够吧,这样子和上次我抽你时候留下的伤一样!你看这个青色的纹路,就是抡圆了来回的大嘴巴呀!”金翱这会儿本事了,还连走带比划的,把林大奶奶给臊的,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舅妈,您就别怕了!真的,只要您和我说,冤有头,债有主。偶因失脚倒地,至今怨入骨髓。城墙高万丈,也得平地起,要是不能起,我就是楞起,想想前程,思思后路,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正在这里破嘴嘚嘚嘚时候,党勉鼓足勇气给了金大师姐一个脑崩……
后面,林大奶奶觉得没有看清,但是最后画面定格的时候,党勉好像一块儿破布袋子一样,被金大师姐投掷来又投掷去,什么苏秦背剑、燕子三抄水,什么月下追韩信、倒提垂杨柳,哪个叫力劈华山、霸王举鼎……花样翻新不一而足,等金大师姐正在起劲的时候,就听见漆匠林撕心裂肺的一声大喊:“叫大夫……,要杀人了这是!……”
“舅舅别!没事……”,在一个柴垛子上面的党勉依然还是可以站起来:“舅舅,我们常对招没事,就是一些皮外伤,几天就好!您看,我这还有金创药呢!”说着打开一个小布包,里面有一个紫红色的小瓶子,倒出了药面……
“你,你们……”,作为舅舅,漆匠林也是不知道怎么说好了,这就是他么的什么玩意啊!狠狠的一跺脚,就淡淡的飘出一句话:“滚!”林大奶奶和漆匠林过了半辈子,估计下半辈子不出意外还得过,看了一眼,知道丈夫是真的生气了,赶紧拉着俩孩子一路出了大羊毛胡同,在东西找了一个茶馆才歇了歇脚。
“党勉!我亏着你吃了?”
“没呀,舅妈,您对我可好了,打小就特别好。”党勉特别诚恳,这会诚恳的脸上的一坨紫都激动的抖啊抖的。
“好,那么你为什么要毁我?你知道我这个是被你舅舅打的,但是你还让你媳妇这么毁我?”林大奶奶几乎在茶馆包间里都是嘶吼着说的。
“舅妈,我拦您一句,我绝对不是毁您……”,金大师姐张了一句。
“你闭嘴!我不和你说!”林大奶奶努力,其实金翱大师姐是真心的是委屈……
“舅妈,我想,金翱肯定不是毁您……”
在这个茶馆,裕泰茶馆的另一边包间里面,艾贝勒正见载振。
“张千,看看去,该弄走,弄走,哪来的大傻娘们儿……”,话还没说完,张千就已经奔出去了,鸡飞狗跳,一阵女人坐地号丧,掌柜的从楼下噔噔噔上来,又是一阵鸡飞狗跳,然后张千和一个女人动了手。
张千一个呼哨,又窜出来几个人,几下,破窗声,号丧声一下子到了高亢,然后戛然而止。这时候,张千喘着气回来,回了句:“爷,您安排的差事完了。”在这时候,一声花瓶的落地声,让张千肩膀抖了一下。
“艾贝勒,要不然,咱趁着还没点单,换个地方坐坐?”
“换个地方坐坐!”说着,拿着扇子就提着大褂走下了楼,这时候载振狠狠剜了张千一眼。换了车,从东长安街一直向西,然后到了载振的老根据地。
西四,文宣楼茶社。
黑长衫还在,载振正进门的时候。
“我听说谭嗣同去天津了?”
“还不是又去找他了……”,说着,黑长衫两手比划了一个圆圈。
“靠谱么?我觉得这人不靠谱啊……”,这时候另一个花纹靛蓝长衫支了一句。
“个人觉得,有兵,有权!”黑长衫是那种自信的玩意了:“据说谭嗣同看上了他的七千新军,您知道么?七千战力斐然的虎贲!”
“拦您了,您知道北京城多大么?那么点人够个屁,就是都进京城来看厕所都不够吧!”一个瓜皮帽绝对的不屑。
“在京城看什么狗屁厕所呢?去颐和园呢,一个园子怎么样都可以搞定了,三千截断京城到颐和园的路,四千新军直扑颐和园……”,正说到这里,就看着一个黑色的官靴,自下而上直接踹到了黑长衫的脸上。黑长衫,就是那么脆声,说倒就倒,还是横飞出去的。艾贝勒都看着载振的腿,都心生佩服,举起了大拇哥。
“滚!付了银子,滚,四六不通,你们,就你们这些玩意,还聊国事呢?”载振叉着腰骂街。
掌柜的趁这机会,挨个收了银子,而且还不找零。谁也没见过这么横的掌柜,就是载振的买卖,其他人还不能!
“我想和您说说,”张千嘟囔了一句。
“说!”
“刚才那几个人不是一般人!”张千一下子就来了精神:“拳脚路数很熟悉,和上次红灯照拐孩子那几个人的套路几乎一样,您看看是不是叫上巡城?”
“滚,该干嘛干嘛去!”这时候载振其实气性已经平复了下去,拉着艾贝勒一起上了楼。在自己的天字号包房里面,继续的骂骂咧咧,艾贝勒也不劝,但凡这时候最好别劝,因为劝了以后都是麻烦,你是说还是不说?随着说,也没辙啊,不说到好,一会无趣了,载振也就不张罗了。
“你说,我阿玛怎么那么贪呢?嗯?您说说,这就三百多个位置,值钱的就四十个,怎么一下子老爷子怹都给收了?那么多银子呢!本来我还想买辆新车,一下子都黄了。”载振心思其实不是这个,气性大更不是因为几个毛贼或者几个碎嘴子。
“王爷一定有自己的用意,再说,我说说您咂摸咂摸,”艾贝勒自己沏茶喝了起来,载振顺势把自己的茶碗推了过去:“您护不住这么多财啊,上上下下的嘴不得说死您?王爷他老人家现在正是主子老佛爷心头的时候呢……”。
说着,呵呵了几声:“振贝勒,您就不用我再说了吧?”
张千一门心思就是想拉着邢副尉一起去玩,之前的事情让他还是余味未烬。在皮裤胡同西边的胡同口,升了官的刑副尉还在内堂坐着,除了旁边的一个榆木牌子变化了以外,一切照旧。
“您这个衙门也忒破了……”
“不修衙,这是老规矩了,您先破了呀,可以活动活动,您出去就得了……”刑副尉今天脑仁疼,不想和这个二百五斗嘴。
“啧啧,您今天是吃枪药了?”
“兄弟,哥哥我真的是懒得和你逗趣儿了,一脑门子官司,烦死了。”
“哥哥,您也叫我兄弟了,您说说……”张千这会儿一脸的仗义相。
“升官了吧,还是一个羁盗拿案的捕头呗,至少上差怹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不”,指着旁边一片有着红圈的宣纸:“一季度内需要缉拿要党至少两名!什么玩意儿叫要党?都是闻香、红灯一个省的大脑袋才算!要是有革命党,那更好了,只是革命党你分不清啊。唉,愁死哥哥我了!”
“哥哥,你请我喝酒吧,”张千这时候不动声色。
“滚蛋,我哪还有什么想法心念去喝酒啊”。
“最好是汾酒,但是需要来一壶黄酒先垫垫肚子。”张千继续。
“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
“我想吃烧羊肉,但是城里的羊肉馆子都不好,我们去羊坊吧……”
“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呢?”刑副尉气乐了。
“哥哥,因为我要送你至少俩要党啊……”张千一脸诚恳的对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