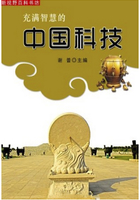詹沛得了信,顿时起了同样的担心,恰巧詹沛刚引兵归营不久,周知行知其疲倦,便没有安排太多事务给他,于是詹沛次日天不亮就出发,傍晚便到了萝泽。
“人住在哪个驿站?”詹沛一见郑楹,来不及寒暄,便问起来投之客。
“天快黑了,你这么急着见他吗?那我叫徐三领你去。”
詹沛点了点头,道:“毕竟是郑峦的人,我还真有些迫不及待想见见。”
郑楹闻言,立即吩咐使女陌如去唤徐三前来,又熨帖地问詹沛道:“路上辛苦,进屋先喝口水吧?”
詹沛笑着摇了摇头:“不必,我就在此处等徐三过来,你快先回屋吧,日头下去了,天凉。”
“无妨,我待会送你到门口……”
詹沛赶忙抬手再次示意不必,道:“不必送了,我明日一早就来看你,快回屋吧。”
说话间,徐三已一路小跑着赶了过来,两人便准备离开前往驿站。郑楹再请相送,詹沛只是不许,郑楹无法,只得怏怏回屋去了。
詹沛看郑楹进了屋,才回身急匆匆走出大门。徐三小跑着跟上,一出门就被眼前景象吓了一跳——府门外,正候着二三十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兵士,个个披盔戴甲,静默无声。
詹沛跨上马背,指了指徐三,向随从道:“诸位,请跟着这位向导,走吧。”一声令下,队伍便开始有序前行。
——————————
驿馆里,蒋相毅等人正准备吃晚饭,忽闻外面传来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蒋相毅与任宣面面相觑,猜想是冲自己而来。果不其然,脚步停在门外,紧接着便是笃笃的敲门声。
任宣去开了门,见是一群戎装持械之人,未及开口,只听对方为首之人先抱拳作揖,冷言说道:“听闻贵客从京城远道而来,在下特来拜会,不揣冒昧,还请见谅。”
任宣向妻子使了个眼色,妻子赶紧带着家小离开。詹沛向两个幼童微微一笑,又向任妻点头致意,侧身让出一条道容几人过去,然后一步踏入门内,留一众手下候在门外。
“不知搭救王女的恩公是哪位?”?詹沛朗声问道。
蒋相毅起身应道:“正是不才在下。”
詹沛立即抱拳,刚张嘴说了个“多谢”,却似乎觉查到什么异样,仔仔细细盯住了对方,抱拳的手缓缓松开,向后一步又退出屋外,一挥手命令手下道:“将此二人捆了。”
任宣下意识想拔刀,被蒋相毅按住:“他们人多势众,且随他去。我料定不会有事。”蒋相毅虽如此说,心里却七上八下——难道竟被看穿?
蒋相毅的担忧一点不错。从一进门,詹沛就注意到蒋相毅眉宇间豪气与煞气并存,绝非寻常杀手。待蒋相毅站起身来,詹沛得以看清他的身形体廓,发觉竟与印入脑髓的仇人身影隐隐相合,再回想他方才讲话的声音……
詹沛遽然抬头,对视的刹那,詹沛几乎完全确认了对方正是那个当年自己抵死相搏的刽子手——身形体廓、声音眼睛,都跟那晚月下所见相吻合。
“呵……”詹沛笑出了声,破天荒地红了眼道,“没有白费,没有白费。”
蒋任二人正摸不着头脑时,詹沛又挥手令手下退出屋外。
“四年来,不论白天夜里,稍一得闲,我都会闭目重现你的眼神声貌、身形体格,生怕忘了这仅有的识别出你的线索,我这番努力看来没有白费。”詹沛说着走上前,进行最后的确认——他一把扯开蒋相毅前襟,右肩上,一条触目惊心的刀疤赫然显露。
“你、你是……”蒋相毅震惊地问道。
“我曾是王府护卫,那晚跟你交过手,对你来说只是无名小卒,你当然记不得。”
“哈……”蒋相毅苦笑着,大摇其头,“本想来讨个生路,竟撞在了刀刃上,看来真是天要绝我,我无话可……只有一句话——我是淄衣侍总使,当年薛王案是我造的孽,与我这任宣贤弟无干,我死后,还请你不要为难他和他的家人。”
詹沛却道:“听说,你是经他提醒才免遭毒手,还听说他宁可舍弃生计前途,也要救你,心甘情愿带着家人随你奔波逃命。这般讲义气,想必曾共过患难?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是……同僚、下属?”詹沛试探地问完,又转向任宣问道,“那么,当晚你也在杀手之列吧?”
“不,他不在……”蒋相毅抢着为任宣辩白。
“来人!”詹沛高声朝外唤道,丝毫不理会蒋的辩白。
一群手下呼呼啦啦进来,詹沛下令:“把右边这位及其家小带去长风居,好生安置。”
任宣还没琢磨透当下局面,一句话没来得及说就稀里糊涂被带走了。
“你要对他做什么?!”蒋相毅惊问。
“放心,我要对付他还需瞒着你?”
蒋相毅不再接腔。
詹沛走近,低声询问道:“当年薛王案,淄衣侍全盘行动是谁策划?”
“是一位名叫詹盛的高官,已经亡故了。”
“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不大清楚,据说是误用药酒。”
詹沛本想从他嘴里先弄出些有关父亲生死下落的线索,而蒋相毅显然对此知道的不多,亦或是不想说。
“看你应三十有五?”?詹沛忽冷不丁问及琐碎之处。
“三十三。”
“为郑峦效命多少年了?”
“十五年。”
“做淄衣侍多少年?”
“十五年。”
“这么说,你十八岁就选入淄衣侍?果真是天纵奇才。那你,明里是什么官职?”
“兵部,团练使座前点校。”
詹沛点了点头,问道:“你虽杀害主公,却有恩于二娘,又这般有本事,你可愿归顺础州,为周大帅效命,赎你之罪?”
“不愿。”
“为何?”
“我受陛下厚恩,就算形势所迫不能再为其效忠,也决不会做有损旧主之事。再说,我既食君禄为君分忧,有何罪要赎?”
“真够忠心的。”詹沛冷嘲道。
“你不也一样?”蒋相毅反唇相讥。
詹沛一笑置之,沉默了好一会,忽道:“听你意思,我留你一命,于础州并无好处?”说着,眼神变得狠戾起来,似有杀意涌动。而蒋相毅毫无畏惧与他对视,嘴角牵起轻蔑的冷笑——身为淄衣侍,哪有怕死的?
此时门外忽然传来杂乱的人声和脚步声,不难听出是郑楹来了,而且不等人报便要进来。詹沛打开门时,郑楹恰好走到门口。
“济之,听说你……”郑楹刚开口,就看到了屋内被缚于立柱面无血色的蒋相毅,露出诧异之色。
詹沛对两名没敢拦阻郑楹的手下挥了挥手,未做责备。两人赶忙称谢退下。
郑楹匆忙走近蒋相毅,确认他没有受折磨后,转身对詹沛不满道:“济之,这是怎么回事?蒋四叔是我的恩人,又千里来投,你怎能如此慢怠他?”
詹沛叹了口气,关上门,走到郑楹跟前解释道:“蒋大侠功力深厚,你叫我来问讯蒋大侠,我当然先要保证自身安全,否则万一哪句话得罪了蒋大侠,我只怕要当场毙命。”
“谁……谁叫你问讯了。”郑楹面上有些过不去,一脸的难为情。
詹沛低头一笑,配合地为女子稍稍粉饰道:“你写信叫我速回萝泽拿主意,我总要问一问才好决定吧。”
郑楹“哦”了一声,继而呆立原地,半天也想不出应该再说些什么,目光逡巡间恰巧对上蒋相毅的眼神,连忙急急避开,使得气氛尴尬不已。
詹沛等候片刻,见女子实在无话,便凑近些试探着问道:“那你……就先……回去吧?”
郑楹听詹沛逐客,只好移步向门边走去,心里对蒋相毅仍旧满是担忧歉疚,走到詹沛身旁时,又驻足交待道:“蒋四叔有伤在身,经不住这样一直折腾,望你尽快决定。决定之后,留也好,不留也罢,都不可有丝毫慢待。蒋四叔虽曾为郑峦卖命,可毕竟救过我,你实在信不过,就多多给他们一些钱,请他们再寻别处投靠。”
“都听你的。”
郑楹一脸歉意地向蒋相毅微一颔首,转身离去,走到门口再次驻足,转身向詹沛道:“你若不留蒋四叔,他们临行前,我要亲自相送的。”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别想私杀蒋相毅。
詹沛见她又明摆着信不过自己,不由想到冯旻之事,便有些不客气地直冲其言下之意回应道:“你多虑了。”
郑楹却没听出对方答话之中的情绪,满意地推门离去。?屋内,再次只余两个各怀心事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