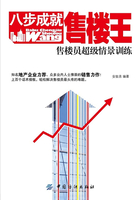本书系“企鹅欧洲史”系列中的一卷,讲述了1815—1914年的欧洲史。上一卷《追逐荣耀:1648—1815》(2007)涵盖的历史时期是1648—1815年。正如那本宏著的作者、我在剑桥大学的同事蒂莫西·布莱宁所言,讲述任何一段欧洲史都必须武断地选择一个起始点,只不过有些起始点比其他起始点更武断。人们对“19世纪”或“20世纪”的提法已习以为常,而历史学家知道,1801—1901年或1901—2000年除了表示年代的先后顺序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历史充满了未解的问题,包括本书在内的许多历史作品都结束在重大战争的爆发和结束上,但即便是这些战争,也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解释。历史作品的侧重面不同,历史分期的方式也会不同。政治、军事或外交史上的某个重要日子在社会、经济或文化史上可能无甚意义。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通常认为,在欧洲很多地区,一直到进入现代之后很久,历史发展得极其缓慢,也就是说,虽然18世纪末欧洲政治体系的旧制度已经覆亡,但旧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半叶。举例来说,直到19世纪后半叶,农奴制度才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绝迹;直到1850年后被称为“人口转折期”的几十年,多年形成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人口模式才开始发生变化,法国除外;1850年之前,工业化仅限于欧洲经济的小块地区,影响微不足道。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传统贵族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该观点的代表是阿尔诺·迈耶(Arno Mayer)的《旧制度的韧性》(The Persistence of the Ancient Regime)(1981)一书。依照此观点,尽管这一时代看上去动荡不安,但政治领域内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同意迈耶的观点。19世纪的欧洲无疑不乏变革,除了政治领域,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
有些人甚至认为,最值得研究的历史年代是“革命的年代”。这一提法来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年代四部曲》的首卷书名,这套书讲述了1789—1991年的历史,首卷《革命的年代》是1962年出版的。乔纳森·斯佩贝尔(Jonathan Sperber)撰写的《革命时代的欧洲》(Revolutionary Europe)(2000)沿袭了霍布斯鲍姆的历史时期划分法,研究1789—1848年的历史,那正是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涉及的年代范围。然而选择这段历史时期并非没有代价,在之后那段时期里,欧洲面貌发生巨变,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框架来概括。斯佩贝尔撰写的第二卷书名很长,是《1850—1914年的欧洲:进步、参与、忧恐》(Europe 1850—1914: Progress, Participation and Apprehension)(2008)。毫无疑问,冗长的书名反映了他为寻找一个统一主题而颇费心思。霍布斯鲍姆后来又写了两卷,分别是《资本的年代》(1975)和《帝国的年代》(1987)。前一本涵盖1848—1875年,后一本从1875年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讲述同一历史时期的所有历史著述中,霍布斯鲍姆的这三本书高屋建瓴,任何想撰写19世纪欧洲史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三部历史宏著。霍布斯鲍姆长于在概念上推陈出新,他将这三部作品涵盖的历史时期称为“漫长的19世纪”。此后出版的诸多教科书和历史入门读物纷纷效仿,比如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和马丁·琼斯(Martin Jones)合著的《欧洲史:1783—1914》(Europe 1783—1914)(2000)。然而,漫长的19世纪是一个断裂的世纪,1848年革命浪潮将其分割为迥异的两段。无怪乎撰写从法国大革命或拿破仑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历史的诸多历史学家不再试图找到任何统一概念,改为选用四平八稳的书名,比如R. S.亚历山大(R. S. Alexander)为他不久前撰写的一部政治史起的名字——《欧洲前途未卜之路》(Europe’s Uncertain Path)(2012)。
20世纪大部分年代,历史学家把民族国家的崛起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视为19世纪欧洲史的主要特征。民族主义的胜利塑造了新的政治文化实体,激起了对似乎过时的庞大的多民族帝国的反抗,也鼓励人们反抗其他民族的压迫或控制的野心。20世纪时,世界各地的国家都采用了民族国家模式,因此探究民族国家19世纪在欧洲的崛起更加意义重大。历史学家一度积极评价这一进程,把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捷克和波兰民族意识的增强以及民族主义时代的其他现象作为其著述的核心内容加以颂扬。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的兴起蒙上了一层阴影,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就是其阴暗面的表现。此后,世界逐渐进入全球化时代,冷战时期的障碍纷纷坍塌,各种国际机构、世界范围的通信、跨国公司等诸多因素侵蚀了国家边界,开始把各国人民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全球人类共同体。自20、21世纪之交以来,这一现象改变了我们对以往历史的看法,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从全球视角审视历史。撰写全球史的呼声本身并不是新现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Marc Ferro)就曾呼吁撰写全球史;19世纪的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20世纪的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也在著作中体现了“普遍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的观念。不过直到近年,才出现了把世界各地区连在一起而不是割裂开来的世界史。历史学家开始对种种专题开展研究:帝国对欧洲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尤其是英国,但不限于英国;把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连接在一起并使其相互影响的全球经济纽带;作为欧洲的普遍进程而非某个欧洲国家特有的全球帝国的崛起。历史学家还忙于从全球视角重写欧洲各国的历史,强调欧洲移民社群——移民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欧洲人——对“母国”的影响,研究源于殖民亚洲和非洲经历的种族理论对欧洲民族主义的影响,探讨全球地缘政治如何成为欧洲各国间关系的主要因素。
我写作本书的方式深受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影响。他撰写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2009)堪称一部真正的全球史,而不像霍布斯鲍姆的那三卷著作那样以欧洲为中心。《世界的演变》一书研究19世纪的历史,各章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记忆和自我观察、时间、空间、人员流动、生活水准、城市、边疆、权力、革命、国家、能源、职业、通信、等级制度、知识、文明、宗教等等。奥斯特哈默有意选择了一些常见主题,比如全球各地区间的联系、共同发展过程和全球进程。然而,总体来看,此书过于突出作者本人的观点和个人思考,盖过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和思考。此外,该书在概述历史时,往往一心建立阐释历史的大框架,而不是力求通过时人的生活经历了解历史。如果是一本简明教科书,这样写也许可以理解,毕竟教科书的最终目的是辅导学生应付考试,但是像该书这种主要针对普通读者的大部头作品,其实可以用更长篇幅来描述反映历史时期特点的细节,既收录读者感到陌生的内容,又谈他们熟悉的史实,而且应该尽可能地让那一时代的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
大致同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全球史著作,其涵盖内容之广不亚于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但对19世纪的描写与奥斯特哈默的大相径庭,这些作者认为,正是在19世纪,欧洲开始引领世界、称霸全球各地。一些历史学家借助大量比较证据,从各个方面论证18世纪初世界各地的文明从生活水准到文化成就大致处于相同水平,这方面的作品有已故的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的力作《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2004)和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讲述全球帝国的宏著《帖木儿之后》(After Tamerlane)(2007)。1700年前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中国的大清帝国、尚未沦为殖民地的非洲贝宁帝国及邻近的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等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与欧洲大体相当。到181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欧洲遥遥领先。欧洲之所以领先,并不像一些历史学家——比如写下《文明》(Civilization)(2011)这一全面论著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说,是因为欧洲具有内在优势,而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结果。直到20世纪初,欧洲在很多领域的领先地位都得到了保持和扩大,但如后文所述,欧洲的领先地位日益受到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撼动了欧洲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将其摧毁,战后欧洲的全球帝国土崩瓦解。我认为1815—1914年在欧洲历史上是一段独特的有意义时期,主要依据就是欧洲在这一时期称霸全球。本书始终强调全球背景,也会论及欧洲之外的事件和进程,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这一百年里发生在欧洲的历史事件。
全球史也意味着跨国史。很多介绍欧洲史的著述基本上是分别讲述不同国家的历史。阿瑟·格兰特(Arthur Grant)和哈罗德·坦珀利(Harold Temperley)合著的《19世纪的欧洲》(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27)可以归入这一类;威廉·辛普森和马丁·琼斯合著的《欧洲史:1783—1914》也属于同一类,书中各章分别讲述了法、德、意、俄和哈布斯堡帝国史。德国史学家米夏埃多·萨莱夫斯基的《欧洲史》(History of Europe)(2000)的副标题是“国家与民族:从远古世界到今天”,该书分别讲述了一些国家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读者基本上看不出是什么把欧洲联结为一个整体,这些国家具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外部环境和事件对它们产生了影响。权威但仍不够完整的《牛津现代欧洲史》(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的编写手法也大致相同,每一卷分别讲述一个国家,只有4卷例外,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希望通过本书说明的一点是,欧洲不仅是不同国家演变而成的松散聚合体,也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共同体。我所谓可以界定的共同体,指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欧洲的东部界限尤其模糊不清,难以界定,欧洲的社会和文化界限因欧洲人大规模移民世界其他地区也变得模糊难辨。在以上前提下,最好是把欧洲视为一个具有多重共同特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区,西起英国和爱尔兰,东至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
我尽量从跨国的角度讲述历史。我这样做是有意仿效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他是19世纪末《剑桥近代史》丛书的发起人。阿克顿筹备出版该丛书时告诉撰稿人:
普遍历史不是各地历史的总合,而是首先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核,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宗教战争、绝对君主制、大革命等等。几个国家对历史主流也许有影响,也许没有影响……但不应分散注意力,把葡萄牙、特兰西瓦尼亚、冰岛放在与法国和德国同等重要的地位……我打算打破罗列各国历史的做法,尽可能讲述超越国家边界的普遍历史。
阿克顿未能实现这一宏大设想就撒手人寰了。在效率很高但想象力不足的阿道弗斯·沃德(Adolphus Ward)爵士的主持下,《剑桥近代史》最终问世。这部史书基本上采取了分国叙述的手法,反映了年青一代史学家身处欧洲变化的政治文化氛围,从国家角度审视欧洲史的做法。直到苏联解体,欧盟涵盖东欧大部分地区,加上全球化再次蓬勃发展,才有了撰写一部真正的欧洲史的可能。然而,再也不可能像格兰特和坦珀利等史学家那样,把这部欧洲史写成一部欧洲各国政治史和国际关系史了。至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历史研究拓宽了眼界,几乎涵盖了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霍布斯鲍姆就已经在《革命的年代》中分章讨论宗教、意识形态、科学、艺术、经济及其他专题了。奥斯特哈默列出的专题清单显示,此后的历史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范围。近年出版的新著还纳入了地貌史和环境史。霍布斯鲍姆用宏大叙事把不同主题串在一起,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决定性影响。然而,21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们无法采用这种手法,因为宏大叙事已经深受诟病。正如蒂莫西·布莱宁所言,我们能做的仅是探究“历史发展的线索”。
布莱宁为1648—1815年这段历史时期找出了两条发展主线,他称之为“国家不断追求霸权”和“公共领域这一新型文化空间的出现”。这两方面的发展在19世纪得到了延续,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18世纪几乎难以想象。1785年的欧洲人如果看到1815年欧洲王朝复辟时期出现的国家体制,依然不会有陌生感,虽然表面现象往往具有欺骗性。1815年,国家权力及对公众生活的干预仍然很有限;公众对政治事务的参与仍然很少,尽管不久前的法国大革命树立了生动的范例;公共领域的范围依然局限于受过良好教育、文化水平较高、人数很少的社会阶层及其组织,包括出版社、咖啡馆和读书俱乐部。然而到了1914年,国家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实现了男子普选,欧洲部分地区还实现了妇女普选;公众直接参与国家、地区和地方政策的制定,一个重要的参与方式是通过有组织的政党。与此同时,国家大大强化了对自己公民的控制,从教育到医疗,从兵役制到社会工作。
布莱宁描述了通信进步与经济增长并驾齐驱的发展过程。19世纪,这两个进程发展提速,速度之快是18世纪的人难以想象的。1815年,铁路、电报、汽船和照相技术刚刚出现在历史地平线上;到1914年,欧洲已然步入电话、汽车、收音机和电影的时代。1815年,我们仍然处于牛顿宇宙观、具象艺术和古典音乐时代;到1914年,爱因斯坦已经提出了相对论,毕加索创作了立体派艺术画作,勋伯格谱写了他最早的无调性音乐作品。从更现实的意义上讲,欧洲正步入机枪、坦克、潜艇和战斗机时代。1911年意大利入侵利比亚时,首次使用飞机轰炸了敌军;英国人和德国人分别在南非和西南非(纳米比亚)建立了最早的集中营。以上发展预示了20世纪上半叶的大规模杀戮和毁灭,警示我们不要像19世纪大部分人那样,把19世纪看成一个持续进步、具有无限改良空间的时代。进步是有代价的。如伊恩·克肖(Ian Kershaw)为“企鹅欧洲史”系列撰写的下一卷《地狱之行:1914—1949》所述,从1914年到1949年,欧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谈到绝大多数欧洲人的生活状况,布莱宁写的这一卷以悲观调子结尾。产业的诞生和人口迅猛增长产生导致“一种新型贫困的出现……不是因饥荒、瘟疫或战争突然袭来而遭受的苦难,而是长期营养不良和就业不足的状态”。相对而言,19世纪的欧洲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饥荒、瘟疫和战争,我将在本书中解释其原因。和这段时期的众多其他方面一样,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有过饥荒,尤其是在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俄国,也有过瘟疫,不时暴发的霍乱就横扫欧洲大陆。不过,无论饥荒还是瘟疫,都没有此前一些年代发生得那样频繁,也没有带来昔日那种毁灭性的后果。19世纪末,饥荒和瘟疫基本上在欧洲绝迹。
然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不平等并没有与饥荒和瘟疫同时消失。本书将勾画出19世纪不平等现象不断变化的轮廓。农奴制等旧日的不平等形式让位给新型的不平等,比如工厂工资劳动制。可以把19世纪视为一个非凡的解放时代。数百万人获得了更加平等的地位,包括大多数农村人口、妇女,以及宗教上的少数群体,尤其是犹太人。本书将详细分析这种巨大变化并解释其原因。然而,平等和解放是局部的、有条件的,1914年后的年月将表明这一点。讲述人在获得解放过程中受到的种种羁绊,也是撰写19世纪欧洲史的史学家的一项主要任务。
围绕不平等的种种论争是19世纪欧洲政治的焦点。法国大革命留下了种种理念,以此为基础,越来越多的政治思想家和践行者开始构想并试验消除他们目睹的不平等现象的办法。解决方案五花八门,从贵族家长式统治和“位高则任重”论的一个极端,到无政府主义者试图摧毁国家体制的另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种种思想理论对剥削压迫下了不同的定义,也据此强调把人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解放出来的某一种方式。看重稳定和社会等级制的人认识到,顽固维护旧秩序是死路一条,至少大部分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也参加了围绕不平等展开的大辩论。宗教为源于世俗世界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各种答案,有的干脆宣扬避世观念。种种思潮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点:渴望获取并行使权力,以便把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蒂莫西·布莱宁把他撰写的1648—1815年欧洲史起名为《追逐荣耀》,意指该时代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荣耀,本书则定名为《竞逐权力》。
对权力的追求渗透19世纪的欧洲社会。国家争夺世界权力,政府追求帝国权力,军队加强自身的军事权力,革命家密谋夺取权力,各政党竞逐执政权力,金融家和工业家追求经济权力,农奴和佃农逐渐挣脱占有土地的贵族的武断权力。19世纪最重要的社会进程——受压迫的各阶层人民挣脱了压迫者权力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妇女摆脱了把她们置于男人控制之下的一整套法律、习俗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权主义者争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工业化的新世界,工会继续争取在薪酬和工作条件上有更大发言权,不断发起罢工;现代主义艺术家对学院派的权威提出挑战;小说家把家庭等社会组织内围绕权力展开的斗争作为自己作品的核心内容。
19世纪,社会驾驭自然的能力增强了。各国政府开始有能力应对饥饿和火灾、水灾等自然灾害。医学研究人员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追求战胜疾病的权力。工程师和规划者疏导河流,排干沼泽地的水,逐走野生动物,夷平森林,他们建造城镇,修建铁路和下水道,造船架桥,把人类的权力延伸到自然界。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发利用新的动力源,从蒸汽到电力,从动力织机到内燃机,从而获取了权力。权力的表现形式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有的权力通过暴力行使,有的则靠说服手段,有的权力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有的仅获多数人支持,权力可以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宗教、组织等形式表现出来。在1815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看重的是荣耀、荣誉等,而在19世纪,人们越来越看重权力。19世纪末,权力的概念带上了种族主义色彩,欧洲人把自己称霸世界各地视为他们高当地居民一等的佐证。本书将重点阐述以上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探讨欧洲各国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影响了欧洲与亚洲、非洲及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后者如何影响了前者。
本书分8章,每章分10个小节。第一、三、七、八章主要讲述政治史,第二和第四章讲述社会史和经济史,第五和第六章讲述或许可以泛称为文化史方面的内容。第一章讲述的政治史起自1815年最终打败拿破仑,终于1830年革命浪潮的最后一波余震。第三章续第一章之尾,讲述1830年到1848年革命的历史,也探讨革命浪潮的后果:冲突频仍、动荡不安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初。第七章分析1871—1914年欧洲各国是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民主挑战的。第八章,也是最后一章,讲述了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征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过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降临后,征服给欧洲自身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上述各章均依循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展开。夹在第一和第三章之间的第二章讲述了1815—1848年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不过若要全面讲述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变化——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农奴获得解放,则需要把农村地区直到1914年发生的一些变化包括在内。第四章涉及自19世纪中叶起欧洲的主要社会经济结构,以及这段时期内这些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五章涵盖了整个这段时期,讨论了社会试图驾驭自然界的努力,从改造欧洲大陆上的荒山野林和河流,到努力控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人性。第六章把这一时期描述为情感时代,将其与之前的理性时代做了对比,探讨了具有情感时代特征的形形色色的精神、宗教、信仰、文化、教育观念和人类概念本身。
为了强调这段历史中人的一面,每章都以一个人的亲身经历开头,这些人的信仰和人生经历提出了供各章探讨的很多问题。8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四男四女,这是我有意安排的。这段历史时期内,妇女人数超过欧洲人口一半,历史上的其他年代几乎也是如此。这段时期内的另一基本特征同样重要:即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欧洲绝大部分人仍然住在农村,靠务农维生。19世纪期间,欧洲的农民、农场主和地主常常被边缘化,尤其在工业社会兴起的地方,但我认为,若说这数百万人都处于马克思所谓“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或说他们仅仅是历史变革的受害者,那就大错特错了。
本书宜按顺序从头到尾阅读。为了与这套丛书的总体结构保持一致,我没有在书中添加任何脚注和尾注。写作这样一本综合性论著,必然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作者的著述;本书原创内容只有所提出的论点和做出的诠释,以及主题的选择和排列。但愿诸多史学家能原谅我引用他们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著述内容却不注明出处。不过,至少请允许我列出每章开篇讲述的个人故事的出处(详见“推荐阅读”):The Diary of a Napoleonic Foot Soldier, ed. Marc Raeff (New York, 1991); A Life under Russian Serfdom, transl. and ed. Boris B. Gorshkov (Budapest, 2005); Máire Cross and Tim Gray, The Feminism of Flora Tristan (Oxford, 1992) and The London Journal of Flora Tristan, transl. and ed. Jean Hawkes (London, 1992); Hermynia zur Mühlen, 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 transl. and ed. Lionel Gossman (Cambridge, 2010); Wendy Bracewell, Orientations (Budapest, 2009); Brita K. Stendhal, The Education of a Self-Made Woman (Lewiston, NY, 1994); Martin Pugh, The Pankhursts (London, 2001); Ivor N. Hume, Belzoni (Charlottesville, VA).本书中的大段引用内容多出自原始资料,但有如下例外:第546—547页引文出自Dirk Blasius, Der verwaltete Wahnsinn (Frankfurt, 1980),第551—554页引文出自Andrew Scull, The Most Solitary of Afflictions (London, 1993),第562页引文出自John A. Davis, Conflict and Control (London, 1988),第746页引文出自F. S. L. Lyons, Charles Stewart Parnell (London, 1977),第783页引文出自Hartmut Poggevon Strandmann, 'Domestic Origins of Germany’s Colonial Expansion under Bismarck', Past and Present, February 1969,第792—793页引文出自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London, 1960),第795—796页引文出自Edvard Radzinsky, Alexander II (New York, 2005),第858页引文出自Adam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New York, 1998)。
2009年,我开始动笔撰写此书。其实我在几所大学讲授19世纪欧洲史时,已经产生了写作此书的念头。1998年我迁居剑桥后,兴趣转向20世纪史。多年来我先后在以下大学讲授19世纪欧洲史:苏格兰的斯特灵大学、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诺里奇市的东盎格利亚大学、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以及最近几年我执教的伦敦市的格瑞萨姆学院。我很幸运,可以在所有这些课堂讲授的过程中汲取素材。我感谢以上大学的学生在我的课堂和研讨会上耐心倾听我的观点,他们发表的意见帮助我补充或修正了自己的论点和总体研究方法。倘若我的研究工作没有得到协助,我绝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内容如此丰富的一部著述。我尤其感谢我以前的学生丹尼尔·考林、尼雅姆·加拉格尔、蕾切尔·霍夫曼、祖西·拉达、乔吉·威廉斯给我提供的资料。2012年,剑桥大学历史系和沃尔夫森学院允许我请学术假,让我获得宝贵的时间来写作此书。每当我需要查找涉及很多专题的资料时,首先会去藏书浩瀚、工作人员热忱相助的大学图书馆。
很多友人和同事审阅了全书或其中部分章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匡正了书中一些错误。企鹅出版集团的西蒙·温德尔是一位资深编辑,他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我还要深深感谢以下各位:蕾切尔·霍夫曼仔细阅读了第一、三、六章,戴维·莫塔德尔对第二、四、五、七、八章做了很多更正,乔安娜·伯克对第五章的评论至关重要,蒂莫西·布莱宁、露西·里亚尔和阿斯特丽·斯温森审阅了整部书稿,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书中若有任何错误,责任全在作者。塞西莉亚·麦凯在挑选插图上给予我宝贵帮助,这些插图为书中讨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挑选的插图依循了各章的先后顺序。如果读者愿意,可以很容易在互联网上找到书中提及的插图和照片。安德拉斯·拜赖兹瑙伊再次证明自己是一位博学有趣的制图专家。理查德·梅森始终是一位工作细致的文字编辑,更正了诸多错误,本书几处文字经过他的润色更加通俗易懂。克里斯蒂娜·沙特尔沃斯编制了一份极全的索引。理查德·杜吉德担负了全书的编辑工作,我谨对他致以深深的感谢。正字法上存在的几个难题最终未能解决,尤其是俄国人名字的音译,我们选择采用了传统的拼法,因为大多数读者不熟悉现代国会图书馆系统。我尽量采用人名的原始拼写方式,比如用Wilhelm而不是William,用Franz而不是Francis。但在极少数情况下,这样做会显得有点怪,尤其是俄国沙皇的名字,为此我采用了这些名字的英文拼法。至于地名,我用的是昔日广泛使用的名称。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克里斯蒂娜·科尔托百忙中挤出时间核对清样,在我撰写此书的漫长过程中,她与我们的两个儿子马修和尼古拉斯始终支持着我。
理查德·J.埃文斯
剑桥,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