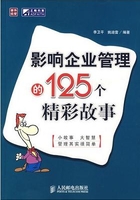“为什么就没有更合适的理由呢?”吴琴用拳头捶打着薛康撒娇地问。
“傻妹子。对于冯家的态度你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退彩礼钱是夏丽萍操心的事,你急什么呀。她让你相亲,你就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刚退了婚,不想再订婚。再说,你家的老大难吴恩峰不是还给你杵在前头吗?即使是吴恩峰有了结婚对象,你母亲也不好意思向你开口说是用你的订婚彩礼钱为你二哥办事。哎,吴琴,你为什么就不能在夏丽萍面前耍耍小孩性子呢?”
“因为我是夏丽萍抱养的扫帚星。”吴琴转头不快地说,下床穿上鞋走向了院子。
呼吸着院落里清凉冷冽的冬意,仰头面对满天繁星,她多么希望璀璨的朔夜是自己的生日。要是当初母亲没有告知自己的身世该多好呀,她没有见过扫帚星,真想见一见。深深地望着星空,她看到了传说中的扫帚星,托着长长的尾巴,很快又消失了,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是看到了没有看到。
“表哥,扫帚星会一闪而逝吗?”她问屋里的薛康。
“别老说扫帚星,这是村里人对彗星的称呼。因为彗星像一把扫帚,所以村里人就说扫帚星。”
“扫帚星明明是骂人的话。谁对自己家不好,别人就骂她是扫帚星。”吴琴辩解道。
“为什么非要说扫帚星?为什么不用冥王星来形容对自家不好的人。总之迷信的没有科学依据的事,最好一个耳朵入,另一个耳朵出。”
“它又出来了。”
“谁?”薛康在屋里问。
“彗星。”吴琴回答,听见表哥跳下床,拖着棉拖鞋快速出来。“哪里哪里?”
“那里那里。”
“就是漫天繁星呀。哪有彗星。你认识彗星吗?比繁星都要大,要明显,要美丽,拖着长长的明晃晃的的尾巴在天际,一动也不动。”
“是呀。它就在那里。”吴琴依然指引表哥看。
“让你再逗我,让你再逗我。”薛康说着从地上抓起一团雪往吴琴衣服里塞。
吴琴一动也不动,对表哥的行为即使毫无感觉,也该感到雪的冰凉寒冷呀。她不明白自己明明看到了彗星,表哥怎么就看不到呢。
“回屋,外面这么冷。根本就没有彗星。”薛康将吴琴往屋里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地球人才会目睹一场彗星。每出现一次有时是几个月,有时数十天,彗星就从地球遥远的身边路过了。”
“表哥,你真的看不到吗?”
“星河里就没有出现呀。”
“我就是看到了。”
“想星星想疯啦。”
他们回到屋里,吴琴内心一直忐忑不安,自己的眼睛明明没有问题,表哥为何就看不见。她再次走到屋外,彗星依然明晃晃的在天上。
“表哥,你的眼睛真得有问题。那分明就是彗星,你却说看不见。”
“好了,我早就看见了。外面冷,你还是进来吧。”
他俩再次躺在床上。
“关于相亲的事,你能扛过吗?”薛康问。
“能。就是你说的,二哥不结婚,我就不订婚。长这么大还真没有对母亲撒过娇呢。十八岁,我也该完全自主了。”
“女人不狠,地位不稳。用作嫁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真是愚蠢之极的活受罪。养儿是用来防老,不是用来敛财的。你有觉悟,更应该将自己的觉悟发挥出来,以后我决不允许你窝囊了自己,快活了别人。”
“但愿二哥永远别回家。这样我用二哥做挡箭牌,母亲即联系不上二哥,又无法强硬地催促我相亲。”
“你不愿意生孩子,倘若我们外出一年,在外面有了小孩,吴家的烦恼就进不来你的脑海了。”
自身的遭遇与身处的环境压迫着人,使人形成一种仿佛固有般的潜在观念。人就这样被后天侵蚀了,人间也不再有纯粹的人。她想成为闲人。有情调的闲人,而非畜生般四蹄着地的闲人。所以她心中的闲态永远不会闲得发慌、闲得作践。是一种对家庭收入与积蓄从不上心的心境。不会为了住更大更好的房子一股子劲地奔波挣钱;不会为了留给子女更好的物质基础而死命地六亲不认地抠钱儿。闲出境界的人是轻松自在的,即使收入不高,也透不出紧迫。他们没有太多的欲求,所以看不出被什么烦恼。闲得发慌的人削尖了脑袋散播流言制造风语,生怕亲朋好友五里乡亲不知自己有着如此根深蒂固的可恶本性,其目的无非是作践自己与乡里,猪狗不如。总之,她不能忍受太多的欲求压迫自己。她明白,生活一旦受到金钱欲求的胁迫,爱情也就成了过家家式的婚姻生活,掉入了俗不可耐的瘴疠深渊中。真要感谢恶俗,若不是一直活在恶俗里,她也不会体味到什么是活得累活得无聊。因此,她选择绝子绝孙来缩减被逼迫的欲求。这也正反应了她骨子里坚信自己生育的子女不会像自己这般觉悟:没断奶时只知道吃奶,断奶后只求五谷杂粮粗茶淡饭。她更拒绝父母张结来的婚姻。与生俱来于恶俗的喜爱搬弄是非揶揄家长里短的精神比物质更贫瘠的穷山村,冥冥中一股强大的力量让她认定自己一辈子也不能逃脱物质贫穷的诅咒。尝到象征精神富裕的爱情后,她甘愿物质上的安贫乐道。
为父母作嫁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不仅仅让她觉得市侩化,更令她有着如芒在背的背叛爱情的意味。当年生身父母已然葬送了自己千金小姐的身份,自己再也不能为了养父母的寸光鼠目中的蝇头小利而硬生生摔碎自己的爱情。让贫瘠的物质生活被赤条条的精神生活如雪在霜。随着家里一些世俗之事对她的逼迫,她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村里太多的亲情关系都是程序化。包括自己成长的吴家,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金钱,对金钱永无止境的贪求使得每个人对人间的真善美麻木不仁,无比做作地与人交道。春节里走亲访友,每个家庭都有着自己待客的那一天。春节里的待客与平日里的待客完全不同,更为神圣。就自己生活的吴家来说吧,每年的正月初三是待客的日子。这一天吴家所有的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总之,吴天虎会摆设几桌酒席来招待小辈至亲。其不目的不仅仅是总结去年展望今年,更为了亲戚间沟通感情,闹矛盾的、有隔阂的,会在喜气盈盈的酒桌上年味里冰释前嫌。岂料,中国人特有的拜年哲学早已被恶俗眼中的蝇头小利屙满了臭狗屎。长辈在纠结窝心结了婚的晚辈们的拜年礼的孰轻孰重。未成熟的晚辈在争执长辈们给的压岁钱的厚重薄寡。本应设的待客酒席早已被触景生情后的上年的纠结窝心塞满了臭皮囊,耿耿于怀地免了长辈为晚辈做出的优良表率。闹着矛盾有着隔阂的亲戚间像是被彼此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般狭隘的思想煎熬着,跃然如不开化的野猪般成为化外的畜生。所以,这些唯利是图的家伙从新年初始的拜年中超脱出来的唯一人生真谛,就是,铆足了心劲心机地挣钱敛财。如此这般地致富了,在亲戚乡里间做着小人的小气态势,不仅没有了乡情,更丧失了亲戚味。没了人情味的人个个都是化外高人。
哪里才不是人间真善美的沦陷区?闲人式的爱情。
人一旦坚定了对某件事的忠贞,身上就透着傻气。对情感的忠贞让人变得傻里傻气,其余则懵愣般的疯狂。这个世界就是一群疯子在嘲笑一群傻子。可悲的是由疯子在推动世界的变革。话说回来,如果让傻子推动世界的变革,那么,高尚的事物一概不存在。凡是大众化的,都不是高尚的。
吴琴不会对亲情犯傻气了,因为爱情的傻气已经傻到她的心坎里。
如果必须再次相亲,自己必然会爆发生平以来最强烈的与母亲的争论。她不是向谁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无心证明,只是为了印证对爱情的坚贞。人们常说,父母欠儿子一个媳妇,儿子欠父母一口棺材。就村里的大众来说,到了老年后,能逢上个孝顺的儿女,才是活得圆满了。有了孝顺的儿女,老年人依赖的养老家庭才能够和睦。子女的不和无非是父母的养老与金钱纠纷。吴琴认为,什么年龄守好什么底线。年轻气盛的守好爱情底线;为人父母、上有老下有小的,在中轴上守好亲情的底线。今天保住了爱情,这份忠诚就会成长下去,以便自己将来守护好亲情。年轻时背叛了爱情,保不准二十年后就会背亲弃义无视对父母的赡养。情,就是这么微妙——一步错步步错。只有情是老百姓的天,情错了,天也就错了。步步错只会结一种果实:无力回天的唏嘘。因为活在地面上的人将情错视为不可饶恕的背叛,他们会用错上加错的改天换日来报复背叛的亲人。小小的情错竟会拿出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不共戴天的心劲心机来报复,以求挽回面子。
倘若相亲的日子定下来,她有太多太多的想法对母亲说。这些想法每一句都是平平凡凡的人间真理。要是经过她的心对母亲说出来,她觉得是伟大而不平凡的,因为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因为母亲当年不顾及扫帚星的忌讳抱养了自己。她有过百依百顺的孝敬父母,那确实是以愚昧的自欺欺人的方式来纵养另一个愚昧的恶俗之人。养育自己的吴家顶顶真是恶俗的。有了爱情的自己就是要在恶俗的环境里挺起不媚俗的脊梁,就像扫帚星的晦气并不存在。往事已随风成尘,她只想有个干干净净简简单单的将来。简洁高尚的梦想无关乎金钱的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