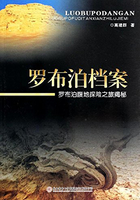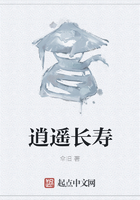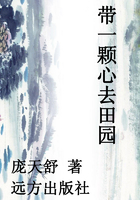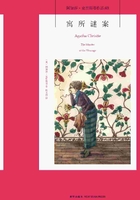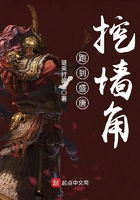面团儿是嫂嫂事先和好的,经过发酵,再加上一些黄豆面,搅拌两个鸡蛋和一点点白糖,上锅蒸好。吃起来又甜又香,外暄里嫩。家中每人分尝一块,其余的全都由我吃了。
小时候,一年到头,最快活的节日,要算是旧历年了。
这是亲人欢聚的日子。无论是外出做工,还是他乡行役,再远也要赶回来,达到阖家团圆。除夕之夜,灯官出巡,锣鼓喧腾,灯笼、火把亮如白昼,一家人都要观看的。回来后,便团团围坐,笑语欢谈;而且,不分穷家富户,到了这个晚上,都要尽其所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母亲常说:“打一千,骂一万,丢不下三十晚上这顿饭。”老老少少,任谁都必须熬过夜半,送走了旧年、吃过了年饭之后,再去睡觉。
我的大哥在县城当瓦工,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但是,旧历年、中秋节,却绝无例外地必然赶回来。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先给水缸满满地挑上几担水,然后再抡起斧头,劈上一小垛劈柴。到了三十晚上,先帮嫂嫂剁好饺馅,然后就盘腿上炕,陪着父亲和母亲玩纸牌。剩下的置办夜餐的活,就由嫂嫂全包了。
全家人一无例外地都换上了新装,父亲戴上了一顶古铜色的毡帽,是哥哥从县城里新买的;嫂嫂为妈妈赶制了一件新的棉袍。屋子里,笑语欢腾,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笑林广记》上的故事,本是寥寥数语,虽说是笑话,但“包袱”不多,笑料有限。可是,到了父亲嘴里,敷陈演绎,踵事增华,就说起来有味、听起来有趣了。原来,他自幼曾跟“说书的”练习过这一招儿。他逗引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自己却顾自在一旁,“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
我是个“自由民”,屋里屋外乱跑,片刻也停不下来。但在多数情况下,是听从嫂嫂的调遣。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戏台上头戴花翎、横刀立马的大元帅。此刻,她正忙着擀面皮、包饺子,两手沾满了面粉,便让我把摆放饺子的盖帘拿过来。一会儿又喊着:“小弟,递给我一碗水!”我也乐得跑前跑后,两手不闲。
到了亥时正点,也就是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标准时刻,哥哥领着我到外面去放鞭炮,这边饺子也包得差不多了。我们回屋一看,嫂嫂正在往锅里下饺子。估摸着已经煮熟了,母亲便在屋里大声地问上一句:“(煮)挣了没有?”嫂嫂一定回答:“挣了。”母亲听了,格外高兴,她要的就是这一句话。“挣了”,意味着赚钱,意味着发财,意味着富裕。如果说“煮破了”,那就不吉利了。
热腾腾的一大盘饺子端了上来,全家人一边吃一边说笑着。突然,我喊:“我的饺子里有一个钱。”嫂嫂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缝儿,甜甜地说:“恭喜,恭喜!我小弟的命就是好!”旧俗,谁能在大年夜里吃到铜钱,就会常年有福,一顺百顺。哥哥笑说,怎么偏偏小弟就能吃到铜钱?这里面一定有说道,咱们得检查一下。说着,就夹起了我的饺子,一看,上面有一溜花边儿,其他饺子都没有。原来,铜钱是嫂嫂悄悄放在里面的,花边也是她捏的,最后,又由她盛到了我的碗里。谜底揭开了,逗得满场哄然腾笑起来。
父母膝下原有一女三男,姐姐和二哥已相继去世;大哥、大嫂都长我二十岁,他们成婚时,我才一生日多。嫂嫂姓孟,是本屯的姑娘。哥哥常年在外,她就经常把我抱到她的屋里去睡。她特别喜欢我,再忙再累,也忘不了逗我玩,还给我缝制了许多衣裳。其时,母亲已经年过四十了,乐得清静,便听凭我整天泡在嫂嫂的屋里胡闹。后来,嫂嫂自己生了个小女孩,也还是照样地疼我爱我亲我抱我。有时我跑过去,正赶上她给小女儿哺乳,便把我也拉到她的胸前,我们就一左一右地吸吮起来。
嫂嫂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蒸的碗花糕。她有个舅爷,在京城某王府的膳房里,做过两年手艺,别的没学会,但做的一种蒸糕,却是出色当行。一次,嫂嫂说她要“露一手”,不过,得准备一个大号的瓷碗。乡下僻塞,买不着,最后,还是她回家把舅爷传下来的浅花瓷碗捧了过来。
面团儿是嫂嫂事先和好的,经过发酵,再加上一些黄豆面,搅拌两个鸡蛋和一点点白糖,上锅蒸好。吃起来又甜又香,外暄里嫩。家中每人分尝一块,其余的全都由我吃了。
蒸糕做法看上去很简单,可是,母亲说,剂量配比、水分、火候都有讲究。嫂嫂也不搭言,只在一旁甜甜地浅笑着。除了做蒸糕,平素这个浅花瓷碗,总是嫂嫂专用。她喜欢盛上多半碗饭,把菜夹到上面,然后,往地当央一站,一边端着碗吃饭,一边和家人谈笑着。
关于嫂嫂的相貌、模样,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在孩子的心目中,似乎没有俊丑的区分,只有“笑面”或者“愁面”的感觉。小时候,我的祖母还在世,她给我的印象,是终朝每日,愁眉不展,似乎从来也没见到过笑容;而我的嫂嫂却生成了一张笑脸,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是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
不管我遇到怎样不快活的事,比如,心爱的小鸡雏被大狸猫捕吃了,赶庙会母亲拿不出钱来为我买彩塑的小泥人,只要看到嫂嫂那一双笑眼,便一天云彩全散了,即使正在哭闹着,只要嫂嫂把我抱起来,立刻就会破涕为笑。这时,嫂嫂便爱抚地轻轻地捏着我的鼻子,念叨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小鸡鸡,没人要,娶不上媳妇,瞎胡闹。”
待我长到四五岁时,嫂嫂就常常引逗我做些惹人发笑的事。记得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嫂嫂叫我到西院去,向堂嫂借枕头。堂嫂问:“谁让你来借的?”我说:“我嫂。”结果,在一片哄然笑闹中,被二嫂“骂”了出来。二嫂隔着小山墙,对我嫂嫂笑骂道:“你这个闲×,等我给你撕烂了。”我嫂嫂又回骂了一句什么,于是,两个院落里,便伴随着一阵阵爆竹的震响,腾起了“叽叽嘎嘎”的笑声。原来,旧俗:年三十晚上到谁家去借枕头,等于要和人家的媳妇睡觉。这都是嫂嫂出于喜爱,让我出洋相,有意地捉弄我,拿我开心。
还有一年除夕,她正在床头案板上切着菜,忽然一迭连声地喊叫着:“小弟,小弟!快把荤油罐给我搬过来。”我便趔趔趄趄地,从厨房把油罐搬到她的面前。只见嫂嫂拍手打掌地大笑起来,我却呆望着她,不知是怎么回事。过后,母亲告诉我,乡间习俗,谁要想早日“动婚”,就在年三十晚上,搬动一下荤油坛子。
嫂嫂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十分通晓事体,记忆力也非常好。父亲讲过的故事、唱过的子弟书,我小时在家里“发蒙”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她听过几遍后,便能牢牢地记下来。我特别贪玩,整天跑到大沙岗上去玩耍。早晨,父亲布置下两页书,我早就忘记背诵了,她便带上书,跑到沙岗上催我快看,发现我浑身上下满是泥沙,便让我就地把衣服脱下,光着身子,坐在树荫下攻读,她就到沙岗下面的水塘边,把脏衣服全部洗干净,然后晾在青草上。
我小时候,又顽皮,又淘气,一天到晚总是惹是生非。每当闯下祸端,父亲要惩治时,总是嫂嫂出面为我讲情。这年春节的前一天,我和两个小伙伴,跟随着父亲,到土地庙去给土地爷进香上供。父亲在给土地爷叩过头之后,开始往设在外面的供桌上摆放猪肉块和点了红点的馒头,还有两样水果。这时,他用手指着庙门上的对联,叫我念。我一看,总共十个字,便分别上下联,念出:“天地之大也”,“鬼神其盛乎”。父亲点了点头。
说着,他就先回去了,留下我在一旁看守着,防止供果被猪狗扒吃了,挨过一个半时辰之后,再将供品端回去,供家里人享用。所谓“心到佛知,上供人吃”。
可是,一个半时辰相当于三个小时,这是很难熬的。闲着没事,手发痒,我便想出了歪点子:从怀里摸出两个偷偷带去的“二踢脚”(一种爆竹),分别插在神龛前的香炉上,然后用香火点燃,只听“噼—啪”几声轰响,小庙里面便被炸得烟尘四散,一塌糊涂。我和小伙伴,却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晓得,早被邻人发现了,告到了我的父亲那里。我却一无所知,坦然地端着供品,溜回家去。看到嫂嫂等在门前,先是一愣,刚要向她炫耀我们的“战绩”,她却小声告诉我:一切都“露馅”了,势态很严重,你就等着屁股挨板子吧!见我有些紧张,不想进院子了,她便又出主意:见到父亲二话别说,立刻跪下,叩头认错。我依计而行,她则在一旁“爹长爹短”地叫个不停,赔着笑脸,又是装烟,又是递茶,父亲渐渐地消了气,叹说了一句:“长大了,你能赶上嫂嫂一半,也就行了。”算是结案。
我四岁那年,正赶上夏季青黄不接,家里把刚刚收下的大麦稞,剪下穗头,用干净的布鞋底,在笸箩里搓下籽粒,然后煮成一锅大麦粥。我在外面玩饿了,一进屋就嗅到浓浓的麦香味,便操起饭勺子,想要从锅里舀出一碗。由于个头太小,勺子又大,舀出来一些全洒在胳膊和手上。滚开的米汁、饭粒烫得娇嫩的皮肤红肿一片,伤处灼痛难忍,我呜呜地哭叫着。正在屋后菜地里干活的妈妈和嫂嫂闻讯,慌忙地跑进来。嫂嫂一面哄着我,说“不哭,不哭,小弟——男子汉,不哭”;一面用舌头舔着我的伤处,舔过了脏兮兮的小手,又舔满是泥痕的胳膊,连续不断地反复地舔。说这是治烫解痛的祖传秘方,比上药都有效。舌头舔过的地方,湿润、温暖,皮肤有些放松,感觉灼痛确实减轻了许多。半天过去,灼伤的皮肤除了颜色稍红,既未见水疱,更没有溃烂,第二天就完好如初了。
我家养了一头大黄牛,哥哥中秋节回家度假时,常常领着我逗它玩耍。他头上顶着一个花围巾,在大黄牛面前逗引着,大黄牛便跳起来用犄角去顶,尾巴翘得老高老高,吸引了许多人围着观看。这年秋后,我跟着母亲、嫂嫂到棉田去摘棉花,顺便也把大黄牛赶到地边去放牧。忽然发现它跑到地里来嚼棉桃,我便跑过去,扬起双臂轰赶。那时,我只有三周岁,胸前系着一个花兜肚,没有穿衣服。大黄牛看我跑过来,以为又是在逗引它,便挺起了双角来顶我。结果,牛角挂在兜肚上,我被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上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母亲和嫂嫂“呜呜”地哭了起来。
事后,村里人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晚上,嫂嫂给我做了碗花糕,然后,叫我睡在她的身边,夜半悄悄地给我“叫魂”,说是白天吓得灵魂出窍了。
每当我惹事添乱,母亲就说:“人作(读如昨)有祸,天作有雨。”果然,乐极悲生,祸从天降了。
在我五岁这年,中秋节刚过,回家休假的哥哥突然染上了疟疾,几天下来也不见好转。父亲从镇上请来一位姓安的中医郎中,把过脉之后,说怕是已经转成了伤寒,于是,开出了一个药方,父亲随他去取了药,当天晚上,哥哥就服下了,夜半出了一身透汗。
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载其父病疟返里,寒索火,热索冰,竟转伤寒,病势日重,后来延请名医诊治,幸得康复。而我的哥哥遇到的却是一个“杀人不用刀”的庸医,由于错下了药,结果,第二天就死去了。人们都说,这种病即使不看医生,几天过后也会逐渐痊复的。父亲逢人就讲:“人间难觅后悔药,我真是悔青了肠子。”
他根本不相信,那么健壮的一个小伙子,眼看着生命就完结了。在床上停放了两整天,他和嫂嫂不合眼地枯守着,希望能看到哥哥长舒一口气,苏醒过来。最后,由于天气还热,实在放不住了,只好入殓,父亲却双手捶打着棺材,破死命地叫喊;我也呼着号着,不许扣上棺盖,不让钉上铆钉。而后又连续几天,父亲都在深夜里,到坟头去转悠,幻想能听到哥哥在坟墓里的呼救声。
由于悲伤过度,母亲和嫂嫂双双地病倒了,东屋卧着一个,西屋卧着一个,屋子里死一般地静寂。原来雍雍乐乐、笑语欢腾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我像是一个团团乱转的卷地蓬蒿,突然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根基。
冬去春来,天气还没有完全变暖,嫂嫂便换了一身月白色的衣服,衬着一副瘦弱的身躯和没有血色的面孔,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其实,这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父亲正筹划着送我到私塾里读书。嫂嫂一连几天,起早睡晚,忙着给我缝制新衣,还做了两次碗花糕。可是吃起来,却总觉着味道不及过去了。母亲看她一天天瘦削下来,说是太劳累了,劝她停下来歇歇。她说,等小弟再大一点,娶了媳妇,我们家就好了。
一天晚上,坐在豆油灯下,父亲问她下步有什么打算。她明确地表示,守着两位老人、守着小弟弟、带着女儿,过一辈子,哪里也不去。
父亲说:“我知道你说的是真心话,没有掺半句假。可是,——”
嫂嫂不让父亲说下去,呜咽着说:“我不想听这个‘可是’。”
父亲说,你的一片心情我们都领了。无奈,你还年轻,总要有个归宿。如果有个儿子,你的意见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可是,只守着一个女儿,将来总是人家的人,孤苦伶仃的,这怎么能行呢?
嫂嫂说:“等小弟长大了,结了婚,生了儿子,我抱过来一个,不也是一样吗?”
父亲听了,长叹一声:“咳,真像‘杨家将’的下场,七狼八虎,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一个‘囊囊揣’(当地土语,意为没有能耐)的杨六郎,谁知将来又能怎样呢?”
嫂嫂呜呜地哭个不停,翻来覆去,重复着一句话:“爹,妈!就把我当作你们的亲闺女吧。”嫂嫂又反复亲我,问“小弟放不放嫂子走”,我一面摇晃着脑袋,一面号啕大哭。父亲、母亲也伤心地落下了眼泪。这场没有结果的谈话,暂时就这样收场了。
但是,嫂嫂的归宿问题,终竟成了两位老人的一块心病。一天夜间,父亲又和母亲说起了这件事。他们说,论起她的贤惠,可说是百里挑一,亲闺女也做不到这样。可是,总不能看着二十几岁的人这样守着我们。当老人的怎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呢?我们于心难忍啊!
第二天,父亲去了嫂嫂的娘家,随后,又把嫂嫂叫过去了,同她母亲一道,软一阵硬一阵,再次做她的思想工作。终归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嫂嫂勉强地同意改嫁了。两个月后,嫁到二十里外的郭泡屯。
我们那一带的风俗,寡妇改嫁,叫“出水”,一般都悄没声的,不举行婚礼,也不坐娶亲轿,而是由娘家的姐妹或者嫂嫂陪伴着,送上事先等在村头的婆家的大车,往往都是由新郎亲自赶车来接。那一天,为了怕我伤心,嫂嫂是趁着我上学,悄悄地溜出大门的。
午间回家,发现嫂嫂不在了,我问母亲,母亲也不吱声,只是默默地揭开锅,说是嫂嫂留给我的,原来是一块碗花糕,盛在浅花瓷碗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吃这种蒸糕了,泪水刷刷地流下,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咽。
每年,嫂嫂都要回娘家一两次。一进门,就让她的侄子跑来送信,叫父亲、母亲带我过去。因为旧俗,妇女改嫁后,再不能登原来婆家的门,所谓“嫁出的媳妇泼出的水”。见面后,嫂嫂先是上下打量我,说“又长高了”,“比上次瘦了”,坐在炕沿上,把我夹在两腿中间,亲亲热热地同父母亲拉着家常话,像女儿见到爹妈一样,说起来就没完,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告诉。送走了父亲、母亲,还要留我住上两天,赶上私塾开学,早晨直接送我到校,晚上再接回家去。
后来,我进县城、省城读书,又长期在外工作,再也难以见上嫂嫂一面了。听说,过门后,她又添了四个孩子,男人大她十几岁,常年哮喘,干不了重活,全副担子落在她的肩上,缝衣,做饭,喂猪,拉扯孩子,莳弄园子,有时还要到大田里搭上一把,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儿”。由于生计困难,过分操心、劳累,她身体一直不好,头发过早地熬白,腰也直不起来了。可是,在我的梦境中、记忆里,嫂嫂依旧还是那么年轻,俊俏的脸庞上,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
又过了两年,我回乡探亲,母亲黯然地说,嫂嫂去世了。我感到万分地难过,连续几天睡不好觉,心窝里堵得慌。觉得从她的身上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而我所回报的却是“空空如也”,真是对不起这位母亲一般地爱我、怜我的高尚女性。引用韩愈《祭十二郎文》中的话,正是“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殓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一次,我向母亲偶然问起嫂嫂留下的浅花瓷碗,母亲说:“你走后,我和你爸爸加倍地感到孤单,越发想念她了,想念过去那段一家团聚的日子。见物如见人,经常把碗端起来看看,可是,你爸爸手哆嗦了,碗又太重,……”
就这样,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嫂嫂,再也见不到那个浅花瓷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