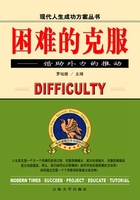我是她十七年的相知。
多少次交往,多少次见面,多少次闲谈;她周遭几多梦幻,几多猜疑,几多暗示;与她一起,早晨苏醒望见的明亮的启明星,雨季黄昏,素馨花的清芬,暮春聆听的慵倦的乐曲……十七年的一切,镂刻在她的芳心。
十七年来她直呼我的小名。应答者不是造物主的杰作,而是用她十七年的谙熟塑模而成。唯独在她的心灵里,时而以亲昵,时而以疏远,时而以动作的热情,时而以恶作青年泰戈尔剧的过渡,时而当着众人的面,时而独坐幽静处,得以塑模这位应答者。
弹指间又流逝了十七年。后十七年的日日夜夜,未曾用我的名字的圣线连接,是零散的。
所以它们天天问我:哪里是我们的归宿?谁引导我们进入楼宇?
我回答不出,默默地思忖着。
它们一面乘风飞驰,一面快活地说:我们去寻找。
找谁?
它们也不晓得找谁,飘来飘去,像迷茫的暮云,融入冥暗,踪影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