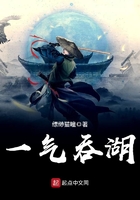我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待在屋子里不行,花园里不行;家里不行,学校也不行。我仅剩下一点狭小的空间隐藏在自己的内心。即使这样,我的内心还是伤痕累累,经常遭受打击和嘲讽。我没有把自己受欺负的事告诉给母亲。一方面是因为她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冷漠的心里竟然生出一丝怜悯。牛群还是不请自来,鲍勃对菲利普的误会更深了,以至于菲利普成天缩着脖子,生怕挨打。母亲说我们该叫“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SPCC)的人来了。为了菲利普吗?我没好气地说,那该叫上“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的人。此外,鲍勃竟把自己的小摩托车骑到屋子后面,然后狠命地踢它。这下我们就不知道该叫谁来了。
鲍勃放弃了规律性的生活。他到花园里走动,又是犁地又是耙土。他眼巴巴地等着,想看看究竟是谁糟蹋了他的花园。他偷偷地蹲在栅栏边上的角落里,一身蓝色的工装裹住他瘦小的身躯。可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牛群出现。我的母亲从窗户望出去,撇撇嘴,自言自语地说,你好自为之吧。邻居们开始议论鲍勃了,不再理会我父亲的去向。相比而言,鲍勃更有意思,他能在花园里用一只眼睛干活,用另一只眼睛提防。母亲跟我说,我们家的条件改善了,可以送我去语法学校念书。她说话的时候,那漆黑光亮的头发在肩膀上跳跃。以前我们家连校服都买不起,现在没问题了。我担心语法学校的人会打探我的家庭情况。“我的父亲在哪儿呢?”我问母亲,“他去了什么地方?给你写过信吗?”
“我也不知道,也许已经死了,”她说,“也许是去了一个没有邮票的地方回不来了。”
那一年,我参加了语法学校的入学考试,鲍勃正在培育盆栽水芹。他站在大门口,想把培育的成果推销给邻居,吹嘘说那是如何富有营养的蔬菜。迈拉比以前还瘦,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鲍勃想通过卖盆栽来贴补家用,可惜玻璃瓶已经沾满了灰尘,蔬果枯萎至干瘪,一如迈拉的身形。
神父到学校来主持每年一度的宗教知识考试,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考试了。他高高地坐在女校长的椅子上,小心翼翼地把穿着粗革皮鞋的大脚放在木制的踏板上。神父年纪大了,气息很重,身上散发出湿羊毛的膻味、膏药的臭味和止咳糖浆的甜味。当然,他还有那么一股子虔敬的味道。考试的题目很奇巧。他要我们画出灵魂的样子。一个傻呆呆的孩子接过他手中的粉笔,到黑板上画了一个肾形的图案,看上去像一只鞋印。神父带着微微的喘息声说道,不对,孩子,那是心脏的样子。
我十岁那年,家境有了好转。母亲的眼光不错。房客虽然脾气暴躁,可是个上进的好男人。我们依靠上了他,跟他一起离开了村子,搬到一个干净的小镇。镇上的春天来得很早,樱花开得耀眼,画眉鸟轻快地在平整的草坪上跳跃。镇上的居民并不讨厌雨天,还说老天在替他们浇灌花园。这和以前村子里的气氛完全不同。村里的人老是抱怨命运的不公,雨天就更增添了他们的怨气。我想起了可怜的鲍勃。他肯定为了那些被牛糟蹋的莴苣而憔悴不已。哀愁、迷惘,还有贫血,已经快把他整个人折腾散架了。看到我们喜气洋洋地搬家时,他大概恨得连骨头都疼。至于菲利普,我把他从记忆中彻底抹除了,当他从来没有存在过。母亲对现在的非婚同居生活很满意,但她告诫我千万不能透露自己的家庭情况。“别跟人说家里的事,他们管不着。”她说。我心里想,你也不能笑话别人,不能提“佛勃斯”这个词。
直到我长大成人、离家生活以后,我才体会到普通人无拘无束的生活。那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可以自由地说话,自由地行事,无需刻意地隐瞒,也无需小心地提防。我碰到许多心地单纯、心胸开阔的人,他们的品质是我所不具备的。也许我曾经有过,但我老早就遗失了,遗失在那夜晚升起的浓雾中,在那下午四点降临的暮色中,在那破败的栅栏和凌乱的草丛中。
有句话讲,人总得生活;我做了一名律师。整个六十年代都过去了,我的童年记忆也开始褪色、老旧。它成了我内心深处的珍藏,有时会在梦里向我敞开。北爱尔兰的争端爆发了,我的家庭也陷入了争执,报纸上登满了小商小贩的照片,他们愁苦的表情和我们一样。
再次想起菲利普的时候,我已经是个成熟的执业律师了,长期在外工作。复活节的那天,阳光明媚,我回到久违的家中,正吃着早餐。餐厅的窗户敞开着,能看到花园里的草坪和假山。烤好的面包放在架子上,果酱盛在碟子里。一切都变了,变得超乎想象!连房客也斯文起来,西装革履地参加扶轮社的会议。
母亲的身材不再苗条。她坐在我的对面,把一份当地的报纸递给我看。报纸被小心折叠过了,正面就有一张照片。
“你看,”她说,“苏西结婚了。”
我接过报纸,放下手中的面包。凭着童年的记忆,我仔细辨认苏西的模样。可不就是她,一个打扮俗气的女孩手捧花束站着,姿势不像是拿花,倒像是举着一根短棍;宽大的下巴努力配合做出微笑的表情。她的旁边站着新婚丈夫,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是她的父母。真是岁月不饶人,她的父母也老态龙钟、弯腰驼背了。我还想从他们的后面找到菲利普。我猜他会做出一副没精打采又略微凶恶的样子,有半个身子都在镜头外面。“苏西的哥哥呢?”我问母亲,“他没去参加婚礼吗?”
“菲利普?”母亲抬起眼睛看我。有好一会儿,她的嘴都半张着,似乎欲言又止,手指捻碎了一小块面包。“没人跟你说过吗?出了意外的事情?我以为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没写信告诉你吗?”她把早餐推到一边,冲我皱起眉头,好像对我有点失望。“他死了。”她终于说出了口。
“死了?怎么死的?”
母亲把嘴边的面包屑抹开,一边起身,一边说道:“自己死的。”她走到餐柜跟前,打开一个抽屉,要从一堆杯垫子和照片中找点什么。“我保存了当时的报纸,我以为已经寄给你了。”
我清楚自己始终在逃离过去,试图一点一滴地从过去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我错过了许多,却以为自己没有错过什么重要的东西。然而,菲利普就这么悄声无息地走了。我回想起他扔过来的石头,他疑惑不解的眼神,还有他穿着短裤、瘦长的腿上显出瘀青的样子。
“已经好多年了。”母亲打断我的思绪。
她又坐到我的对面,把她保存的报纸递给我。才几年的工夫,报纸已经变黄,像是从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共图书馆借来的。我翻看报纸,想知道菲利普是怎么炸死自己的。报纸上登载了验尸报告,最终的裁决是意外死亡。
菲利普在父亲的花园小屋里用糖和除草剂自制了一枚炸弹。那时候自制炸弹很流行,主要是从贝尔法斯特流传开来的。炸弹的用途无人知晓,总之它就在菲利普的跟前爆炸了。我不知道菲利普当时身上带着什么。我能想象到的情景是:小屋被炸得四分五裂,摞好的花盆“哗啦啦”地全碎了,连野地里的牛也被爆炸声吸引,好奇地抬起头来张望。我突然冒出一个毫不相干的想法:爱尔兰终于除掉了菲利普。我成了幸存的一方,被生活划归“临时派”,戴上了黑色贝雷帽。我的同龄人当中,菲利普是第一个离世的。我现在经常想起他,脑子里重复一个声音——“除草剂”。这是一种能除掉杂草的液体。如果说我的生活中也有这么一枚自制的炸弹,那么,炸弹的导火索正在缓慢地燃烧。
消杀
我很小的时候,每次都会被后门外面的街沿石绊倒。老狗维克托经常充当我的护卫。我们一起小心翼翼地穿过庭院,我的手牢牢地抓住维克托脖子上粗硬的皮项圈。它确实老了,连项圈都已经磨软磨薄了。我紧紧握住这一条项圈,让维克托领着我四处旅行。阳光洒落在石头和石板上,菖蒲丛中夹杂着盛开的蒲公英。各家的门前,老太太们出来晒太阳,透透气。有的窝在高背椅子里打盹,有的整理膝上的裙摆。而远处的英格兰,正在工厂、田野和煤矿的噪音中沉闷地运转。
母亲经常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意义上的替代品。每一件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消逝的事物无法重来,幸福不可复制。对孩子来说,就该取一个贴切的名字,而不该继承别人的名字。母亲说她不赞成以别人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孩子。
既然如此,母亲为何自破规矩呢?这事让我琢磨不透,又勾起我对另一件事的回忆。那件事与狗有关,也许能提供一些线索。等我讲完之后,希望你能帮我解开疑团。
母亲的立场是很坚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她自己就继承了一位远亲的名字——克拉拉。那位远亲是在湖上划船的时候不慎溺亡的,若活到现在,该有107岁了。母亲之所以不满意自己的名字,并不是因为那位远亲有什么恶劣的品质,大家根本不了解她的为人。真正让母亲苦恼的,是村子里的人叫出那名字来的声音。那种黏糊糊、拖拖拉拉的声音,像一股黏液从人们的嘴里挤出。
那时候,我们的邻里街坊都是表亲,相互之间经常串门。母亲总是要求串门的人先敲门,说这是文明人的规矩,可没人听懂她的意思,依旧我行我素。事实上,母亲所能施加的影响非常有限,与她的期望相差很远。这一点,是我长大以后才明白的。我当时只有7岁。在我的眼里,母亲就是太阳和月亮,是随时随地都注视我的上帝。我自己只能看些小人书,接触不到什么高级的思想,母亲却能看懂别人的心思。
我们家的隔壁住着我的姑妈康妮。她其实和我同辈,之所以叫她姑妈,是因为她年纪不小了。我们的亲属关系说来复杂,你也没有必要搞清楚,只要知道老狗维克托在给姑妈康妮做伴,喜欢待在她的餐桌底下。维克托每天要吃一块肉饼,由康妮专门到街上为它买来。它还要吃水果,吃所有碰到嘴边的食物。可我的母亲说,狗狗应该吃特制的狗粮,装在罐子里的那种。
我7岁的时候,维克托去世了。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总之是阴郁而沉痛的一天。康妮是个寡妇。儿时的我不知道“寡妇”意味着有过丈夫的妇女,还以为康妮一直独身。大家都替康妮惋惜,失去一个忠诚的狗伴无疑是丧夫之后的又一次打击。
我7岁的生日礼物是一块表,等到8岁生日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只小狗。最初说起要养狗的时候,母亲说想要一只哈巴狗。人们的反应仍是一脸的疑惑和不解,就跟母亲要求串门的人先敲门一样。村子里突然有人养起了哈巴狗,这件事情想起来就好笑。我心里也很清楚,真要养了一只,定会被村民们剥了皮,烤来吃了。
于是我跟母亲说:“是我的生日礼物,我想要一只维克托那样的狗。”
母亲回答道:“维克托不过是一只杂种狗。”
“那我就要一只杂种狗。”我坚持己见。
你看看,我还以为“杂种狗”是一个狗的品种。康妮跟我说杂种狗是非常忠诚的狗。我喜欢忠诚的品质,尽管还弄不懂它具体的含义。
杂种狗毕竟容易弄到手。过生日的当天上午,我应该很兴奋,可我记不清了。一个男孩从戈德伯农场带来一只小狗。狗狗站在火炉前的一块毯子上面,眨巴着眼睛,身子微微发颤。它的小腿细得跟小鸡的腿差不多。当时正值冬季,路上结满了霜。小狗也是一身雪白,和维克托相仿,卷卷的尾巴,也像维克托;它的背上还装了一个小鞍,显得十分驯顺。我摸了摸它脖颈后面的皮毛,感觉某一天它能长得强壮有力,禁得起拖拽。
从戈德伯农场来的男孩在厨房与我的继父交谈。我现在得叫他父亲了。我听那男孩说了一句“真是可耻”,但我没兴趣知道他具体指的什么。接着男孩走出厨房,继父也跟着出来。他们一边走还一边亲密地交谈。
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人们是怎么相互认识的。他们会说,你认识某个女的,她嫁给了某个男的。她嫁人之前,名字是保持不变的,比如说一直叫赖利。可我一时还弄不清楚人的名字是怎么变来变去的,到底变化是如何产生的。我很茫然。当某人走出房门的时候,我总要猜想他会以什么名字或什么身份回来,猜想他是否还会回来。说这些的意思并非想让我自己显得单纯无知。事实上,我能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举出充分的理由。在我看来,别人都是命运的奴隶、情感的仆人,唯独我能追随理性。
继父出门之后,我独自留在客厅,对着一团微弱的炉火。我开始和小狗维克托说话。为了迎接它的到来,我特地找了一些训狗的册子来看。册子上说狗喜欢低沉、舒缓的语调,但没有说明应该说些什么内容。维克托看来是没什么偏好的,所以我就说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蹲坐在地上,紧挨着它,让它不必为我的大个头感到不安。我看着它的脸,心里祈祷说,请记住我的脸。大概是觉得我太无聊了,维克托忽然直挺挺地倒下,死狗一般地躺着。我又坐到它的旁边,仔细地观察它。虽然我的腿上还放着一本翻开的书,可我没心思读。我静静地看着维克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安静。我本是个坐不住的人,也努力想改掉这个毛病,但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自己能有这么好的耐性,能一声不响地把维克托看上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