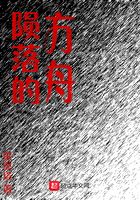宝蓝抬头,淡淡望了这身前之人一眼,却没说什么话,刚想径自走向前去,宁王眉头一掀,便侧步一拦,那双目中,却有怒火闪动。
徐伯渊把眼瞧去,自然知道这位小主子已憋了许久,此刻宝蓝只言不发,却是撩起了他的真火,便和声道:
“小王爷,蓝小姐也是为了大局,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
宁王侧头望去,却是不怒反笑。
“为了我好?便终日学个乌龟模样,任凭别人骑到头上拉屎,还悠悠然在这召什么密会?”
“为了我好,便明知已是九死一生,还要拖我兄弟入这火坑!”
“难道王家出来的人,便只知道拿张脸去勾那些涉世未深的男子替你卖命,且不论先前便勾着一个,如今又朝我兄弟下手,你这蛇蝎…”
他越说越怒,便将一张脸都拧了起来,那桌首的长姐姐终于忍耐不住,轻声喝道:
“坐下!”
这一声喝之下,便是满屋寂静,更没半个敢喘口大气的。
宁王缓缓回头望去,那长姐姐一反常态,一双眼瞪的极大:
“性命攸关之际,第一件事,却是替你那些臭味兄弟着想,你便是这怪脾气,我不怪你。可宝蓝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姐妹,你兄弟信得过,我姐妹就不行了?”
宁王沉默。
他心知自己家这位在外从来都是给足面儿,更极少呵斥自己,此刻如此,怕也是动了真火。
他回头冷眼望着宝蓝,终于没把那句最伤人之话说出口来,只是冷笑望着这少女频频点头,便大步回了座儿,却是一副吊儿郎当模样,连一双脚,都搁在了桌上,身子往那椅背一靠,又拿双手枕着脑后,竟是副闭眼假寐模样。
徐伯渊苦笑一声,望着那双新换的醒目白绿大鞋,叹了口气:
“小王爷,在座各位,可都是一方首脑,我们先端了仪态,好好议事,可好?”
宁王望了这人一眼,便是一声冷笑,他可不在乎什么大统领,又瞥了宝蓝一眼,轻笑道:
“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明知那边已有了定论,只留给我们殊死一搏之路,却依旧在这边做缩头乌龟,还要一本正经邀这劳什子的会。”
他眼瞧着宝蓝已缓缓坐到了另侧桌首,讥道:
“素闻王家眼线通天,便是陆步惟身边都能插进人去,套出信儿来。可连我都知道,自今日入夜起,这大城里,最少有六处王家产业被付之一炬,死伤只怕有上百口,便连家中护卫教头,都被人毒打致死,那尸首,如今还光明正大的吊在城门口,我倒想问问你,你难道不知道?你又做了什么?”
宁王越说越怒,忽然便直起身来,猛的一拍桌子,巨响之下,这屋中之人却没一个动了半分眉毛,只静静听着他喝问。
“我们是修为比他们差了,还是高手比他们少了?尽拿些隐忍无用的妇道算计,那些人与你同吃同住,也算是极亲之人,你就忍心看着他们尸首遭人轻贱?我问你,那些人无辜身死之际,你又做了什么,你晚上不会梦到那些面孔么?”
他一串逼问,便如暴风骤雨般迎头浇向宝蓝,便是长姐姐与另外两人,此刻也是神色黯然,微微摇头,那为首的女子极担心的望了始终低头不语的宝蓝一眼,柔声道:
“妹妹,你素来机智,但凡行事,便没由头,也必有苦衷,你…你倒是说句话啊。”
她说到最后,却是带上了几分无奈。
宝蓝闻言,似如梦初醒,这才抬起头来,轻声道:
“宁王殿下是问我入夜以后,在做些什么么?”
宁王一怔,不耐道:
“卖什么关子?”
宝蓝点头,似想了半刻,恭敬回道:
“逛了会院子,述了些儿女情长,交了个朋友。”
她瞧着宁王鼻息渐沉,似又想了想,又轻声道:“还招了个门房。”
此刻密室之中,除了宁王沉重的喘气声外,便在无半点声响,就连隐在墙角的那个庞然妖物,此刻似也听懂了主子那些话儿,坐在那处,却不敢挪出半点声响,更不敢滴下半点口水。
宁王已是怒极,冷笑之下,却当真不知该拿什么话儿骂这厚颜无耻之极的女子,把眼瞧了瞧长姐姐,见她神色也是极难看,便再也忍耐不住性子,正欲痛骂过去时,却见宝蓝在那边缓缓立起身来。
这少女平时温婉娇柔模样,便是个人瞧了,都会心生怜惜之意,生怕她着了欺负。此刻静静立在那处,轻眼将屋内扫了一番,却有股莫名气势跃然而生,便是宁王,也是声势一滞,这才忆起这姑娘先前便露过极深韬略,实是这一屋之人之长,更远胜此刻一脸心不在焉的徐伯渊。
他正自踌躇,却听宝蓝在那清声道:
“成大事必不拘小节,王家心痛,便有我家在一日,那些兄弟事后必将厚葬,家人定得一世厚报,我以我性命发誓。”
她淡淡瞧了瞧宁王,却不停歇:
“可殿下话语之中,却是有多偏颇,便最重要一条,我觉得,此次虽确无胜算,却还谈不上什么九死一生。”
宝蓝说话之间,便自怀中掏出了张薄纸,恭谨递给了长姐姐。
长姐姐脸上亦是有疑,便望着宝蓝面孔,展了那纸读了一遍:
“自吾一去,闻主家终日思念,幸得平京亦有善人,顺道于我书此信聊挂思念,实大幸也,有皇天在上,小子平安,未卒与岁。万幸,万幸,勿回,返日再期。”
她念毕,却有些云里雾里,又将信递给宁王,这厮念了许久,连一头头发都抓成了鸡窝,却也一筹莫展,却听宝蓝轻声道:
“这信,是你那位小兄弟偶尔得来的,说起来,他只花了小半柱香便解出了这藏字信,还快过我一些。”
宁王一愣,斜眼瞥了瞥宝蓝,脸色便有些僵硬。
“那,那小子那么快就看懂了?…那我可不能输。”
他猛一抽手,便自徐伯渊堪堪摸到那纸边缘之际,又摆到了桌上细细吟了几遍,便发现了些许因头,眉梢微展处眼露笑意:
“原来如此。”
“怎么说?”长姐姐一脸情急。
这小王爷一脸得意瞧了瞧身边之人,笑道:
“倒也稀松平常,便每行第二字,与最后四句第一字连读即可。”
长姐姐依言,便轻声读到:
“吾主证道,大皇子卒,万万勿返?”
她猛然抬头,望着宝蓝轻声道:
“这是平京给陆步惟的信?”
她见宝蓝点了点头,心头却是依旧有些困惑,又细瞧了这信一眼,便朝宁王问道:
“那,我们能如何?”
宁王那张笑脸便顿时僵在了那处,他知道此信定是个大契机,可此刻真要他说上些什么,却有些说不出来,一时尴尬之际,那先前还将将眼皮瞌睡的徐伯渊却已长身而起,睥睨之间寒声道:
“趁他们还在等讯不敢放手做事,雷霆一击,攻他们个措手不及!”
众人眼中皆是一亮,下首那两人中,便有一面阔目深之人沉吟道:
“听着倒是慷慨,可这就全力以赴,便没任何退路了,我寻思着,是不是太过冒进了?”
这人一脸朴素之相,说话语调奇怪,似也不是大梁人士,可也并没东海话中那些硬直之意,听起来,倒似鼻音用的甚多。
徐伯渊眼神一瞥更不多话,舒臂抽出了腰间那柄青鞘长剑,沉声一喝,便猛力将那剑刺入桌中尺余。
“大梁自建国以来,从来便以武为首,以军为先,便连如今陛下立储,都以长幼为次,修为为先。”
他望着桌上那剑寒意凌冽,厉声道:
“如今千奇百巧之间,倒叫我们得了讯息之利,必是先祖亦在眷顾长公主,让我们放手做事,凭奇武雄兵,立不世奇功!”
“说的好!”宁王眼中似有烈火熊熊,一脸跃跃欲试,便也猛的站起身来。
这密室内其余众人,望着这一老一小二人慷慨激昂,却都有些冷淡,便就是那位被唤做长公主的贵人,此刻也在琢磨徐伯渊先前那些话儿,连什么祖宗护佑都扯了出来,实在有些颠三倒四,不由微微摇了摇头。
那先前说话之人性子却有些直,皱眉道:
“大统领是先前喝多了么,怎么有些少年莽撞意味。”
徐伯渊一愣,眼神微斜,便望了那人一眼。
“到底是我喝多了,还是有些人到了如此关头,心中生了胆怯?贵派千年以降,便与极宗王家交好,如今筹谋大事,你家那个疯疯癫癫的掌门,却又在何处?”
那人脸色一僵,一双眸子冷冷瞥回了眼徐伯渊,低声道:
“来了大梁如此久,倒没曾想到,还有被人说胆小的一日。”
他这话一出,不光是屋内知道他的诸人,便是徐伯渊也是微微一愣,知道这话拿来说这出了名的南洋凶徒,倒确实有些可笑,他却似不在意,朗声道:
“不管如何,如今那处已定,徐某千辛万苦,遣铁甲军逾了防区几千里,便已是立了投名状,再没存什么后路之想了,诸位可能还留有后手,可扪心自问,你们是那处的人么?便是腆着面孔此时投靠过去,就算他们如今放你们一马,日后难道还会给各位太平日子不成?”
众人听了这话,却皆是暗暗点头。
大梁天下,不光是朝野,哪怕武道中,也是派系分明,皇宗独大势压三宗,可其他三宗,却也没一家肯轻易与皇宗结好,各自在朝中有所依靠,更每多明争暗斗。
此次那位琪皇子得势,皇宗必愈发如日中天,只怕便要借机发难,寻着三宗诸派的麻烦,了那些恩怨,在场诸人,可都脱不了干系。
只是长公主思索之间,却有些忧色,把眼轻轻望向宝蓝道:
“别的不怕,可你那边,与吾宗那些血海深仇,我倒真担心他们这次会站在皇宗那边,若那些人也参合进来,那就真大事不妙了。”
“不用担心了,吾宗早来了人,不多,但修为极高。”
宝蓝轻声一句话,却把屋内五人都听的一愣,徐伯渊那张脸都有些发白,寒声道:
“怎么不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