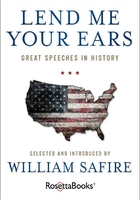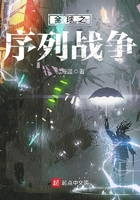可是,海子质疑:“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声嘶力竭,宣称“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的海子“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注:《春天,十个海子》,写于1989年3月14日凌晨3点至4点,这首诗完成不到两周后,海子即自杀)。如果说,这是一个不自量力的诗人,和整个人类的对抗——他竟然为黑夜辩护,那么他的死亡,肯定充满了愤懑和挫败感。然而,又怎样去理解同样出现在诗中的句子:“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它们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繁殖。”这是一个将死之人的不甘,还是以“繁殖”的诱惑来劝阻自己的冲动?
或许海子的呼喊过于锋利,以至于我长久以来徘徊在疑问之中,却独独听不进去诗中的任何一句。可它们已然刺痛了我,那些曾因为海子质疑曙光而生的疑惑,又全部被用来质问那些流逝黑夜的愿望:你们到底期待什么?
黑夜除了自己便一无所有,你不能向它索取黎明和曙光。相反,它存在的意义不是流逝,却是保存和联系。夜是一条绳子,但往往被视而不见,就像我们看不见它没有棱角的颜色一般。《诗经·唐风·绸缪》:“绸缪束楚,三星在户。”《诗经·豳风·七月》:“昼尔于茅,宵尔索綯。”夜的绳索收束了白昼,白昼在夜里得以休养、保藏。因此,诗人才不厌其烦地将绞索入屋、束薪于库的夜景编入诗章。夜之绸缪,千丝万缕,有多少种思绪,就有多少缕丝绦。并且,就像连接不曾交汇的天空和大地,一片无需边际的夜,随时为记忆备好回溯的藤蔓。
夜里的思绪绵密而悠长。如在此刻,月色髣髴,摇曳蔓延;如在往昔,夜雪悄然,飘扬轻旋。曾在窗边铺开被褥,月光倾泻,洒满被面,触手棉白,月色柔软,南风的夜,上无片瓦;也曾被限电停灯,一截短烛,一杯热水,细细的光晕和绵绵的蒸汽,给我抵御寒冷,陪我读那些放不下去的文字,狂想又是一夜。
在这绵密而悠长中,白昼的幻想进入夜的梦,而梦境幻化,翩翩起舞。《庄子·齐物论》曰:“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一只翩跹的蝴蝶,就是全部。夜色不只泯灭了天与地的差别,还打破真实与幻想、清醒和梦境的壁垒,生活进入艺术,忽视了之间那堵不见庭院的深墙。
然而,忽视也只是忽视,黑夜的心中,总有一个无法释怀的白昼。庄子有鉴于此,不得不讲述这样的故事:“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庄子·天地》)一个面貌丑陋的人,在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取来火把,惨淡地希望新生的孩子不要像自己一样难看——黑夜无力遮盖人们对白昼的惊恐。即便是庄生晓梦,可一旦醒来,则蝴蝶、庄周判然两分,知蝶是蝶,知周是周。“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南朝·谢庄《月赋》)黑夜让位于白昼,但哀伤踟蹰,郁结成露,沾衣为霜,挥之不去。蓦然回首,那残月一痕,也划成心头亘古的忧愁。
夜以诉怀,夜以抒忧。然而,人们总是丢失夜的绳索,像是“厉之人”丢失了姣好的面孔。因此,那些多愁善感的诗人呼唤着,不仅求助浑然的黑暗,也滥情于春末的柳絮和残秋的烟景,在用文字垂下的华美帷幕中,时而孤芳自赏,时而顾影自怜。但真正的诗人没有帷幕,海子清晰地感觉到“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而在“在光明的景色中”,“十个海子”不断地“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还厉声紧逼:“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于是无路可退的海子“野蛮而复仇”,用最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这无视天地分离的大风何其壮观,他根本是一个从地狱返回人间的海子!
我能理解那些退到帷幕之中的文字,相信海子也能理解。事实上,我看到过海子同白昼和解的努力。那是他的另一首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同样是夜色。虽然海子宣称他“只有戈壁”、“不关心人类”,并且“这是唯一的,最后的”之类的字眼,仿佛也告诉别人,他已然被逼进角落。可恰恰是这唯一和最后,还保有草原和姐姐,而“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的海子则孑然一身,无可掠夺。那一晚的德令哈,石头是石头的,青稞也只属于自己。夜晚只属于夜晚,从不是白天的延伸和附属;海子握不住的眼泪,也和任何未完成的工作无关,自然而然。因此,这一切都不属于人类,也无需“关心人类”。可是,那些我们所熟知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做一个幸福”之人的愿望,统统要“从明天起”——海子最终抛弃了黎明,永远的回归黑夜。连同那些“劈柴喂马”“粮食蔬菜”的温馨,都决绝地留给了他所不关心的人类。
当然,海子属于海子,剩下的大多数都只能关心人类。而我,一个常常熬夜的人,总还相信那条绳子可以找得到。“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宋·范成大《田园四时杂兴》),《诗经》时代的古老传统一直被继承,在世代传唱的歌谣中,无论是书卷文雅,还是村哑啁哳,总会有一条绳子,将夜的给予夜,自己保留给自己。
此刻,我在一盏台灯之前,将要跨越最后的黑夜。启明荧荧,树木渐露醒目的枝丫。眼前是清晨的残夜,天色如茶落杯水,丝丝散开。寒霜两点,一在树梢,一在窗棂,打得视线濛濛一片。街头的萧索同屋内的低鼾一样阴沉,掩盖不住野猫柔软的脚步。一万个窗子的夜,比乞丐的呢喃还要卑微,却和坟墓上的野花一样娇艳……
点评:常常熬夜的人如不是为了赶白天未完成的活儿,则熬夜就变成守候一个人的精神小天地,如月明同学所说:“总会有一条绳子,将夜的给予夜,自己保留给自己。”这让我忽然想起了朱自清的那句话:“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夜屏蔽了尘世的喧闹,屏蔽了人间的是非,所以,夜色将至,会让在白天心绪不安顿的人,在安静的夜里回归自我。
月明同学的文章总是挥洒自如,这得益于他丰富的阅读,许多素材有招之即来的感觉。读之丰则思之深,因此,月明同学对人生的思考也常有独到之处,这篇《熬夜随想》对夜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就是颇具启发性的。(范文彬评)
梦
2004级·王心宇
昨夜梦里是淡淡的阳光,照射在六月江边碧绿的草丛上,一切都闪闪发光。
光,笼罩在那光芒中的你,微笑着伸出手来。
光,过了这么许久,我可以如此称呼你吗?
仿佛心底的一个创伤,从开始的刺骨疼痛、喷涌而出的疼痛,变成了现在的丝丝缕缕。久久地、久久地缠绕着、紧抓着我的心脏。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作为插班生第一次走进了陌生的教室,面对着陌生的脸。自我介绍时,抬起头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后排的你。
微白的皮肤,从挽着的卡其绿色的衣袖里露出来。黑发。光线透过窗外丁香树丛的枝丫在你的脸上投下了斑驳的阴影。偏又把最亮的光线折射在你的眼睛上,你不得不眯起琥珀色的眼眸,猫一样看着我。唇角轻轻上扬成优美的弧度。空气潮湿,在那一瞬间好像凝固成了一个固有的形状,穿过所有的颜色,我只看见了你。
就这么看见了你,遇见了你,没有日剧里突如其来的大雨,没有只容得下两个人的屋檐。只是如此平凡的初次照面:新来的插班女生和一个普通的男生。不过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
彼时高中三年级开学。现在已经是高三毕业后的第四个年头。一年加四年,一共是五年。
这可能是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女生,所有所有人都可能遇到的事情。那种青涩的,纯净的感情。像蔓生的植物一点一点,爬满心里每一个角落。
你不是小说中桀骜的男生,总是酷酷的没有表情,也没有一张走到哪里都能惹来尖叫的帅帅的脸。你只是很普通很普通的男孩,中等的身高、中等的成绩,连体育都是男生中比较中等的那一种。可是你有一张扯扯唇角就很清澈灿烂的笑脸,有像光芒一样让我仰慕的笑容。
你就在我身后两排的位置,可是必须要整个身体都转过去才看得到你。只能默默地注意去听你的声音,不低不高的声音。干净的声音。总是明朗的声音。有时候也有喊的,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谁谁。从你口中喊出班级同学的名字,大多时候只是约了去踢球而已。我只是默默地默默地去听,坐在你前面两排的位子,挺直了身体。
渐渐和周围的女生混熟了,开始加入课间幸福的八卦讨论。从某某个明星如何如何,直到班上的男生。多数是说可以称为校草的俊,他怎么怎么在校公演的时候出尽了风头,如何如何又拒绝了谁。关于你的消息好少,可是我还是捕捉到了一些关于你的点滴。
比如听说了你是B型血,双鱼座,没有近视。
听说了你的家在医院后面的家属楼里。
听说了你最爱足球,每个周末一定会到西面的球场。
甚至……还听说了……你喜欢的女生。
那天的天空水一样碧蓝,阳光照射在敞开的玻璃窗上面,转了一个角度,让我的眼前一片白花花的。我眯起眼睛,发现根本看不清老师的脸。只有她的声音七拐八拐地钻进耳朵,好像是讲中世纪欧洲云云。我的嘴角上扬了一个弯度,听到心里稀里哗啦的声音,我在讲台上时,你其实也看不见吧。
恍惚间觉得我们之间两排的距离,变得那么遥远。
那个有着一头漂亮长发、美丽眼睛、举止高雅的女孩,在我的前面安静地坐着。可是她现在站在你的眼前,隔在我们中间,让你看不见我的脸,我那在一头短发下面,普通而不加修饰的,因为你而开心或者忧郁的脸。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幻想着所有的能跟你说话的理由。比如借一支笔一类的。简单得好笑,其实不需要任何理由和借口吧。只是那样想,觉得幸福地想。
周末的时候跟妈妈借口要去散步,去了西面的体育场。进大门的时候一个白色的足球卷着灰土滚落到我的脚边停了下来。然后,看见满身汗水的你朝我跑来,阳光又多了N个折射的角度,在汗水上闪闪发亮。笑容满满的脸,让我的心脏险些漏跳了一拍。
是你!你家在附近吗?
我忙把球还给你,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赶紧点了点头。你接了球转身跑回了场上。我们的第一次对话,仅仅是这样吗。你不知道其实我们的家在一条直线上,你家到体育场的中间点就是我的家。我坐了七路车绕了一个大大的弯才来到这儿的。我绕着足球场的边缘看着你,看着你偏瘦的身材,看着你的衣服迎着风在背后鼓得高高的,看你的脸,专注于攻守游戏的认真的脸。比画着想象着,在心里成了一张张的速写的图样。一张一张一张张,飞扬的白纸把我掩埋。
渐渐地熟识起来,从那次没有回答你的对话开始。因为我有计划地接近,抑或许是因为她,在我身边依旧举止高雅的她,美丽得像SD娃娃的她。我不知该如何去形容这么让我嫉妒的她。从那次串座开始跟我直到毕业同桌的她。那次串座把俊串到了她的前面,也把你串到了我前面,但依然是两排的间隔,我可以放肆地看你黑色的发丝,像画笔没有停住的样子,在脖子上留下散落的线条。
忘记了什么时候开始叫你哥哥的,只是因为你说我像一个懂事的小妹妹。我一直这样叫你,偶尔也会叫你“??”,你不知道这句在朝语里称呼自己爱人的称谓,只是问真的这么叫吗?认真得让我想笑。又发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比如说你只爱喝碳酸饮料,一天要喝两瓶,比如说你喜欢颜色不明不暗的牛仔裤,比如说你喜欢听已经过了气的歌,比如说你喜欢吃热的菜,再热的天也不吃冷的。也有以前就知道的,比如说……你还是最喜欢她。
自习堂上一个字条把正在昏睡的你砸醒,看着你睁开惺忪的双眼,环顾四周找惊扰你美梦的罪魁祸首,锁定目标,然后伸手拿起。晚上的灯光发出微微的声响,你展开字条。然后回过身,冲我点头。灯光猛地灭掉,一闪,再闪,我看见你的脸也跟着忽明忽灭,恍惚觉得我们隔了一个光年。灯光作了最后一次挣扎,然后彻底地灭掉了,毫无生气。周围的同学一片欢呼,在昏天暗地的题海中得以暂时的解放。随后欢呼在老师走进教室的瞬间戛然而止,在来者宣布放学时又一次响起。我听见你在黑暗中打了口哨,四处漆黑,但我知道那是你的声音,只有你的声音我才能听得真切。
你答应了我第二天陪我去写生,你总是宠溺我,让我忘乎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