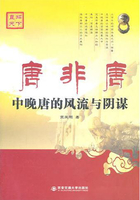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有本事又厉害,遇上不高兴的事儿就大吵大嚷,要是遇上大事紧要事,没等想出解决的好办法,早就嚷嚷开了。殊不知静水深流,只有修炼到像那老太爷这样,才是一流的功夫。如果没有这样的修为,只怕那老太爷没死在甲午海战的战场上也要死在战后受的窝囊气中。
越是生气,那老太爷就越冷静。那木深知祖父这一点。当下也安下心来,默默地想些对策。
韩百济违心地说着刺激李迎春的话,并不都是为了遵从那老太爷的嘱咐,还有一部分则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这小算盘是从一开始就扒拉开的。
那木和李迎春在对待俩人的那段感情上,明显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当初的整个过程并不如俩人各自认为的那样,而是掺杂进了为俩人所不知的人为因素。
学业未成再跟一个身份低微的汉族女子勾搭,这岂能被那老太爷容忍?那木心里不以为意,岂知那老太爷已经如临大敌!为了那家的未来,那老太爷只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给韩百济下令,让他不露痕迹地拆散那木与李迎春。
韩百济假借那木之名用二百块大洋羞辱了李迎春,又在那木与李迎春之间搬弄了些许小是非。本来那木与李迎春两个人就羞答答青涩涩的,被这么一搅和,就完全不是滋味了。
等到李迎春成了寡妇,韩百济才觉得终于可以配得上她了。如今,这个寡妇还在打自家少爷的主意,真是让他瞧不起。
韩百济先是瞧不起自己,现在又瞧不起李迎春。可能有一天还要瞧不起主子那木,一辈子都是在瞧不起当中度过,可见内心是何等的卑微?如果不是几世修来的奴才身份,想如此都难啊!
无论韩百济怎么劝说,李迎春都要找那木理论个明白。
韩百济觉得女人被情感网住的时候是没有智商的。他有些粗暴地扛着李迎春走在中富街,直至将她扔进家门,并且大声豪气地告诉她,过了今天,你爱怎么闹怎么闹,别让阴曹地府的怨鬼们看你的笑话了!
这么一弄,李迎春一下没了动静。不管哪个年代,大抵女人都是这样,越是有人哄着捧着越是闹得欢。就好像得宠的小孩子一样,跌倒了也不要自己爬起来,非要等到大人来抱,本来睁着眼睛静观其变,谁知被抱起来就开始闭着眼睛瞎哭。
李迎春也是一样,在那木面前不得发作的女人病,在韩百济面前可以肆无忌惮。等到韩百济也不耐烦,她也闹得够了。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当年革命党大喊破除封建礼教,第一个拿出来批斗的就是这句话。但细想想,孔夫子还真够冤的。
一个女人把最世俗与粗陋的一面展示给一个男人之后,这个男人仍然能够接受她,这大概就是除了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另一种爱情模式。
李迎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把这一切都给了韩百济,留给那木的还能是什么呢?
人间的月光照得亡魂的路透亮,世人的路却被乌云遮挡。
对于那家来说,这个“鬼节”,鬼闹得可真不轻。
一连几天,都没有族谱的消息。因事关那家的尊严,不能大肆张扬大动干戈,更不能满城发布告,只好在可控的范围内寻找,并随时留意可疑的异象。
那木的婚期已定,那老太爷虽然嘴里说不搞繁文缉节,但还是要走程序。在媒人的陪同下,那老太爷去富察家送聘礼。韩百济则被安排在那木身边充当耳目,以防他跟李迎春再生什么枝节。
那老太爷愿意相信那木娶亲的诚意,但还是做足了防备措施。这跟他是军人出身不无关系。
听闻军事中的作战计划都有两套。如果当统帅的做打胜仗的计划,军师肯定要做打败仗的计划,两套计划分别制定,但要配合着用。不能都做打胜仗的美梦而忘了留后路,也不能悲观地都做打败仗的计划而放弃了主动进攻的勇气。总之,统帅和军师要做不同的打算。
除非如诸葛孔明般千年难得一见的军事奇才,才可以一人身担两角,同时做好胜仗怎么打和败仗怎么逃。
那老太爷无非是一个水军小头目,不是将才,但把这套军事规矩带到生活中,反倒屡试不爽。
韩百济不想让那木感觉到被监视,只好若即若离地在远处瞥着那木。
那家在河边有一小块菜园,里面种满了应季的蔬菜瓜果,足够一家人随时取用。韩百济一边在菜园里做帮工浇水,一边留意着那木的动向。
那木闷在屋里读书,可心却沉静不下来。拿书的手细长而白哲,血管像地图上的河流一样在手背上若隐若现。那木有一双完美的医生的手。想到这双手在李迎春的背部娴熟地处理伤口,那木不禁放下书,端视起来。
李迎春背部的伤口在位于心脏右边三公分处,是匕首的尖刃直刺造成的皮外伤。
李迎春为何在自家附近?李迎春跟盗贼真的没有关系吗?到底是谁伤害了李迎春?李迎春现在过得怎么样?
想到今生跟李迎春不会再有任何关系,那木不禁生出一种悲悯。转而又把这悲悯转化成对明珠的愤怒。这看起来实在好没来由,但却是那木的真实心境。
想起李迎春又想起明珠,想起明珠又想起结婚,想起结婚又想起李迎春新婚守寡……转了几圈之后,有些迷糊的那木换了身衣服出了大宅的院门。
还没等那木想好去找李迎春的借口,韩百济光着膀子挥着手冲那木喊起来:“少爷!少爷!快过来!来呀!”
阳光有些热辣辣的刺眼,但风是凉爽的。那木故意对着太阳瞪大眼睛,虽然只是那么一瞬,但很快一阵酸涩袭来,眼泪不由涌上眼球。
这是最调皮的行为,也是那木唯一抗拒那老太爷的孩童行为。那木有些丧气地向河边走去,去问问韩百济吧,就算他没什么主意,有个人商量总归比一个人闷想好得多。
韩百济看起来很兴奋,不过是为了吸引那木而已,其实菜园里能有啥稀罕的东西。
“给,顶花带刺的嫩黄瓜。看,像不像戴着花帽子的小姑娘!”韩百济像逗小孩一样说给那木听。
那木接过去,对着黄瓜尾巴咬了一口。
韩百济嗽了嗽嘴,像是失望的女人一样:“就这么吃了呀?”
“李迎春家还在老地方吗?”那木装作毫无私情似的直奔主题。
韩百济料到那木会问自己这事,虽然有所准备,但摘西红柿的手还是用力过猛,一下将熟透的柿子捏了个稀烂。
“嗯,还在老地方。”
“我带了点消炎药,想给她送过去。”
“这事吩咐下人去就行了,再说前天刚送过去,还去呀?”
“怎么?我想去看看她的伤口恢复得怎么样,有什么不妥吗?”
“不是我当下人的说过格儿的话,今天老太爷可是去富察家放大定,少爷您是要娶亲的人了,总归避讳避讳吧?”韩百济少有的立场鲜明,他以为提到老太爷一定会让那木退却,但想不到那木快速而有力地回击了他。
“都什么年代了,有什么好避讳的?再说,我有事要找她问个明白。”那木将韩百济送他的小黄瓜带花一口吃掉,“你再帮我摘些,都要跟方才的一模一样,像小姑娘的。”那木故意拿出主子的腔调指挥韩百济,实际上是一种戏谑的心态。说完自己笑个不停。
韩百济的整个嘴都裹在西红柿上吸吮着,以为那木要问李迎春的是当年的情事,为了急于阻止那木,汁液呛得韩百济一阵咳嗽,红色的汁液顺着嘴角流出来,越是着急越说不出话。
“看你这猪样!怎么光顾着吃!快去帮我摘啊!”
韩百济为了拖住那木,顾不得擦脸,只在水桶里洗了洗手,就跑去黄瓜架旁。
等到韩百济手捧着顶花带刺的小黄瓜过来,那木已经不见踪影了。韩百济顿脚,扔了小黄瓜,将一桶水从头直接浇下来,然后擦干身子穿上衣服匆匆跑了。
那木以为李迎春还在店里当帮工,不紧不慢地向中富街走去。想到当年也是这样走着去理发,那木突然一个激灵,仿佛李老爹的剃头刀子刮过头皮时凉咫爬的感觉。这个促狭的韩百济,偏偏要跟我作对,难道我连见一见李迎春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去见李迎春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
等到那木从李老爹的口中得知李迎春不在家,又转回头去小山日文学校的时候,韩百济早就以李老爹突然生病为借口将李迎春叫走了。
那木有些沮丧,来时路上的兴冲冲一下子变成回去时的腿酸脚乏。人力车的铃声正在这时响起。
“车夫!车夫!”那木挥手招呼人力车,一时精神松懈索性蹲在地上等。
人力车来到身边,那木正要上车,却冷不防被身后冲出的一个人抢先一步。
人力车夫与那木都有些吃惊地看着车上坐着的人。
“是你!”那木打量着他,认出是那个从上海到安东一直同路的年轻人,仍是一身中山装,口袋里插着没有帽的钢笔。
“我要去城隆庙。城,煌,庙……”乘车人说了句日文,然后一字一顿地重复了几遍城煌庙,看也没看那木一眼。
听到乘车人满口日文,车夫不觉面露难色地看着那木。
那木不理会车夫的眼神,觉得这个日本人真是不讲道理还理直气壮的样子。
“这是我先叫的车,请你下来!”
日本青年不为所动。
那木又重复了一遍,日本青年理也不理。
车夫拉了拉那木:“大爷,他是日本人,可能不会说汉语,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再等等,一会儿别的车夫就来了!”
那木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最主要的是他认为,这明摆着不公平!如果这个日本人态度客气,说他有急事,这又另当别论。可看他的神态,明显是目中无人的冷漠与傲慢。既然如此,自己如果让步就是耻辱!
“这事不用你管。”那木甩了一下胳膊,想挣脱车夫拉扯的手,谁知,车夫的大手竟像螃蟹钳子一样夹得紧紧的。
“你这是干什么?”那木这才把目光投向车夫。
人力车夫膀大腰圆,全身上下裸露的皮肤都被晒成古铜色,与偶尔露出来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拉车时长期弯着的腰似乎直不起来一样,谦恭地甚至带有一种可怜巴巴的恳求看着那木。
“还不快走!我要去城陛庙!”日本青年再次发号施令。
“车是我先叫来的,车夫不会拉你去城煌庙!”
“支那猪,听不懂日文吗?”
那木想都没想,一拳打过去。日本青年看起来又矮又瘦,但反应很机敏,竟从车上弯腰滚下来,躲过了那木的侧勾拳。
车夫仍旧拉着那木,让那木有些愤怒:“你拉着我干什么呀?松手!”
“支那猪,看你挺有种,来吧!让你领教领教……”日本青年的语速过于快,加上跳动躲闪的动作,活像一只猴子。
“你这杂种!”那木被完全激怒了,边用日语回击,边摆开架势。
车夫的手慢慢松开那木的衣襟,躲到安全地带。
那木与日本青年不再对话,只想制服对方。虽然那木身材高大,但却没有占到太多优势。日本青年仿佛一只醉酒的公鸡,血液沸腾,斗志昂扬。
那木不理解,那个在火车上一言不发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人,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
虽然一直以来日本人在安东县多有得意,也不乏欺负中国人的事件发生,可还没激化到一定矛盾。但这个家伙已经完全超出强烈的优越感转变成对中国人明目张胆的歧视,这实在让那木不能容忍。
那木的愤怒与日本青年的轻蔑,两个人被各自的精神鼓舞着打得不可开交。
周围开始拥上来一些人,更多的是日本人,并不去拉架,而是在一旁评头论足。
一些中国人也凑过来看热闹,听了车夫讲的因由,都替那木不值,这么点小事,跟日本人斗干啥?
那木在安东县算是个名人,仅限于名气比较响亮,一般的平民百姓又有几个知道那家的少爷长什么样呢?更不会联想到那家的少爷居然文武双全,打起架来不比卖鱼的张三斯文多少。本着在日本人的属地上中国人老实本分不插手的原则,众人也只是看着,小声嘀咕议论。
开始俩人还有套路,打了一会儿就没了风度,为了取胜不免开始走下三路。
那木终于抓到一个机会,一把拽住了日本青年的脖领子,随即施展中国式摔跤的功夫,一个大背将他压在地上。借助体重的优势,日本青年只好老实挨揍。旁边的中国人发出一阵叫好声,奇怪的是日本人也一样。
“支那人是日本人对华夏先祖的尊称,如果你叫祖宗为支那猪,你自己是什么?”那木气喘吁吁质问日本青年。
日本青年敛牙咧嘴的脸露出一些不明所以的笑意:“斗转星移,海枯石烂。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那木重重地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日本青年:“回答我!”
“华夏先祖早就灭亡了,剩下的不过是支那猪!”
那木的耳朵好像是被打坏了,日本青年的话听起来带有嗡嗡的双音。
“支那猪,支那猪……”那木被这咒语一般的话刺痛得无以复加,突然像暴怒的狮子一样开始对日本青年拳打脚踢。
围观的人看得有些不忍。
日本青年在那木的暴怒中发出尖利的笑声,仿佛是一种无形的能量附着在他的身上。
如果不是小山一郎的出现,那木险些酿成大祸。
当得知这是小山一郎的次子小山广文时,那木仍有些缓不过神来。不过,挨打的身体开始四处发射出疼的信号给大脑,这让他开始清醒了一些。
小山广文伤得不轻,被立即送到了满铁病院。其实也不过是做做样子,那木不是嗜血的暴虐之徒,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也还留有分寸。
小山广文其实认识那木,并对他做了很多的分析。他来到安东县的这几天,全面分析了小山一郎实行的措施,对父亲的做事风格很不以为然。觉得对待那家这样的满洲狗何必软塌塌,只需要给他几拳问题就解决了。
日本人中持这种论调的为数不少。其实小山一郎心里也曾有过类似的念头,只是没太敢冒进。况且,大日本帝国国内形势如何,他还不能做出切实的判断。
小山广文说,当初大日本帝国与清政府实力相差悬殊,但却准确地找准了战争的契机,这都是因为先期的试验起了作用。他还说,我们对付那家也是一样,别看他们是名门望族有钱有势,不痛不痒地从各个方面刺激他,看看他的反应,再判断怎么对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