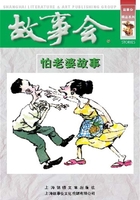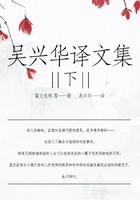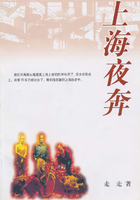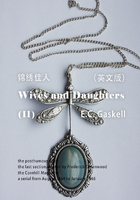1964年,对中国的科技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贺喜的年头。
众所周知,自1958年起,中国科研单位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尤其是反右斗争扩大化,致使不少科技人员受到冲击,积极性遭到严重挫伤,从而阻碍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拖延了人造卫星发射方案的诞生。
但从1960年冬起,科技界的形势便开始好转。为纠正错误,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聂荣臻亲自组织领导有关人员,写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年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这个草案时,刘少奇、李富春称赞这是个好文件,而邓小平则说,这个草案要在实践中加以补充,使之成为科研工作的一部宪法。1961年7月19日,中央将此文件批转全国各大单位,要求必须贯彻执行。
“科研十四条”总结了建国后科技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针对“大跃进”中发生过的错误,规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按照“科研十四条”规定,各国防科研单位对科研工作实行了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的“五定”制度,并规定科技人员每周至少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专业工作。1962年2月,聂荣臻还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陈毅在会上明确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对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热情,调动其积极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仅如此,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聂荣臻元帅还以个人的名义向海军、北京、沈阳、济南和广州等军区领导呼吁,尽快调拨一批副食品来支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批食品到来后,均以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专门分配给专家和科技人员,而其他行政人员包括领导干部在内,都不许分给。食品下发后,聂荣臻还派陈赓大将去检查落实情况,当得知这些东西确实已分到了科技人员的手上,吃进了科技人员嘴里,他才放下心来。陈毅元帅对关怀知识分子这一举动,亦表示坚决的支持。他说、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国家的宝贝,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要硬起来,就得靠他们,一定要保证他们起码的生活。贺龙元帅听取了研究院领导汇报情况后,也表示说,要好好照顾好科技人员的生活,特别是对老知识分子更要注意,不仅要让他们本人吃好、住好,就连他们的家属,小孩也要照顾好。罗瑞卿则让秘书安东亲自去研究院了解科技人员的住房、伙食、取暖等情况,一旦发现谁的暖气不热,或者灯泡不亮,立即就找有关领导马上给予解决。
为进一步推动国防科技工作的开展,1964年4月,张爱萍还在南京十四所专门主持召开了现场工作会议、与会者有解放军各总部、工业部、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共计600余人。这是60年代国防科技战线一次大的集会。聂荣臻向大会写了信,刘伯承还亲自接见了大会代表。这次会议将日后的国防科技工作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由于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政策正确,措施有力,特别是对科技人员政治上信任,工作上依靠,生活上关心,因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才能得到了最佳展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到1964年底,国防工业部、研究院、国防高等院校以及试验基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已达16万人,形成了一支从常规到尖端的庞大的国防科技队伍,因而被人们称为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
当然,这一时期国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困难。但导弹的研制工作始终处于由仿制转向自行设计的大建设、大发展时期,国家给予尖端武器以特殊地位,制定了自力更生,大力协同,优先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方针。在财力和物力上均使“两弹”发展处于优先地位。对导弹的研制。毛泽东主席还明确指示:“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而聂荣臻元帅则再三叮嘱:“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争一口气、突破从仿制到设计这一关,迅速发展提高,建立我们自己的高度技术水平的导弹技术体系。”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导弹发射成功。同年7月9日和11日、又连续发射了两枚导弹,使全程试验均获得圆满成功。这表明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经过了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艰难历程,将由研究试验转入定型试验,由工业的批量生产阶段进入航天工业发展的新时期。
接着,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又爆炸成功。这一方面标志着我国工业初具规模,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则显示了我国的新型材料、电子元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测试技术、计量基础等得到了新的发展。
于是,导弹的成功,原子弹的爆炸,为发射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因而发展人造卫星的问题自然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历史把这个特殊的机会抛给了赵九章。
1964国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赵九章作为科学家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赵九章的情绪始终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自年苏联卫星上天以来,便几乎放弃了自己从事多年的大气物理研究工作,转而献身于中国的空间技术。整整七年来,中国的人造卫星便一直在他大脑的天空旋转不停。导弹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他似乎获得了某种神奇的暗示、下决心要加快人造卫星方案的制定。1964年10月下旬,他和方俊、钱骥等几位科学家应邀去酒泉发射基地参观了“东风”二号导弹的发射、并在基地座谈了运载工具的发展前景和卫星发射工具的可能性问题。基地科技工作者纷纷向他提出呼吁,希望尽快考虑发射人造卫星问题,使他的情绪又受到了极大的感染。而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当他听完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更是激动难抑,信心百倍。于是,他决心把多年的愿望和奋斗变为现实,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第二天便当面交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
这份建议不过寥寥几千字,却是中国空间史上一份极为珍贵的文献。赵九章在这份建议书中开门见山,直抒胸臆,除了对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意义作了简明的阐述外,还对发射人造卫星的技术途径以及现已具备的条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周恩来总理接到这份建议后,十分高兴,利用开会的间隙,与赵九章作了简短的交谈,并希望赵九章回去后尽快拿出个成熟的意见。
会议一结束,即1965年1月6日,赵九章又以地球物理所所长的名义与自动化所所长吕强一起,联名向中国科学院党组递交了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建议尽快加速发展人造卫星的步伐。
党组书记张劲夫和副院长裴丽生见此报告后,很是激动,当天便批转给了星际航行委员会主任竺可桢,请其尽快审阅处理。竺可桢阅完报告,当即便在报告上欣然批下四个大字:“刻不容缓!”
于是,在张劲夫、裴丽生、竺可桢的组织下,很快召集有关专家对赵九章和吕强的建议书进行了讨论,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份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建议报告,正式呈送中央。
与此同时,中国航天事业的倡导者钱学森在认真分析了我国研制人造卫星的有利形势后,也写出了一份制定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的建议。钱学森在这份建议中说道:
自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对这些技术都有过一些考虑,但未作为一项研制任务。现在看来,弹道导弹已有一定基础,如进一步发展,即能发射携带仪器的卫星,计划中的洲际导弹也有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工作是艰苦复杂的,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研究,才能到时拿出东西。因此,建议早日主持制定研究计划,列入国家计划,促其发展。
聂荣臻看完钱学森的建议后,作了如下批示:
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这点我一直很明确。人造卫星早就有过考虑,但过去由于弹道式导弹还未搞出来,技术力量安排上有困难,所以一直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钱学森这个建议,请张爱萍副总长邀请钱学森、张劲夫等有关同志及部门座谈一下,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1965年3月,在张爱萍的主持下,国防科委召开了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张劲夫、钱学森、孙俊人、赵九章、吕强等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上、与会者对发射人造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对运载工具的选择及卫星的重量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最后一致认为,现在技术基础已经具备,研制和发射卫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科技上都有重要意义,应该统一规划,有步骤地开展卫星工程的研制。4月10日,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又召集张劲夫、张震寰、钱学森、赵九章、钱骥等,对卫星的规划方案问题进行了讨论。赵九章在会上作了卫星方案设想的发言。4月29日,国防科委根据各方的讨论意见,形成一个报告,正式上报中央。
此报告设想在1970年至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并建议卫星本体、探测仪器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工具由七机部负责,地面观测跟踪、遥控系统以四机部为主,中国科学院配合:宇船医学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承担。
中央接到报告后,罗瑞卿受周恩来的委托,邀集有关专家对报告作了进一步分析研究,认为国防科委的报告切实可行。5月,此报告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得到批准,并责成国防科委具体组织协调。
从此,中国的人造卫星按正式的分工纳入各部门的长远规划及本年度计划,开始了全面的研制工作。
卫星专家潘厚任是在1965年4月的一个深夜突然接到赵九章的电话的。潘厚任是学天文的,1958年“581”卫星小组成立后,便开始搞开了卫星轨道的计算。但由于种种原因,七年时间转瞬而去,人造卫星的问题始终没有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起来,为此,他常常深感不安。3月6日晚,中国科学院召集有关研究人员会议,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国科学院参加人造卫星研究工作的指示。会议结束的当晚,他便翻开了有关卫星轨道的资料,独自久久坐在小小的简易台灯下,激动得几乎一夜未眠。因此,接到赵九章的电话后,他便披衣下床,急匆匆地赶到了赵九章的家。
这个夜晚的赵九章情绪显得格外激动。据潘厚任后来回忆说,当他赶到赵九章家时,数学所的所长关肇直和渠柏新两位专家已经就坐。彼此简单介绍后,赵九章便急切地说道:“我去年年底写信给周总理,说明我国着手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在导弹研制过程中,把导弹打靶试验和卫星发射结合起来,可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赵九章停顿片刻,翻了翻手中的一个小本,又继续激动地说道,“现在周总理已发出指示,要我们提出设想规划。我们从1958年开始、就一直在作准备,日日夜夜都在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现在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但是,试想一下,一颗几米尺度的卫星送上轨道后,如果不能紧紧抓住它,就像几公里外的一只苍蝇,如何去控制?因此,要发射卫星,首先要把卫星运行规律、轨道计算、测量、预报以及跟踪站的布设等,搞得一清二楚。科学院理当把此承担起来,先走一步。希望关所长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尽快落实此事。”
接着,赵九章又对潘厚任说:“你是学天文的,过去又搞过卫星轨道,今后由你代表组参加此项工作,并和数学所具体联系、协调。”
第二天,潘厚任、何正华和胡其正三人便组成了卫星总体组,由何正华担任组长。同时,在关肇直所长的具体安排下,又将以叶述武为首的力学组转到了卫星轨道的计算上来,并邀请紫金山天文台也来人参加。
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的胃当时刚切除了3/4,一天要加十余次餐,而每次都是半杯开水和两块饼干,行动极为不便。但接到通知后,张钰哲台长当即便领着赵先孜、张家祥等几位专家赶到了北京。这样,中国科学院集中了最强的阵容,成立了专攻卫星轨道计算的联合小组,立即投入到卫星上天后的测轨、算轨以及预报等工作中。
与此同时,中科院其他有关的研究所亦纷纷行动起来,如力学所、电子所、自动化所和原“581”组,均派出强有力的代表,定期集中开会,交流报告,一起商讨卫星的型号和发展规划问题。
1965年5月31日,中科院新技术局副处长舒润达代表院领导,正式宣布成立卫星本体组、“581”组、轨道组、生物组和地面设备组,并要求在6月10日前必须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和卫星系列规划轮廓。
于是,有关人员立即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准备。赵九章和钱骥配合院领导负责全面组织工作,钱骥还亲自带领18位业务骨干定期会商。虽然当时专搞卫星的只有何正华、潘厚任、胡其正三人,但在原有基础上,只用了十天时间,便拿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初步方案。此方案归纳为三张图、一张表:卫星外型图、卫星结构布局图、卫星运行轨迹图以及卫星分系统组成表。
但初步方案搞出后,这第一颗卫星该叫什么名字呢?
此事看起来虽小,却使许多人都犯了难,如同父母好不容易生下了孩子,却久久苦于取不出满意的名字。
后来,还是卫星总体组组长何正华提议:“我看就先叫它‘东方红一号’吧!”
这一提议得到了众人一致的赞同。于是卫星组携带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初步方案,先后到文津街院部和国防科委大楼,分别向张劲夫和罗舜初等领导作了详细汇报。而且,钱骧等人还带着方案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据钱骧后来回忆说,汇报中,当周恩来总理得知他姓钱时,便握着他的手对众人风趣地说:“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姓钱,看来我们搞原子弹、导弹和卫星,都离不开钱啊!”
为保证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开展下去,1965年7月,中国科学院又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的建议》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空间技术的指导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1.以我为主,走自己的路。根据我国自己的需要来确定卫星种类,据我国特殊条件来确定技术途径。赶超问题要以解决自己的需要为衡量标准:
2.要大力协同,元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3.卫星工程综合性强,协作面广,必须统一领导,集中管理;
4.人造卫星要采取由易到难,由低到高,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方针。首先以科学试验卫星开路,然后再发展以返回式卫星为重点的应用卫星系列;
5.发射卫星的运载工具,在初期以中远程火箭为基础,进行适当修改或配以专门研制的末级火箭发动机而成,下一步再发展大推力运载火箭;
6.系一颗人造卫星和初期卫星的发射,应利用已有的火箭发射试验基地,同时要在适当地点建立新的发射场;
7.地面观测系统研制周期长,工作量大,必须分期建设,以近为主,远近结合。
中科院在作此规划时,迫于当时的国际环境(美国对中国长期的技术封锁和年中苏关系的恶化),因而除了从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进行考虑外,还特别强调了人造卫星的政治意义。
1965年8月2日,此报告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在原则上得到批准。中央专委会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提出的要求是:必须考虑到政治影响。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应该比苏美第一个卫星先进,表现在比他们重量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技术新,听得见。
同时,中央专委会还确定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方针是: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并对卫星工程作了明确分工: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测控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负责: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
这样,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便开始进入了工程研制阶段。为全国协作方便和保密起见,再加上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便把搞人造卫星的代号定为“651”任务。
8月17日,裴丽生召集中国科学院有关负责人开会,正式传达了中央专委的决定,并对“651”任务的落实和组织机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同时决定先成立三个小组:一是领导小组,由谷羽(组长)、杨刚毅(副组长)、赵九章等人组成;二是总体设计组,由赵九章(组长)、郭永怀(副组长)、王大珩等11人组成;三是办公室,由陆绶观任主任,操办日常工作。
9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在力学所礼堂连续召开了三次有关人造地球卫星的工程技术人员会议。张劲夫在会上号召大家从各个角度来谈人造卫星的设计方案。最后,还是中国科学院“581”组提出的方案获得了会议的一致赞同。接着,10月19日裴丽生又主持召开了“651”会议的预备会,并在会上形成如下决定:卫星领导小组组长由裴丽生担任,具体领导工作由谷羽负责;卫星总体组由杨刚毅、赵九章负责;卫星本体组由王跃华、钱骥负责;卫星地面组由吕强、王大珩,陈芳允负责。这样,便为下一步全国性的卫星方案论证做好了方方面面的准备。
196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的委托,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论证会,即会议。
这是中国科技历史上第一次著名的会议。会议从年10月20日起,到国月30日止,历时42天。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内容之多,可谓史无前例不少专家后来都回忆说,这是他们一生中参加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主持,杨刚毅负责会议组织工作,出席会议的有: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总参,海军、空军、二炮、一机部、四机部、七机部、通信兵部、邮电部、20试验基地、军事科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13个研究所的代表。裴丽生、罗舜初、张震寰先后在会上讲了话。有关专家分别就第一颗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第一颗卫星的运载工具方案设想、第一颗卫星的地面系统方案设想作了报告。赵九章就卫星的总体设计问题作了总结发言。钱骥就卫星的本体设计问题作了总结讲话。
由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与发射,将是中国迈向宇宙空间的第一步,直接关系和影响到中国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卫星技术、运载工具以及地面台站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因此,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反复慎重的论证。比如,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什么?经技术分析,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应该做到:成功地飞上去,进入轨道运转起来,地面跟踪测量系统能“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让全球人民“看得见,听得到”,并在可能条件下,比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先进。此外,会议对卫星的重量、轨道的倾角、运载工具及地面观测等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与论证。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还特别邀请与会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一起观看了文艺演出,鼓励大伙集思广益,献计献策,搞好第一颗卫星方案的论证工作。
经四十余天的论证,会议初步确定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并将第一颗卫星定为科学探测性质的试验卫星,其任务是为发展我国的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必要的设计数据。而总的要求概括为四句话十二个字:“上得去,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
为了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任务的完成,在组织机构上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1966年初,中国科学院经请示报告聂荣臻后、正式成立了“651”设计院,由赵九章任院长,着重狠抓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和筹建试验室的工作,为加强地面观测跟踪系统工作,1966年5月,中国科学院又组建了代号为“701”的工程处,由著名电子学科学家陈芳允担任技术主管,负责地面观测系统的设计、台站选址和勘察、合站的基本建设等工作。与此同时,七机部第八设计院也开始了运载火箭总体方案的论证和设计工作。军事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也开始按照规划,进行宇宙医学、环境工程的研究试验工作。中国科学院的所属单位,还安排了200项空间技术预研任务,分向全国各地。
至此,中国的空间技术,从1958年毛泽东主席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开始,走过了整整七年曲折而艰难的路程,经历了创建时期、技术准备时期,现在终于进入了全面规划和正式开始研制时期。
然而,正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技术攻关阶段,卫星本体、运载火箭和地面观测三大系统的研制工作取得可喜进展时,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