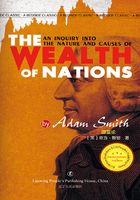苗姑姑站在祠堂的阴影里,背着光,那感觉仿佛是整个祠堂都成为她的背景。如果连同躺在祠堂里的矮胖子叔叔也考虑进去,这样一个背景就显得压抑而沉重。
然而祠堂里热火朝天,一点都不压抑,也不沉重。按照半步村的风俗,葬礼有严格的程序,人们似乎有意用十分繁琐的程序来减轻内心的悲伤。半步村的红白事,都在这个祠堂里操办。祠堂左边的墙上挂着婚庆使用的红绸丝带,右边是葬礼用的麻绳和抬棺材用的扁担,窗台上红蜡烛和白蜡烛交错摆在那里。对于这样悲喜杂陈的状况,半步村的人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
天井的中央摆着方形的桌子,桌子围着四条板凳,许多人围坐在那里,穿拖鞋的人干脆把脚放到板凳上,边说话边用手指抠脚趾甲。他们都是来等吃饭的,和办喜事一样,办丧事也是要请客吃饭的,不过吃的时候多了一个礼节,必须整齐站着吃完第一碗饭,不能发出声音。还没有到开饭时间,祠堂里充满了陌生而又熟悉的东州话。我看到两个叫不出名字的亲戚在吵架,都愤愤然,看样子是为了一条猪尾巴。拜祭矮胖子叔叔的,除了一个猪头,还有一条猪尾巴。猪尾巴代表一年的好运气,所以有必要争抢一番。
苗姑姑将我迎进祠堂的时候,有人便接过我的行李,同时将我的糯米酒打开了,周围都是围在桌子边上聊天的人,由于无所事事,所以几个回合便将酒都干掉了。接着是我的高丽参:“阿施啊,这是高丽参吧?可以拆开吗?”
我转过头去,这哪里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分明是在告诉我她们已经拆开了。或胖或瘦的女人们围在一起,这个闻一闻,那个也闻一闻,都说这高丽参不错,她们像变魔术一般,高丽参很快就都不见了,剩下一个铁盒子,哐当一声被扔到了屋角。
苗姑姑看他们拿了我的东西,便高声埋怨了两句,又转头对我说:阿施呀,你也别见怪,农村人比不得你们城市人,都爱沾点小便宜。我更正说我不是城市人,还是个农村人。
“人啊,活着的时候说不怕死,都是吹牛的,真要死了,挣扎着想活下来,但就是做不到。”苗姑姑口中说着这么沉重的话,但嘴角还带着笑意,露出那口金牙,“去,去看看吧,这种病,他们都不愿意接近,你也别靠得太近。”她回头对我说,我看到她正用无名指撩了撩耳边的头发。
我往大厅里走。矮胖子叔叔的棺木停在厅堂里,已经第三天了。厅堂中弥漫着一股类似烂香蕉的甜味。我轻轻揭开覆盖在矮胖子叔叔身上的彩色锦布,看到一个有点蜡黄的柿饼。他身上的脂肪仿佛都不见了,那么圆鼓鼓的一个人,如今却显得很——也不是瘦,那些肥肉似乎都变成水,被一层蜡黄的皮裹着,似乎针一刺,便会流出五颜六色的汤水来。
我盖上锦布,眼中掠过一丝惊怖,想起了一部日本电影叫《入殓师》,如果能让一个入殓师给矮胖子叔叔处理一下,那该多好。
半步村的人都说,我来到这个世上睁开眼睛见到的第一个人,其实是矮胖子叔叔。我妈带着身孕来到半步村,人们还来不及了解她,她便因为难产死掉了。矮胖子叔叔是这么对人们说的:“我以前以为孩子像猫狗一样要过些日子才睁眼,没想这小子一出生,便睁着乌溜溜的眼珠子瞅着我,眼睛半天一眨也不眨,你说有多神!”
我七岁那年,苗姑姑阴差阳错开始她人贩子的营生。传说苗姑姑要嫁给矮胖子叔叔,但始终没有。人们问及此事,矮胖子叔叔总是摇摇头说,没有的事。问话的人便会傻笑起来。这样傻笑的次数多了,矮胖子叔叔有时也黯然神伤。其时碧河的上游建了一个印刷厂,河水变黑发臭,鱼都浮在水面,翻着白肚皮。矮胖子叔叔每天清晨撑着小渔船,荡开晨雾捕鱼去,但总是空手而归,日子陷入困顿。但苗姑姑的事业却在此时达到顶峰,她的那口金牙就是那时候镶的,金灿灿,成为她的商标。她更爱笑了,满口灿烂,似乎已然忘记那个在她肚子里死去的孩子。我曾经坐在门槛上,看着苗姑姑在门口走来又走去,对着肚子里的孩子说话。直到有一天发现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死去两天,苗姑姑竟一夜白了头发。苗姑姑活下来,但仿佛变了一个人,她走出村子,接来了第一单贩卖孩子的生意。富有起来的苗姑姑,直接监管了矮胖子叔叔的生活,间接监管了我。
我关于半步村的记忆,是从矮胖子叔叔“咝”地一声划亮火柴开始的。每天早上,他都会点燃了喇叭一样的手卷香烟,蹲在门槛上,像一只嚣张的大鸭梨,将早晨微弱的光线都挡在屋外,我在门口刷牙,透过他的肩膀望进去,屋内有一种神秘的黑。隔壁守寡多年的苗姑姑从门帘后面钻出来,在门口树底下洗脸,他们有时会聊几句,有时什么都不说。这个情景重复多年,我都分不清是记忆,还是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