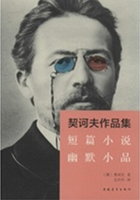来源:《湖南文学》2016年第12期
栏目:小说
在湘鄂边陲的丛林深处,在武陵山脉的皱褶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开凿出一条绵延十里的峡谷,峡谷两岸天然生长着白梅。寒冬时节,花开十里,幽幽梅香浸淫整条峡谷和谷底那条清澈的梅河。于是,这里便有了一个诗意词韵般的地名——“梅谷”。
从县城到梅谷全程一百七十公里。警车一路向西,山越来越深,路愈走愈烂。我坐在副驾驶座,左手撑住车,右手抓牢旁边的扣手,屁股像一只瘪气的篮球在座位上蹭来滚去,根本没法坐稳。我不时朝开车的侯君瞟一眼,只见他两手死死抓住方向盘,整个身子也在不停摇摆,两只眼睛瞪着前方,神情如临大敌,看样子并不比我更好受。
突然想起梅谷——成了梅谷人,我们应该谈梅。
“侯哥,去过梅谷吗?白梅长什么样子?”
侯君不好意思地笑笑:“我还真没去过呢,倒是计划过两次,可每次临行时总是因为所里有事耽搁,一直没成行。”
“我听说许多外地人都大老远专程去梅谷寻梅呢。”一个在梅谷工作的人,居然不去访梅,真是件遗憾的事情。我在心里有点替侯君感到惋惜。
“你以为访梅是件容易的事吗?”
我倒有点奇怪:“不就是上山看花嘛,那么难吗?”
侯君告诉我,白梅只生长在梅谷两岸的峭壁处,上去连路都没有,还要涉过那条梅河,不请向导你根本进不去,就算进去了也可能走不出来。再说,白梅只开在寒冬时节,花期并不长,稍一延宕就错过季节。许多人就是这么缩手缩脚、瞻前顾后给耽搁下的。
“不过,现在好了,有你搭伴,今冬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去梅谷看看。”侯君的话正中我下怀。我想,我离开县城来到梅谷,唯一幸运的事情恐怕就是有机缘赏梅了。
湘西北的初春昼短夜长,天黑得早,还只六点不到,夜色就像一张网罩下来。迎候我的余所长和小白在派出所院子内站成一幅剪影,他们身后的房子和远山朦胧的轮廓成为这幅剪影的背景。
余所长近花甲之年,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许多。他穿一身皱巴巴的警服,胸前的警号歪戴着,额头上几道抬头纹陷得很深,浊黄的眼珠下面垂着两个大黑眼袋,两只耳垂上残留着冻疮初愈的血痂,几根鼻毛探出略显红肿的鼻孔,下巴上的胡须白里间黑,短而粗硬,想象中每根须子都是针,足以刺穿一张纸。如果脱去警服,以他这副粗糙形象,和一个山民别无二致。“这是所里的微机员小白,白梅。”侯君介绍完余所长,把立在旁边笑盈盈的女孩指给我。白梅自我补充说:“我还兼着炊事员的工作。”
我发现,说话时,白梅的目光朝侯君撞去。这一撞,把侯君的头撞低下去。
这个夜晚,我第一次躺在远离都市的梅谷,躺在派出所板实的木床上,不时翻动出吱嘎的声响,渲染着我无眠的意绪。这时候,肖嫣打来电话:“感觉怎样?”她声音发苶,有着圆润而勾魂的穿透力,尤其在这样清冷孤寂的夜晚。
我说:“谈不上什么感觉,所长是个土包子,但看上去人还好。”
听说所里有个叫白梅的女孩,肖嫣说:“她长得比我好看吧?”
我明白她话里的潜台词,说:“一个山里女孩,跟你比就是凤凰和鸡。”
肖嫣说:“那可不一定。俗话说‘高山出鹞鹰’,山清水秀养美女。你不是一心向往梅谷,向往开在梅谷深处的梅花吗?”
“放心吧,梅谷的白梅只是昙花一现,你才是我心中那朵常开不败的梅花。”肖嫣没话了,电话那端的笑声臭美得要死。要说斗嘴,她并不是我的对手。要不,我的中文系四年就白混了。
后窗隐约传来不明声响。我迷瞪着眼朝窗外望,天刚麻麻亮。挨了一会再起床,扒开窗帘一瞧,派出所后院菜地里,余所长正打着赤膊挖地。他叉开双腿,上半截身子躬下去,腰杆弯成九十度,头上正袅袅冒着热气,身后是刨松的黑土,黑土两边旺绿着白菜和葱蒜。薄白的晨光里,但见锄头起落,板结的泥块被翻出来,然后给锄头敲开,蒙住余所长的赤脚。接我报到的路上,侯君告诉过我,所里食堂的蔬菜都是余所长一个人种出来的,他从不让别人插手。
侯君告诉我,梅谷大着哩,差不多等同太平洋上某岛国的国土面积。这里地广人稀,三分之一的青壮劳力外出打工,派出所想管够不着;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和老人根本不用管;剩下三分之一的人住在老山界上,那里连公路都不通,他们到派出所往返一趟没两天不行。于是,余所长每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趁天气暖和时带民警上山“巡视”一圈,时间两个月或更长。梅谷藏在大山里,避开世间纷扰,人心向善,社会和谐,十多年没发像样的案子,就连矛盾纠纷也稀少。所以,警察在梅谷的存在似乎显得多余。我心里想,怪不得余所长在梅谷扎下根,他是吃惯了这里的安稳饭。在局里,我父亲凡事都由着余所长,除了他是根“老油条”外,也许梅谷派出所在他心里的地位根本无足轻重。
侯君还特意告诉我:“这里不比县城,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不管用,余所长那一套才行。我们都要跟他学。”
我不明白,余所长的那一套究竟是哪一套。
终于等来第一起报警,我也彻头彻尾地领教了余所长的“那一套”。
野猪岭的村主任说,村里有对古稀老人,房子快垮塌了。老人担心砸死屋内,要求两个儿子轮流赡养,老大家同意,可老二媳妇坚决不答应。村主任并没说要派出所介入处理,他或许只是向余所长咨询一下,请余所长帮忙拿拿主意。可余所长一听就火冒三丈:“翻天啦?自古养儿防老,哪有嫌老的道理!你马上把人召拢,我要会会这个二媳妇。”撂下电话,他对我和侯君说:“来事了,我们出警。”
遇事这么不冷静,我心里对余所长有想法。这种家长里短的琐事派出所一定要管吗?这种扯不清的“麻纱”缠到头上,警察未必管得过来;再说,村里又不是没治调组织!侯君对我的嘀咕不予理会,只说:“在这里,余所长的话就是圣旨,到时候你只管听和记,千万别多嘴。”
这算忠告吗?我不信邪,回了句“那可不一定。”
野猪岭村距离派出所三十多公里,一条简易公路只通到半山腰,到村部还得弃车爬坡半小时。天气晴好,春日融融,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植物气息。阳光照射下,山间的雾岚散开,不知名的花树呈现出来,粉白的、火红的、嫩黄的、浅紫的,五颜六色,美不胜收;白色的鹭鸟停歇在高高的树冠上,憋了一冬的熏风在山林里慌慌张张地窜动,搅得整个林子一片响声。我虽说对这样的出警不感兴趣,但窝在派出所大半月,我也憋得快要受不住了。所以,能感受野外明媚的春光,就只当是一次难得的春游,我心里稍许释然。余所长不愧是爬山的老手,我和侯君跟在后面浑身淌汗、大口喘气,他却没事一样。半坡里,我提议歇歇再走,余所长没回头,只把话从脚跟往下丢:“你们歇吧,我先走。”他的话明摆着欺负人,我们哪敢歇脚!只能中间隔着一大段距离,吊着他走。
在村部门口,我发现余所长在和迎候的治调主任握手时交给他一样什么东西,然后还嘀咕了些什么。
人到齐,客套免去,先听情况。大儿子和大媳妇倒没说什么,二媳妇还是拒绝接受轮流赡养老人的方案。余所长说:“不接受也可以,你二媳妇就写份申请贴在村部。我们出面把两位老人送到养老院去。”
村主任不明就里,说:“这恐怕不行。”他说乡民政办有规定,进养老院必须是五保户,有后人的不符合条件;二来,老人的生活费和护理费村里要负担一部分,这个钱没着落。
余所长说:“现在,儿媳公开拒绝养老,老人就成了有后人的孤老,民政那边由我去做工作。至于钱嘛,我看这样,把老人的责任田地和山林拿出来,一次性卖掉经营权就足够了,不会给村里增添负担。”
对余所长提出的方案,二媳妇最先跳出来反对。老人的责任田和山林早就分到了两个儿子名下,现在要拿走,不亚于要她的命。
“那你就写份申请吧。”余所长继续给二媳妇下套。
弃老的申请二媳妇不敢写,她就是再“苕”,也能掂量出这件事情的轻重,申请一贴出去,贻笑大方事小,光唾沫星子就足以将她淹死。
老大问老二:“轮流养老你家里不同意,送养老院也反对,我建议干脆把两老撵出去讨米算了。父母白养了我们兄弟俩,我们把脸装裤裆里去。”
二媳妇有主意。她说:“我并没说不养老,两家各分一个。我们家龙儿跟他爷爷最亲,我就认领爷爷。”
二媳妇好狠心。老人都黄土埋起脖颈了,她还要将他们生生拆开。爷爷身子骨硬朗,还干得动田地里的农活,认下他等于白捡半个劳力,而奶奶一年四季病病歪歪的,只把药罐当饭碗,闲饭可能要吃到闭眼睛那一天。二媳妇早在心里把算盘扒拉清楚了才说的话。
老大两口子一言不发。他们听懂了弟媳妇没有说出来的话——老大家是个女儿,男对男,女对女,他们没有叫板的资本,只能认领婆婆。
余所长看看村干部,村干部都装哑巴当好好先生。二媳妇看样子泼得很,村干部肯定领教过厉害,谁都不想得罪她。余所长不会让二媳妇的阴谋得逞,而且他似乎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说:“凡事得讲个公平,既然派出所来处理,就得立个规矩。”我怎么都没想到,他定下的所谓“规矩”居然是抓阄。他的理由堂而皇之——“领谁不领谁要讲公平,不能哪家说了算。”他转向村干部,“老人不是物品,政府也不能搞强行摊派,是不是?”
村干部们都说是是是。
余所长将治调主任叫到身边监督,三把两把做好纸团。他把纸团攥在手心里,宣布了抓阄规则:只能由两妯娌抓,而且一次性生效!他问:“谁先来?”
大媳妇表态说:“我没什么,反正是养老,公公和婆婆谁跟我都行,随小婶子的。”
二媳妇有点迫不及待。她说:“嫂子既然承让,我就不客气了。”
余所长没急着松手。就在二媳妇把手伸向余所长展开的巴掌,即将要拈纸团的时候,他把散开的手握回来,告诉二媳妇:“抓阄全靠手气。嫂子讲境界让你先抓,她就等于放弃了机会。我要把丑话说到前头,结果出来不得反悔!”
二媳妇小心翼翼,像要抓一颗炸弹。
二媳妇抓出的是婆婆。她把纸团展开,脸上立马刷白,颓丧得像涂了一层霜。余所长把手里剩下的纸团递给治调主任,看看愣怔发呆的二媳妇,吩咐说:“写协议吧。”
治调主任把纸团朝老大扬了扬,问:“父亲归你,要不要看看?”老大犹豫片刻,两口子都摇头。治调主任把纸团收进衣兜。我发现他的表情不大自然,马上悟出余所长玩的鬼把戏——治调主任衣兜内的那个纸团上写的一定也是“婆婆”!想到这一点,我替余所长感到有些汗颜,二媳妇就算不尽孝道,但作为一名警察,我觉得余所长不应该拿自己的小聪明忽悠人家。这样处理问题有失公允!
二媳妇果然不是吃素的。她似乎看出什么猫腻,对摆开纸笔正要写赡养协议的治调主任说:“慢点!你是不是应该把老大的阄也打开让大家看看?”
治调主任停下纸笔,伸手从衣袋内捏出一个纸团。他直接丢给二媳妇:“你的意见很对,老大两口子不想看,但应该给你瞅一眼。”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发现治调主任拿出的纸团比先前收进去的纸团略大了一点。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精明过人的二媳妇还是慢了半拍。二媳妇不是善茬,但在老谋深算的余所长面前,她还嫩了点!
这就是所谓的调解?这就是余所长说一不二的“那一套”?他们在写协议,我感觉无地自容,一分钟也不想在屋内呆下去。我走出村部来到旁边一块地头,见几个农人正在烧火土粪,就随便聊起来。
“翻过野猪岭,再过去是哪儿呢?”我想象中的答案应该是湖北。
一位大叔说:“翻过山去就是十里梅谷。”
我顿时来了兴致:“你们去过梅谷吗?白梅长什么样子?”
大叔用遗憾的目光看看我,直摇脑袋。
我不禁替他们感到惋惜。上苍把一条梅谷安放在身边,仅仅一岭之隔,他们却从未去过,遗憾啊!山里人质朴。大叔读懂了我脸上的错愕,说:“梅谷没有路,又险,不就是开在悬崖上的野花吗?不值得费功夫去看。”
大婶反应快:“你要看梅花,现在还不是季节,等入冬下雪了再去吧。”
我感到无端的茫然和失落。
回去的路上,余所长给治调主任打电话,意思是让他把嘴巴闭紧,守住抓阄的秘密。
等他挂了电话,我直言不讳地说:“余所长,你这样搞调解违反规定。”
“是吗?”余所长正在得意中,对我的批评毫不介意。他说:“云飞啊,你是说不符合书本上那一套吧?告诉你,那是读书人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山里人有山里人的口味,他们不吃书,就吃阄。”
从余所长的语气里,我知道再和他理论下去毫无意义!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