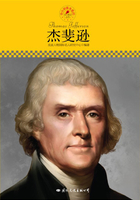第2年夏,上官芳生下儿子王丙东。
第3年秋,上官芳生下儿子王丙南。
第7年冬,王安绪去世。临死前的王安绪两只眼睛凹得像两只干缩的倭瓜,裹在被子里,看不见鼻梁上那几粒儿雀斑,他透明的身体躺在上官芳的臂弯里,一动不动西天而去。
两个寡妇支撑起两个男孩的教育和40亩出租的农田。
租种沁河河滩30亩沙滩地的是郭壁村的李栓,王姓家族走到现在家存的积攒因不断的减增人口已经空空,而且债台高筑。高秀英和上官芳商量想卖了河滩地。这时候有人就站出来想要买下这30亩地。买地的人是租地人李栓。
下里村的人不相信李栓能买得起地,可李栓就是买了。
李栓放出话来说:“河滩地是我日弄出来的,就像养活了一个人一样和它有了感情,现在比不得从前,要卖地就得先卖给我,我种王家的地是迟早的。”
这叫什么话?婆媳俩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有人从中间做梗,想不起是什么人,就哀叹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外人就要下看。上官芳说:“这么些年了,大伯和咱家老不上门,现在有人要找咱的茬儿,是不是也应该和他商量商量了?”
高秀英因丧夫丧子的打击,身体极度衰弱,用手指了指胸口又指了指嘴,摆了摆手。
上官芳说:“咋说也是大伯,我去找一找看看。”
上官芳抱了小儿子牵了大儿子走下大门外的台阶,走近三槐里的大门。上官芳要怀中的小儿子拿起门环拍拍门,就听得有下人叫了声:“谁呀?”
“是我,青乡里安绪家里的,大伯在吗?我给他老人家问安来了,烦你通报一声。”
有一会儿功夫门开了。上官芳随了下人走进了正屋。她看到王书农坐在太师椅上,头戴毛织贡瓜皮帽,身穿青哔叽夹袍,手里取了水烟袋咕噜咕噜抽着。
上官芳说:“大伯在上,收侄子媳妇给您老人家头。”一边招呼两个孩子也叩头。
王书农没有想让他们母子起来的意思,放下水烟袋说:“我怎么就没有见过安绪娶过媳妇?”这时候,有一个女子披了头发从门外走进来,看着地上跪着的人咧了嘴笑,笑声由小而大,上官芳身边两个孩子就哭了起来。
上官芳呵斥孩子不要哭,然后说:“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六进的门。”
王书农说:“是光绪年间的事啊,光绪年已是老黄历了,我不记得了。你还知道我是你大伯!”
上官芳说:“知道。只是因为家里一直有事没有过来拜见,又因为过去的旧事,侄子媳妇现在提起,肯定还伤大伯的心,青乡里的日子不好过,活到现在我们守业都难了。不来拜见是小辈的错,还希望大人不记小辈错。”
王书农把水烟袋端在左手上,用烟嘴指了指依旧在一旁傻笑的春香说:“她吓哭了你的两个儿子,你知道她是谁?”
上官芳说:“想是妹妹春香了?”
王书农说:“还算好记性,有些事情因你而起,想必你也该记得了。你来是和我说李栓买地的事吧?”
上官芳说:“大伯真是明白人,真要有劳大伯了。李栓是郭壁人,一直租种河滩那块沙地,现在一下提出想买那块地,不是不卖,家里已经借了不少外债,债台高筑,讨债人年底来讨拿什么去还?地是要卖,只是不想卖给李栓。”
王书农把盘在太师椅上的腿伸展了,用手捋了捋头发看着春香说:“噢,不想卖给李栓,那么想卖给谁?”
上官芳说:“说心里话,谁也不想卖,还望大伯看在祖母的面上能给周转一下,大恩永记,容我儿明事理,懂情怀,当报不忘。”
王书农皱了一下眉头看着春香说:“你不觉得太久了吗?可惜我这女儿连个废话都不会说。”马上又调转了话题说:“很好,能想到大伯就好。你看,不管你是不是安绪的媳妇,不管往日有过什么纠葛,难中能想到你的大伯就好。有8年了吧?8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们,这日子越往前走就越觉得重,就越觉得痛,能想到大伯就好,就好!河滩地那就不卖了,不过——”
上官芳听到王书农似有什么迟疑的事,抬起头来看着说:“大伯还有什么不好说的事?自家人就说出来,侄子媳妇也不是不懂大理,以往的事情我也隐隐知道一些,要是我的公公和丈夫做错了什么,8年了也请求大伯看开些,咋说王家圪洞也就剩咱这一脉血亲了。”
王书农换转了手上端的水烟袋,说:“是啊,只怕这一脉也要断了。哦,不说这些了,刚才说什么来着?是李栓买地的事吧,只是怕引起郭壁李姓家族的猜忌闹出笑话来。既然决定不卖了那就这样吧,你把租种地的契书取过来,和李栓说,地要租种给大伯,现在王家还有长辈在,要他来和我商量,租种地的年租金是多少还是多少,你现在就回去取来契书,我也好给你打点一下。你看如何?”
上官芳弯腰抱着小儿子磕了一个头说:“有大伯作主,侄子媳妇还怕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大伯。”想了一下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说了声:“那侄子媳妇告辞了。”上官芳起身站起来,腿有些麻,打了个踉跄,春香就大笑着说:“好哇,好哇。”
上官芳看着春香想:她要是不这样儿傻,真是一个俊秀的人儿。牵了儿子走出三槐里,从心里想着大伯的好处:没想到借钱就借了,紧要的时候还是自己的亲人帮忙。说大伯记仇那都是从前了,大伯还是咱大伯。
回家和婆婆说了自己去三槐里的收获,高秀英说:“也许你那大伯真的回心了?!”
上官芳取了租地契书又一次走进了三槐里,看到大门洞站着一个人,是春香。春香的脑袋里好像有笑不完的事,胸前挂着一粒饭渣子,上官芳掏出手帕想帮她弄下来,春香一把抓住了那手帕不放,上官芳笑了笑就丢开手帕走进了堂屋。发现太师椅上多了一个人,是本村的地保张五爷。上官芳跪到地上给大伯和张五爷请了安,因为有外人在怕不好说话等大伯叫起。听得王书农说:“东西拿来了?拿来就递上来吧,张五爷也好做个证。”上官芳把东西递上去说:“大伯请过目,一切由大伯来做主。”
王书农起身从竖柜里取出一小包银钱递给上官芳:“这是你河滩地的,你取了去,有张五爷在,我王书农怎么能不管不顾呢!起身去吧,有什么事过不去就来找大伯。”
上官芳告辞出来,手里的银钱变做了希望和温暖,心里一热就有泪掉下来。
纳闷儿的是,李栓没有再来找上官芳说买地,李栓不来上官芳心里反倒不怎么样踏实了。不踏实归不踏实,日子推拥着挤得满满的,心里就把这事搁在了一边。因为日子过得紧使唤人都已经辞去,空空的一个大院里什么也听不到,就听到孩子们的哭声。两个孩子中间只隔了一岁,你争我吵,你欺我霸,整日里清鼻涕和着眼泪不断头地流,不时听得上官芳的呵斥声。忽一日听得有唢呐和笙音传来,像是大伯家办喜事了?想不起是谁,大伯家的女儿春香傻在家,是谁呢?怎么也不通告青乡里?以前因为结仇互不上门,现在不是已经说和了吗,怎么也不说一声?上官芳抱了孩子迈动小脚走下了石台阶。迎面碰上了村中一个。那人说:“李栓招了你大伯家的老姑娘春香,陪嫁是李栓要买的三十亩河滩地。”
上官芳觉得距离喉咙五寸的地方有些闷,咬着自己的下嘴唇竭力装出想笑的样子,没有笑出来扭回头上了石台阶进了青乡里。王丙南哼哼叽叽用小手撩她的大襟衣服,想吃奶了。就听得一巴掌下去,王丙南脸儿显出了五个红印子,半天没有哭出来,又一巴掌下去哭出了声,红印子变成了血印子。高秀英急忙走出屋叫道:“什么事憋了这大的气打孩子?”要过王丙南搂在怀里哄。
上官芳说:“王书农招李栓上门,陪嫁是咱河滩地。”
高秀英楞怔了一下,一把拉住上官芳的小袖:“你说什么啊?那地不是租出去的,怎么成了陪嫁?”
上官芳说:“我也不晓得,要去问问!”
三槐里的鞭炮响得震耳,周围看热闹的人远远站开了,上官芳迎着炸下来的鞭声走进大门。王书农正站在院子里迎送来人,上官芳走上去正视着他说:“大伯家办喜事怎么也不通告一声?我想问问,李栓陪嫁的那三十亩地是咋回事。”
王书农把小辫子从前胸摔过后背,立马表现出感到意外:“那三十亩地不是你要我做主卖给李栓的?张五爷在场,红嘴白牙定了的事,你也拿了银子的,怎么现在倒咬一口了!”这时候主持婚礼的张五爷笑着走过来说:“是啊,媳妇,我是亲眼见的。大喜的日子里,舌头没长脊梁你可不能胡说。”
上官芳感觉自己掉到了悬崖边上,手里抓着一根绳子也脱落了,气流冲击着她的胸口,心没着没落的,一下就嚎啕大哭了起来:“你可是我王家的大伯呀?一年的租金买了三十亩地?你怎么配做王家的大伯?你要我和我的婆婆说什么?”
王书农眉头一皱说:“我这是办喜事,不是要你来叫丧,你扯了嘴嚎什么?你和你的婆婆说什么,这事也要我来管?卖地的时候你找我,要我来帮助你卖,现在地卖了反倒落了这么个话!”
上官芳说:“事情哪是你说的这个样子?你说的这个样子,要是别人还说得过去,怎么你是王家的大伯也敢做这样的绝事?”
王书农拿了旱烟袋锅子在手掌心磕了一下,抬起头笑了起来:“做绝事?下里村人谁见过我做绝事?谁不知道我是看着人的眼色长大的。人还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就想着卖地?那是败家子!王家出了不孝子孙啦,大伙来看看,这就是我王家的妖精,克死我母张金花,克死我弟王书田,克死我侄子王安绪,克傻我闺女王春香,现在又想要来搅我傻闺女的婚事,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守住这份家业不败,就不能让贱人得逞。你怎么就连一个被害得半傻的人也放不过!妖精!”王书农背转手弯下腰脸冲着上官芳说。
看热闹的人都拥过来看,上官芳张着个嘴说不出话来。眼泪掉到前胸落到膝盖滑到地上,人们指指点点说着什么。
上官芳掩面跌跌撞撞出了三槐里,爬着上了石台阶看到婆婆高秀英抱着王丙南站在门墩旁,上官芳抱住高秀英的双腿叫了一声:“娘,我对不住你!”一口气没上来,瘫在了大门口。
有腿快嘴快的,早把这边的情形告给了婆婆高秀英。上官芳像春风刮过草地,悠悠缓过来一小口气,看到婆婆高秀英吐了一地血,无常的命运毫无表情的就这样来了。她急忙上前扶稳婆婆,高秀英指了指天,指了指地,指了指她,从嘴里蹦出两个字来:“祸水!”
上官芳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呼吸减得很慢很慢,然后,长长吐了口气,眼泪在眼眶里汪着到底没有掉下来。
“娘啊,你也这样来骂我了?我是为了王家,我养了儿在王家,你也是女人,你要是这样以为,我还说什么?说给谁来听?谁来信?”
高秀英捂着自己的胸口说:“要我怎么信你?你来了王家,王家出了多少事?自己干不了事还想逞能,心强命不强,倒好,我王家咋就娶了你这么个祸水?你去给我把地要回来啊!”地收不回来了。
上官芳被不断降临的灾难攫住了。这一年高秀英带着满腹的仇恨去了,上官芳借了高利贷葬了她,为了还贷,她变卖了娘家的陪嫁。上官芳买了猪、牛,她不相信日子是一潭死水,她要它活水长流。
母子们守着剩余的十亩地过活。上官芳的心里支撑着一重希望:两个后生的成人。此时,他们正在院子里打架,她喊了一声:“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娘的苦啊?”上官芳哭了起来,为自己哭,也是一个母亲为抚养孩子哭,她的哭暗含着她的仇恨。以前没有做母亲的时候她做上官家的女儿,她渴望一种有别于上官家的生活,从来没有想到要发生过坏事情,现在,当孩子们一一从自己的身体中出来了,自己也经受了地狱般的苦。娘家因为遭了水患年景一年不如一年,娘家不给自己添乱,自己怎么能去求娘家人?哥哥不说什么,嫂子那双眼睛她就不愿意看。指望不上娘家,指望谁?自己在哭声中只能指望另一个祝福:长大,长大,长大,长大的孩子们可以为自己做主,长大的孩子是未来的指望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分界。其实,那根本就不是祝福更像是一个诅咒、谶语!因为,灾难阻止了她想象中的未来。
真的有指望了。这一年王丙东13岁,王丙南12岁,上官芳添置的那头牛也从牛犊长成牛了,在租种地的同时她决定也出租牛。
可事情说来就来了。
李栓敲开了青乡里的门。李栓说:“听说你家添了牛,春天了借牛耕耕地。”
上官芳说:“不借!”说完就恶气顿生,用力把门关上。
李栓撂下一句话扭头走了。
李栓撂下的话是:“王家圪洞的牛,我日,怎么也不长个记性。”
隔了几天下里村东,张姓人张亮来借牛耙地。牵了牛路过三槐里,牛脖子上的铃铛“叮当,叮当”响得脆耳。大门“吱呀”一声开了,王书农走了出来,嘴里咬了旱烟袋锅子,翘起腿在鞋帮上磕了一下说:“借王家的牛耙地?”
张亮说:“耙地。”
王书农望着高天上的流云说:“自己要是有牛了,是不是就不用借别人的了?”
张亮说:“那是。”
王书农低下头往烟袋锅子里按了一揪烟丝说:“那就牵了不用往回送了。”
张亮吓了一跳,拽了缰绳扭回了头看,看到王家圪洞还是王家圪洞,王书农也还是王书农,石头是石头,门头是门头,是自己听错了?
王书农拿烟袋锅子指着张亮说:“是真的。害怕什么?我们王家的牛,王家的长辈说话了你害怕什么?”
张亮说:“要我买,我是买不起,要送我一头牛那不是天上掉饼子了,哪有这等好事?老叔真会开玩笑。”
王书农说:“我是开玩笑了吗?没有,这样大的岁数和你开玩笑?笑话!”
张亮狠劲掐了自己的大腿一下,不像是梦。
王书农说:“进来说话吧!”
张亮牵了牛走进了三槐里,出来时上官芳的牛就不是上官芳的了。它一下就变成张亮的了。王书农和张亮说:“你只要想要这头牛,这头牛就是你的了,参与买卖的事要有证人,我就是你的证人,我是看见你日子过得苦,古话说,马不吃夜草不肥。你想想看,我也不想讨你什么便宜,就想争口气儿。她搞傻了我女儿,我搞她一头牛,说到桌面上吃亏的还是我。“张亮说:“你直接搞她的牛就是了,怎么要我来讨这个便宜?我没有恩给过你呀,我收受不起。”
王书农说:“我小时候被王家打的时候,你爹给过我一个糠团子,人不能知恩不报吧,你牵了她的牛,你获利我顺气有什么不好!”
张亮回头再看院子里槐树上拴的牛,觉得那就是我张亮的牛嘛!
上官芳不见张亮往回送牛就差了丙东去问。儿子回来告诉:“张亮说了,是你忘了,还是他忘了,牛不是已经卖给他了。”
上官芳说:“张亮说的?”
王丙东说:“是啊,是张亮说的。”
上官芳说:“你是不是没有操心听,听得说走嘴了?”
王丙东说:“不信,那你去问嘛!”
外面下着小雨,上官芳戴了顶草帽出了青乡里往张亮家走。沁河水有些看涨,泥泞的村路有些滑,沁河两岸有人在等上游发大水,水也许能冲下来一些有用的东西,有小孩子举了石头等着砸洪头。上官芳顾不上看这些,她的胸腔里也涨着一个洪头。脚高脚低地走进了张亮家的茅草屋。一进门就看到了她的牛,牛和人住在一起,张亮的穷酸是她始料不到的。她说:“张亮,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因何要赖我?我一个寡妇人家拉扯着两个孩子你怎么忍心赖我?就算你家里穷见不得眼前利你倒说给我听,我白借你牛用也不该赖我?常话说富人容易残忍,穷人常常怜爱,你怎么也学了富人那一套套?”
张亮的脸红一阵子,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张亮老婆说话了:“你王家圪洞是大户,不在乎这一头牛是不是?牵回来的牛是送不回去了,不是我们不想送,是人家不让送。”
上官芳抬头看着自己的牛说:“谁不让送了?借是你张亮去敲了青乡里的门借的,你张亮借了牛该还回青乡里是吧?借了人的不还人,想赖,赖一头牛,你张亮就富了?”
张亮瞪了他老婆一眼,想这事不大好解释,不能直说,可也不好把弯子绕得太大,这么的说吧:“我是从青乡里牵了牛,我还走了王家圪洞,王家圪洞我还路过了三槐里。我一路过三槐里,我说你卖给我了就卖给我了。”
上官芳说:“你路过王家圪洞怎么啦?路过三槐里怎么啦?你不路过能牵了牛走到地里,走到你家?”
张亮说:“我是不该路过,我一路过不是我想让牛是我的,是有人想让牛是我的,我不想让牛是我的也不行,因为我就想有一头牛。”
上官芳“哼”了一声说:“知道了。张亮,一头牛富不起来,人要是丢了良心就志短了。牛我不要了,就算我王家上辈欠了你,就算我王家这辈子不该养这个畜生!别忘了,我王家是不想闹事的,真把事情闹大了,我娘家陪过来的东西你该是听说过的。”
上官芳说完抓起草帽,外面的雨落得很大,打在草帽顶上发出乱响儿,她抓住草帽下的布条,提了心跑,一路小跑回了王家圪洞。路过三槐里,她站在门口狠狠跺了一脚,泥水溅到了她的脸上。她拣起一块石头想对准王书农的门扔过去,她想理论,终究还是压下了火,脑子里飞出了一段不大连贯的想法:儿子还小,不能让他下了毒手,忍字心上一把刀,能忍住就能化解一切。为等待活着,活出血也要等待!我倒要看看一头牛能把人养肥到哪?就当是沁河发大水冲走了。
隔了一天张亮把牛送进了三槐里,张亮说:“这牛不能要。人家是有陪嫁的,娘家的毛瑟枪那可不是耍的。老叔,咱命中无牛,牵了睡不稳当。”
王书农说:“一个人要想成大事就得做绝事,也就是一头牛,怎么就不敢要,那毛瑟枪又怎么啦?她一个女人敢把你撂过去?想你也成不了大气候。这样吧,你不要我也不会亏待你,你扛了那半袋麦子走吧,也算你帮我出了恶气的报酬。”
张亮扛了麦子出来,脚有些打漂,一打漂就上了石台阶走到了青乡里。他把麦子放到石门墩上,喘了口气想叫门,抬起了手又放下了,想了什么,脱下布衫把两个袖口挽住,打开布袋掬出些麦子放进袖中,挽好布袋口绳,双手捏了肘窝处搭在双肩上往回走,走了几步觉得自己真是背了个祸害,再回头看门墩上的布袋还在,有些不舍,放下布衫搂在怀里含了两颗泪珠走下石台阶,一路吊了心回了自己的茅草屋。
上官芳到院外挑水时看到了门墩上的麦子,布袋口上写了一个“王”字,是王家的布袋,那么是谁送来的呢?是王书农?她厌恶自己怎么能想到他。她想也许是祖上有人借过,现在连布袋一起还回来了,扭身叫了王丙东要他拿回去。
王丙东说:“娘,是谁送的麦子?”
上官芳说:“不管是谁送的,往后要是有人提起来,记着欠了人家一份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