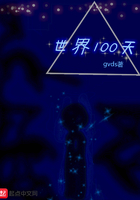我们是战友,有啥说啥。
当年你们十一支队(基建工程兵的一个师)在青海修青藏公路,我们十二支队在新疆修天山公路;你们修了10年,我们也修了10年;你们牺牲了108个,我们牺牲了168个。咱们都是从基建工程兵出来的,都在雪山上抡过铁锤,背过石头,所以见到你感觉特别亲。
我们实话实说,不整那没用的。但是有些话、有些事,你可别写到书里去,别让人家笑话咱老兵没水平。来,喝,听我给你慢慢唠。
我这一辈子呀,做过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吃了四个战友最后的一个救命馒头。当然,我也做对过几件事:一是当了兵,二是娶了个好老婆,三是退伍后又重返天山为班长和牺牲的战友守墓。
我们村里的许多媳妇都是骗来的
我家在辽宁省辽中县老达房孟家岗。我们弟兄三个,我是老二。老大是残废,23岁那年,给生产队赶马车,让马给踢了,双目失明,现在还没有成家呢。老三也是个农民,成家了,有一儿一女,听说日子过得还可以。
你说我父母?我父母已经不在了。我父亲是2003年去世的,我没回去,太远了,没有那么多路费。再说接到家信时,人都下葬一个多月了,回去也不赶趟。我母亲是去年去世的,我也没有回去。当时烈士陵园的事挺多,离不开,我想她老人家能原谅我。
不瞒你说,我来天山24年了,没有回过东北老家一次。为什么?我也说不清,阴差阳错的,就是没有回去。现在父母不在了,以后更不可能回去了。我想一直陪着我的老班长,陪着这168个战友,死后就跟他们埋在一起。你看天山这地方多美呀,多干净呀,死后能跟这么多战友埋在一起,也是我的福分。
我父亲排行老二,是个农民。我大伯也是个农民,担任过大队书记。老三当兵去了朝鲜,牺牲在了朝鲜战场。老四当了工人。我父亲最没本事,大字不识一个,人老实得有点过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给队长写大字报,落款都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陈彦令。我父亲不认识,还乐呵呵地跟在人家后面看热闹,结果让队长臭骂了一顿。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公社、县里领导写信告生产队长,落款也写我父亲的名字。你说这老实人倒霉不倒霉。
那时候穷啊!我们家过春节买不起鞭炮,我父亲是赶大车的,就用马鞭子甩两下,让我们听个响,算是过年放了炮。我的小名叫“赶趟子”,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叫吗?因为我出生的第二天,正好赶上生产队分粮。小时候看人家戴手表,我特别羡慕。当时“戴手表、穿皮鞋、镶金牙、别钢笔”,最牛气。不管有没有文化,衣兜里也要别上一支钢笔,有的别两支三支。再多就不行了,别上一排,那是修钢笔的。有的没有钢笔,捡了人家扔掉的笔帽别在衣兜上,冒充有文化。
我哥哥12岁就辍学了,回家放猪。我父亲吃了没文化的亏,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希望我和弟弟能继续上学。那时我就想,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买一支真正的钢笔别在衣兜上,那才叫真有文化。可是好好学也没用,那时提倡的是交白卷。我们辽宁的张铁生就交了白卷,还说“条条铁路通北京,老师何必硬强求”。当时没人好好上学,天天写大字报,学生给老师写,老师给校长写,贴得满墙都是。
我们村的知青说:老达房这个地方,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光棍能把人绊倒。女娃都嫁出去了,男娃找不到对象。找不上对象咋办?骗呗。咋骗?跑到山东去骗。让村里最年轻长得最帅的小伙子去山东相亲,说我们那里地多人稀,哪个姑娘要是肯嫁过去,连她的亲娘老子弟弟妹妹都可以带过去。这话很管用,又看小伙子长得帅,姑娘就上了当。
但是新婚之夜,前去相亲的那小伙子就消失了,换成了另外一个人。等新娘子发现上了当,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只好认了。
最要命的是,新婚三天后,新房里的摆设都让村里人抬走了。为啥?因为当时为了糊弄娘家人,全村人都把自己家里最好的摆设集中在了新郎家。媳妇已经到手,当然要物归原主了。
我当兵就是为了能吃上馒头
但是,我母亲不是父亲花钱骗来的,是她自己主动来到我们孟家岗的。来的时候,母亲怀里还抱着一岁多的大姐。我父亲三十多岁还没结婚,就娶了我母亲。母亲以前的丈夫是谁?为啥来到我们孟家岗?我一直没弄明白。母亲不说,父亲也不说,这事就成了一个谜。现在父母都走了,这个谜永远也解不开了。
母亲生下我后大出血,几乎死掉。我一声没哭,也不睁眼,一动不动。父亲以为是个死胎,就拿破布一卷,用草绳一捆,扔到了山上的野沙岗。父亲走出老远,听到我的哭声,又把我抱了回来。我确实也不争气,小时候多病多灾,长到11岁才会说话。村里的土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舌头大。
那时我们那里以吃高粱米、玉米、大豆为主,想吃大米白面得到外地去换。过年的时候村里才发几斤面粉,让大家初一包顿饺子。一年到头,三十那天能吃顿猪肉炖粉条。粉条是自己用土豆或者红薯加工的。把红薯放在缸里,捣烂,加水,把浆打出来,淀出淀粉,然后加上白矾和成面,支一个大锅,下面烧苞米秆,上面“漏鱼”,就是粉条。生产队分的粮食,一年总有一两个月接不上顿。
记得有一次,锅里就剩下了两个苞米贴饼子。我和弟弟放学回来,揭开锅一看,谁都舍不得吃,又悄悄去了学校。父母和哥哥还要下地干活,饿着肚子可不行。我和弟弟坐在教室里上学,省力气,饿一顿也没啥。
可是我们经过苞米地时,实在饿得走不动了,就溜进去掰青苞米啃。青苞米不好消化,容易放屁,而且还特别臭,又不敢放,怕同学听见,就拿捏着,一点一点悄悄放。同学嗅到之后,问谁放的臭屁?我也左顾右盼,寻找放屁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去世那一年,在城里工作的堂姐夫来我们家,拿了一盒点心,用红纸包着。堂姐夫走后,母亲将点心挂在屋梁上。母亲不让我们吃,一是舍不得,二是想让人家看看,我们家来城里客人了,还带了这么好的点心,觉着很有面子。等家里没人的时候,我踩着凳子,用手指头将红纸抠开一点点,沾了点心上的油,用舌头舔了舔手指,算是解了馋。后来时间久了,那红纸上落了厚厚一层灰,母亲才取下来分给我们吃。那时点心已经有点变味了,但是吃起来还是很甜,很香。
你知道,我们东北农村都睡大炕。家境不好的一家人挤一个大炕。有人开玩笑说:老公公把儿媳妇的鞋都穿错了。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一个大炕上。我大姐长大了,还和我们挤在一个炕上。但是大姐穿衣服优先,她毕竟是女娃,不能让她穿露屁股的衣服。大姐穿过我们再穿。我16岁以前,一直都穿大姐的旧裤子。那时女式裤子前面不开叉,解手很麻烦,我就自己在前面开一个小洞。一条裤子你穿了我穿,穿破了也舍不得扔,补一补又穿。有时来不及补,就用书包挡着屁股后面的破洞往家走。哎呀,别提多别扭了。
当时谁都想穿一身绿,但是买不起绿布啊,咋办?母亲就把莲花叶子和生布放在锅里一起熬,捞出来就成了绿布。母亲用这样的绿布给我做了一身衣裳,穿在身上心里别提多美了。我喜欢绿军装。我做梦都想长大了去当兵,穿上真正的绿军装。还因为当兵能吃上馒头,而且管饱。这话是我姐夫告诉我的。
那时大姐已经出嫁,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姐夫是沈阳军区的,叫何长友。他第一次来我们家,看着他那一身绿军装真是眼馋。我说何哥,能不能把你的军装脱下来,让我过过瘾?他只把上衣脱下来让我穿了一会儿。哎呀,那领章,那帽徽,真是让人羡慕。姐夫说,你要是喜欢,等长到18岁也报名参军,部队不光能穿绿军装,还能吃上馒头和猪肉炖粉条。那时我就发誓,一定要去当兵。不为别的,就为了能穿上绿军装,能吃上馒头。
为了当兵,我给大队书记跪下了
其实,我最先想当的不是基建工程兵,而是云南的野战军。那是1978年3月,当时我已经体检合格了,有人告我的状,说我高中还没毕业,结果没去成,我心里很难过。那时政审很严,大家都想当兵,争破了头。
你不是告我高中没毕业吗?那好,我干脆不上学了,回家务农,就等着当兵。但是我不会铲地铲苞米,队长见我有点文化,就让我跟人去拉草,拉回来粉碎了喂牛喂马。生产队有一头瘸骡子,没人愿意赶,队长让我试着赶。
那年冬天,又开始征兵。这次是我们基建工程兵。当时不知道基建工程兵是干啥的,也不管那么多,只要能当兵就行。
我们大队五个体检合格,另外那四个都有来头,就我没有一点关系。这可咋整呀?上次没整成,这次再黄了,我当兵的梦不就破灭了吗?
我夜里长吁短叹,睡不着觉。母亲也替我难过,可是有啥办法呢?我们家没有一点关系,找谁帮忙呢?后来母亲想了个办法。大队书记姓王,我母亲也姓王,母亲就跟人家书记套近乎,提着半篮子鸡蛋,领着我去找书记。
母亲见了书记说,大兄弟,咱们都姓王,五百年前是一家,我求求你了,让你这个外甥去当兵吧。母亲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母亲一边流泪一边让我跪下,喊书记“舅舅”。我心里很难过,很不情愿,可是为了当兵,我还是扑通一下跪在书记脚下,喊了一声“舅舅”。那一刻,我的泪水也落了下来。
书记很高兴,答应研究研究。
书记说话还真算数,没过多久,我就穿上了崭新的军装。
生产队长对我父亲说,陈彦令,你儿子要当兵走了,放你一天假,你去赶大集。父亲就抱着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去赶集,准备卖了钱再买点肉和菜,请大队干部吃饭。可是父亲把老母鸡揣在怀里,在集市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没舍得卖,又抱了回来。母亲说那就把老母鸡杀了吧,给大队干部吃。这是规矩,人家请,我们不能不请,我们家再穷也不能少了人家这顿饭。
父亲就把母鸡宰掉了。我心疼啊。家里就指望这只老母鸡下蛋换钱,给母亲买药呢,鸡蛋送给了书记,现在连鸡也杀了,母亲以后靠啥买药?母亲说,儿子你放心走吧,妈以后吃黄连素,黄连素便宜。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到部队后好好干,将来混出个人样来,为父母争气。
第二天,民兵连长把我们带到公社,然后坐汽车直接去了辽中县城。晚上我们到了沈阳,啥也没看见,又被送上闷罐子兵车。
闷罐车上只有一个小窗户,车厢里光线很暗,接兵干部都穿着“四个兜”,也分不清谁大谁小,见了“四个兜”都叫首长。我第一次坐火车,心里很激动。想问“四个兜”我们去哪里,但始终没敢问。
天安门上的钉子不是金子做的
一下火车,我们才知道到了北京。那个激动啊,简直没法说。但是看了看周围,没有多少楼房,不像是心目中首都北京的样子。一打听,才知道是房山区李庄大队。我们将在那里度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生活。
我们住的是老乡的房子。我们班住的那家姓池,他家有个沼气池。那一带许多老乡都用沼气做饭。训练休息时,我经常帮老乡清理沼气池,干点家务活。老乡很喜欢我。他家有两个丫头。
老头子跟我开玩笑说,小伙子,你将来退伍了,就给我当上门女婿吧。
我听了心里很不乐意。我刚到部队,还准备好好干一番哩,将来穿个“四个兜”啥的,你却说我退伍的事,你知道我一定会退伍?
但是冷静一想,老头子说得也没错,再说,人家丫头长得也不差。
说实话,我既然出来了,就不想再回东北老家了。
三个月新训结束后,我们才真正走进北京城,驻扎在西城区安德路,任务是修地铁。我们连队的主要任务是扎钢筋、支模板,支好后往里面浇水泥,等水泥凝固了再把模板拆掉。你说啥?馒头?那当然了,连队馒头管饱,我们新兵特别能吃,干的又是重体力活,一顿能吃七八个。但是我们天天在地下施工,又是封闭式管理,很少看见外面的繁华世界。
一个休息日,连长对我们说,你们新兵刚到北京,可以出去转转,但必须三人一组,由老兵带队。还说,出去时要衣帽整齐,军姿端正,不要影响军人形象。这可是我们伟大的首都,你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把军装平铺在床上,用嘴往上面喷些水,用装有开水的茶缸熨平。然后穿上,高高兴兴地走出了营门。
一个老兵带着我们两个新兵逛王府井。我对逛街没兴趣,一心想去天安门。为啥?说了不怕你笑话,我们村里人都说天安门城楼大门上碗口大的钉子,全都是金子做的,有人还为此打过赌。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到底是不是金子做的,还要亲手摸一摸,将来探家的时候好给村里人吹牛。心里这么胡思乱想着,我就与另外两个战友走散了。找了半天没找到,我干脆自己一个人去天安门。
我一路问到了天安门。看到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我激动不已。我用手摸了摸大门上那碗口大的钉子盖,原来不是金子做的,而是铜铸的。
我在天安门转了很久,后来就转迷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问路人:西城区安德路怎么走?人家说安德路地界大了,你到底要到哪里?我说不上具体地址。我一路走一路问。我从地上捡到半根粉笔,担心自己越走越迷,就在走过的电线杆上画一道,如果找不到,大不了顺电线杆子再折回来,重新再找。后来还真找到了。但是天已经很黑了,连长急得在院子里跳,带我出去的那个老兵站在一边,吓得满头大汗……
天山的冰棍不花钱
我在北京修了半年地铁。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不久,我们才离开北京。不是去前线,而是去相反的方向。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以为是去越南前线。
当时传说是一部分人要调走,大家都很兴奋,都盼望着去前线。为啥?去前线可以立战功,立了战功可以入党、提干,穿上“四个兜”。能入党,能穿上“四个兜”,是每一个新兵的梦想。别看北京是首都,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但是前线才是我们真正向往的地方。北京再好,我还是一个兵,可是上前线我就有可能穿上“四个兜”。
那天晚上,天很黑,我已经睡着了,突然听到了紧急集合哨。
连长在外面喊:一号装备,把该带的都带上。
我们打好背包,黑压压站在操场上。
连长说,点到谁谁出列。
营门口停着6辆解放车,车厢用帆布蒙着。气氛神秘而紧张。被连长点了名的站到另一边。我心里很紧张,等着连长点我名字,可是就是听不见“陈俊贵”三个字。心里那个紧张啊!我一心想去前线。打仗我不怕,死了也痛快,不死就立功、提干。连长终于念到我了,我很激动,答“到”的时候,声音都有点哆嗦。
解放车把我们拉到丰台,我们在那里坐上了闷罐车。一人发了一袋江米条、两瓶罐头。窗户还不让打开,只留一道缝。铁门一直关着,只有停车解手的时候才打开。我们的火车白天不走,晚上才走。白天停靠的都是小站,也不让下车,大家就坐在车厢里等。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离越南边境还有多远?干部不让问,说保密,这是纪律。
现在总队的雷永文副总队长,当时就跟我坐一趟闷罐子车。但当时我们并不认识,前年他来乔尔玛看我,说起来以前的事,我才知道他当时也在。
闷罐子车把人坐得晕头转向,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最后到了一个地方,让大家打背包下车集合。我们下车后才知道,是乌鲁木齐。有人问干部,不是说到前线吗?怎么跑新疆来了?干部说,队列里不要说话,注意纪律。没人敢吭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那个小干部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九月的乌鲁木齐,已经有点冷了。我看见许多大篷军车朝我们开过来。我们按次序上车,刚坐稳,车就开动了。军用帆布把车厢蒙得严严实实的,看不见开往哪个方向。
颠簸了整整一天,到了一个兵站。睡了一晚上,第二天继续往前走。半路上来一个矮个子,姓郝,“四个兜”,人很精干,也很和气。后来才知道他是副团长。听说他后来当了将军,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北京。你认识他?那太好了,你见到他就说,他以前的兵陈俊贵向老首长问好。
我们坐在车里啥也看不见,心里那个急呀。我就用手悄悄抠帆布,抠开一个小洞,往外一看,乖乖,满世界都是冰雪。除了冰雪啥也没有。
天黑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叫那拉提的地方。这才知道已经到了天山,我们的团部就在那拉提。但是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叫那拉提的地方,后来会跟我有那么深的不解之缘。
第二天继续往天山深处走。一路往上,积雪越来越厚,路也越来越滑,大家吓得不敢吭声。走到半道,车队停下了,说前面塌方了。有人问塌方是咋回事?没人回答。干部们神情都很严肃。干部说路不通了,都下车,步行。我们就背着背包,徒步前进,走到天黑才到营地。刚从工地上下来的老兵们,一个个黑黢黢的,脸上带着笑,列队站在营门口,敲着脸盆欢迎我们。
我和另外17个新兵分到了二营五连。我们连长叫许排顺。连长把各个班长叫过来,说来了一批新战友,谁谁谁到一班,谁谁谁到二班。班长把我们领回各班帐篷。
我的班长是四川人。他把我领进帐篷,老兵们帮我拿行李,铺床,说你一路辛苦了。我一看那环境,心情不是很好,但是老兵的热情让我挺感动。帐篷里生的火炉子是用废油桶做的,上面连着两个水桶,里面都是雪水,一个洗脸,一个饮用。正副班长住在两头,中间住战士,因为两头到了夜里比较冷。帐篷里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用罐头盒做的。也不是煤油,是柴油,所以直冒黑烟。老兵们就往油里撒点盐巴,烟一下子就小了。这一手我很快就学会了。
当天晚上吃的是面条。那时的面条可是病号饭,一般人平时吃不上,那天是连队专门招待我们新兵的。还有大肉罐头、鸡蛋罐头。那顿面条吃得特别香,现在都记忆犹新。饭后,老兵们给我们打了一盆热水,说你们走了很远的路,烫烫脚好睡觉。这时老兵才告诉我说,我们是基建工程兵,是专门来修天山公路的。我一听心就凉了。本来想去前线,没想到被拉到这里修路来了。但是坐了几天的车,确实很乏,一躺下就呼呼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老兵们早不见了,上了工地,帐篷里就剩下了我们几个新兵。火炉子上有洋芋片,大米粥,还有七八个馒头。我们吃过饭,走出帐篷,外面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有几只比兔子大点的动物,肉乎乎的,笨笨的,在雪地上跑来跑去,“嘎嘎”乱叫。后来老兵告诉我们,那是旱獭。
我们几个没事干,就往山上爬。想爬到山顶上看看山外是啥样子。可是等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山外还是山,一座比一座高,连绵不断,没有一个人影,看不到尽头,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外。
我们坐在山顶,有些绝望。这咋整?怎么来到这么个熊地方!
晚上,指导员把我们新兵叫过去开了个会,说这是毛主席最关心的一条重要的国防公路,叫独库公路。但是你们给家里写信不要提具体干什么,也不要提国防公路,这是军事秘密。
最后指导员开玩笑说,新战友们,北京有北京的好,天山有天山的好,你们想想,你们在北京吃冰棍还得花钱,我们这儿的冰多的是,随便吃,不用花钱。
从此,我就在天山上开始了筑路生活。
在天山修路,牺牲是常事
那时,天山公路已经修了六年,大部分毛路已经开辟出来了。
部队没有大型机械,用的全是钢钎、铁锹,最先进的工具就是风钻。后来机械能开上山了,才配备了几台D80推土机。我们连队主要任务是备料。说实话,施工环境相当艰苦,劳动强度也相当大。早上天麻麻亮就得上工地,晚上天黑得看不见了才收工,中午饭在工地上吃,一天至少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
我们白天施工,晚上还要学习。学些啥?学政治,学“两报一刊”社论,学在天山上牺牲的烈士们的先进事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姚虎成和李善国,他们两个的墓碑你刚才在陵园里都看见了。
姚虎成是你们陕西人,城固县的,牺牲的时候是副营长。入伍前他是个孤儿,到部队后特别能吃苦,有点拼命三郎的劲头。部队打导洞出现塌方,他冲进去排险,连续42个小时没合眼。战士们把他硬从导洞里拉出来,强迫他休息。他从手腕上摘下手表交给通信员,说你半小时后必须叫醒我,否则我处分你。他只打了一个盹,又钻进洞里指挥排险。有一次,几台筑路机械要运上山,上级要求他带领战士们炸山开路。那时机械可是宝贝疙瘩,不能有半点闪失。他用七天就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保证将机械按时运上了山。后来他荣立了二等功,还当选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十一大代表。
我到天山的前一年,姚虎成和打前站的战友为大部队开辟道路。他们从早上一直干到中午,他看时间不早了,就让战士们先回去吃饭,自己和两个推土机手留下继续清除积雪。战士们刚走不久,冰达坂上突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响声,雪崩发生了,把推土机冲出50多米,两个推土机手昏迷在变了形的驾驶室里,姚虎成不幸牺牲,年仅28岁。当时他还没有结婚。姚虎成牺牲后,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荣誉称号,号召全军指战员向他学习。
另一个就是李善国。他是湖北武昌人,1965年入伍,牺牲时是政治指导员。1974年,他跟随大部队第一批进军天山。第二年6月底,他爱人来队,他正带领部队打“飞线”,没有下山去接,他爱人自己上山找到部队。爱人来队他也没有休息一天,坚持带领官兵在“飞线”施工。半个月后,一场意外的大塌方发生了,李善国等五位同志不幸牺牲。李善国终年29岁。他爱人就在不远的营地等着他。你想想多惨。
新疆军区有个作家叫李斌奎,好像也是你们陕西人,他根据姚虎城和李善国的事迹写了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还改编成了电影,就是8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天山行》。
我再给你讲一个比这还悲惨的故事。但不是发生在我们团,而是另一个团,我是听战友讲的。部队在“老虎口”施工,突然塌方了,一块巨石头落了下来,把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四川兵砸住了,整个身子都被压在巨石下面,压成了饼子,只有头露在外面。当时人没死,还能说话。战友们用钢钎撬,想把石头撬开,把他救出来。可是那么大的石头,咋撬得动啊!当时“老虎口”在悬崖峭壁上,机器又上不去。想用炸药炸开石头,又怕伤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看见战友的惨状,全连人哭着喊着围着石头跑来跑去,就是无从下手。
被压在石头下面的那个兵说,你们别白费劲了,我肯定活不成了,你们就把我和石头一起炸了吧,别影响施工。
谁忍心炸?没人这么干!
那兵说,我还没来得及给家里写封信呢。
战友们急忙找来纸笔,说,你说,我们写,一定寄到你家去。
那兵就说:爸,妈,我在部队挺好,工作也不累,吃得也不错,首长很关心我,战友关系很不错,跟亲兄弟一样,你们就放心吧。爸,妈,我啥子都好,就是有点想念你们。
说着,那兵的眼泪涌了出来,跟鼻子里的血一起流在了雪地里。
那兵最后说,爸,妈,我在部队很努力,干得不错,没有给你们丢脸。
在场所有的人都哭了。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战友们把全连所有好吃的东西找出来,轮流给他喂吃喂喝,陪他说话。第二天,那兵才牺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一点一点死去,那是一种啥心情?我每次想起这事都流泪。
当年在天山修路,确实很艰苦,很危险,战友牺牲的事时有发生,要不烈士陵园里咋会有168座墓碑?
有一个叫石博韬的湖北兵,在隧道施工时遇到了塌方,他为了救战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2006年,总队组织“重走天山路”活动时,也邀请了他父亲石文华。老人七十多岁了,当时站在儿子的坟墓前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老人说:我没有一天不想念儿子,我人在湖北,心在新疆,因为新疆还有我的儿子。每天晚上,我都和老伴要看新疆的天气预报,30年来天天都是这样,已经养成习惯了……
有一个老兵,叫董二龙,当年他们营打2号隧道,去年他从河南老家来新疆捡棉花,回去的时候专门跑到天山来,想看看牺牲的战友,看看2号隧道。他走到隧道口,“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泪流满面,他哭着说:30年前,我在这里奋战了5年,我的好几个战友就牺牲在这里啊……
“司令员同志,能不能让我们握握女兵的手?”
唉,不说这些伤心的事了,说说高兴的事。
要说最高兴的事,那就是看电影。当年在天山,也没什么娱乐活动,最多也就是看场电影。但是看一场电影要等一两个月,全线560公里,大家得轮流看。
一听说晚上放电影,大家早早就完成了任务,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精神。看电影要到营部去,全营一起看,要走好几公里地呢。最远的连队要走10公里。我们排着队,拿着雨衣,提着马扎,朝营部走。为啥拿雨衣?天山上一会儿雪一会儿雨的,没个准,看到中途下起雨来咋办?不能等雨停了再看,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人家电影队第二天还要赶到下个营去放映。我那时觉得当个放映员最牛,可以天天看电影。
那时电影都在露天看,哪有现在坐电影院里舒服。我们有天看得正起劲,突然下起了大雨。这咋整?没有一个人动,大家冒雨继续看。电影放完了,雨也停了。
营长喊:全体起立,各连带回!
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营长说:吆喝,今天还较上劲了,咋回事?
一个班长站起来说:首长,能不能再放一遍?我保证我们班明天不耽误施工,并且超额完成任务。
大家一齐喊:再放一遍!
营长没办法,去给放映员说情。人家不同意,说今天太晚了,我们明天一大早还得到乌苏去放呢。别看团里的放映员是个兵,说不放就不放,营长说话也不灵。营长悄悄给放映员塞了一包烟,放映员这才勉强同意,又放了一遍。
我们连有个陕西兵,我来的第二年他就复员了。当了五年兵,从来没去过团部。一个团撒在两百公里的战线上,远哪,不立功受奖,参加团里年底的庆功会,很少有机会到团部。指导员对退伍老兵说,你们在天山干了这么多年,今天就要复员回家了,还有什么要求?陕西兵说,指导员,我没有别的要求,走的时候能不能绕个道,让我们看看团部,在大门口照张相?指导员向团长汇报,团长同意了,就让老兵绕道去看了看团部,还专门安排人给老兵每人照了张相。
别说当兵五年没去过团部,就是女人也从来没有看见过。
有一年,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来天山公路视察,身边带着一个年轻女军医,顺便给山上官兵看个病。战士们哪儿见过女兵?眼睛都直了。
有个战士大着胆子报告说:司令员同志,能不能让我们握握女兵的手?
司令员一听这话,眼睛湿润了,对那位女兵说:去,跟战友们握一下手。
战士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家正在施工,手很脏,急忙用雪将自己的手搓洗干净,等着跟女兵握手。跟女兵握过手后,有的战士好几天都舍不得洗手……
我哪儿有那福气?我当时不在场,那是另一段工地。这件事后来在整个部队传为佳话,现在总队的许多领导都记得。
我的班长郑林书
我跟我们班长只相处了38天,我却甘愿用一生来为他守墓。
我原来是一班,那年老兵复员后,才把我调整到了四班。四班长叫郑林书,湖北人,个不高,圆脸,大眼睛。他普通话讲得不好,说话爱带个“老”字。说话爱带把子,我不大喜欢。但是后来有两件事,让我挺感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你也知道,山上海拔高,馒头蒸不太熟,抓在手里黏糊糊的,吃到嘴粘牙。把馒头从炊事班打回来,先放在火炉子上烤,然后再吃就好一点。你们那时在青藏高原也烤馒头吃?呵呵,看来都一样。对,用铁丝编个小笼,把馒头放上去烤,如果时间允许,烤得焦黄焦黄的,吃起来特别脆,一咬嘎巴响。我看老兵烤,我也去烤。第一个吃完后,觉着不过瘾,又烤了一个。结果吃到一半听到了集合哨子,我顺手把剩下的半个馒头丢进了帐篷角的脏水桶里,跟着战友跑了出去。
连长集合说,今天营里检查卫生,要求大家回去好好整一整,一定要扛上卫生红旗,不能给连队丢脸。那时啥都讲究争第一,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
可是还没等我们整理好,营里检查的人就来了。也该我倒霉,人家正好就抽查我们班,发现了我丢在脏水桶里的半个馒头。结果红旗没扛上不说,连长还让营里来检查的人训了一顿。那时丢半个馒头,可不是个小事。连长很窝火,把班长叫去训了一顿,让他一定要把丢馒头的人查出来。
班长回来黑着个脸,问谁扔的馒头?我看事情闹大了,吓得不敢吱声。我要是承认了,今后入党就没戏了,提干就更别想了。我心里有鬼,很害怕。班长瞅了我一眼,没说话。我是最后一个跑出帐篷的,当时就我一个人吃烤馒头,还能有谁?班长肯定知道是我干的,但他什么也没说。
班长从桶里捞出那半个馒头,看了看,当着我们全班的面,一口一口吃了下去。吃完后,班长说:我们部队苦,老百姓比我们还苦,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村来的,可不能这样糟蹋粮食!
我羞愧难当,感动得几乎给班长跪下。但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我没有勇气承认。这事我们班长自己扛了下来,说是他扔的,连长把他臭骂了一顿,没有再追究。一直到班长牺牲,我也没有机会向班长承认馒头是我扔的。我后悔死了!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
有一天晚上,我洗完脚,去帐篷外面倒水,刚一出门,我就“哗”的一声泼了出去。只听有人“唉呀”一声。原来是班长。他刚从连部开会回来,被我当头浇了一身脏水。那时山上多冷啊,零下十几度,泼出去的水很快就能结冰。
我说,班长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他一边往帐篷里走,一边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班的战士见我泼了班长一身水,赶忙帮班长把衣服脱下来,在火炉子上烤。大家都瞪着我,说你个新兵蛋子,净干些没屁眼的事!
班长冻得直打哆嗦,一边用毛巾擦头发上的脏水,一边说,没事没事,陈俊贵,你以后倒水跑远点,别倒在门口,一结冰,容易滑倒人。
这两件事,特别让我感动。这就是我的班长,比我亲哥哥还能包容我的战友!现在班长就躺在陵园里,我想对他再说声对不起,他都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