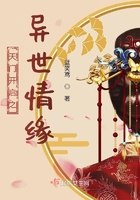一、宝玉真是雪芹的化身吗
倘或这宝玉,就是作者雪芹的化身
——他这般地恶搞自己,图什么?
当然亦可强辩:
雪芹并非常人,
他以“淫人”为傲。
就像而今有人炫富,雪芹喜欢炫性。
个人爱好嘛,与他人何干?
欲看清宝玉这位公子哥儿,先看他是如何荒淫的吧。贾琏是“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孙绍祖是“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而与宝玉比,他们竟连个小巫都不及。倘或不信,我且将宝玉那性伙伴儿的名单,及主要的情场性事,撮其要,删其繁,分类开列一番。你可别嫌絮烦。
(一)媳妇类
秦可卿
她是宝玉性榜之首。
宝玉在她床上睡中觉时,尽管雪芹作得至为朦胧,但二人的“儿女之事”,还是极彰显的。
宝玉先是看到了“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可卿又“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调情气氛已是十足。宝玉梦中相会的女子,偏又是“乳名兼美字可卿”“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这以梦写真的法子,正是雪芹的惯用伎俩。
至此,谁还能说宝玉可卿再无爱事呢?
可卿病故时,宝玉痛不欲生,“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这却不是宝玉恋情难舍,原是“第一个”的感受,竟是深刻的。
王熙凤
制灯谜时,宝玉“扯着凤姐,扭股糖似的只是厮缠”。“扭股糖”,却比拥抱还要扎实些。
凤姐协理宁府时,可卿的尸骨尚未入土,宝玉便见了嫂子,就忘了侄媳妇。他“便猴在凤姐身上”。这个“猴”,竟比“扭股糖”更甚。故凤姐道,“我乏的身子上生疼,还搁的住揉搓”。
“猴”除了“扭”,还兼着揉搓揉搓。
为可卿出殡的路上,凤姐独坐一车,寂寞了,便向宝玉笑道:“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坐车,岂不好?”宝玉哪里听得这话,他“忙下了马,爬入凤姐车上,二人说笑前来”。
在凤姐心里,宝玉猴在马上,自然不及猴在她身上的好。此时繁事已过,身子也不乏了,因便搁得住揉搓了。宝玉爬入车内以后,二人说笑间,若是不扭股糖、不揉搓,那才真是奇了呢。
我无那多经验,不知那放情揉搓的一男一女,如何避得了颠鸾倒凤的事。
嫣红
即贾赦娶鸳鸯不成,遂“各处遣人购求寻觅”,花“八百两银子”买来,收在屋里的那个17岁的女孩子。
先算个账。赵姨、周姨,以及后来的袭人等,这些妾的月例是二两银子。妾是半个主子,年薪二十四两。嫣红的身价,竟是半个主子三十三年的总收入。偏又是各处遣人寻觅来的,她如何不是“水葱儿似的”漂亮女孩儿。若是比不上鸳鸯那“一概齐全的”,人家大老爷又如何肯收呢?
其实,仅就“嫣红”这名字,便足以引出宝玉一番呆意的。刘姥姥信口开河,说了个“穿着大红袄的女孩”,宝玉都盘算了一夜,又给了茗烟几百钱,命去寻找。他在家等待时,竟“急的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如今一个叫作“嫣红”的标致女孩来到了贾府,宝玉怎甘做热锅上的蚂蚁,而不谋一会呢?
宝玉一旦会了,猴上来揉搓揉搓,嫣红又如何拒得了。因宝玉猴上来,较那大老爷自是活力多的。因此,趁大老爷不在,宝玉赶来幽会一番,便顺理成章。
这却不止我的推测。众姑娘填完柳絮词那时,窗外“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众丫环笑道:“好个齐整风筝!不知是谁家放断了绳,拿下他来。”宝玉一看便道:“我认得这风筝。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嫣红姑娘放的,拿下来给他送过去罢。”
宝玉连嫣红的风筝都认得。他建议送过去,当然是亲送。这一送,自然会送出个机会来。然他这既不深且不细的花马吊嘴,紫鹃一眼就看破了:“难道天下没有一样的风筝,单他有这个不成?”遂又颇失身份地,“我不管,我且拿起来。”这原是紫鹃维护黛玉的爱情,竟成心毁坏一次宝玉的作怪呢。
如说至此还不清楚,再看嫣红那风筝——“大蝴蝶”。蝴蝶不正是寻花问柳的使者吗?
(二)丫头类
袭人
与宝玉云雨初试时,“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今后再屡屡如此,自也是礼内之事。却有红学家叫喊,宝袭此后再无床笫之事。这是尚未读懂。
贾琏是个“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的人。因巧姐出天花,家里供娘娘,贾琏与凤姐隔房。除了“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还与多姑娘儿“宽衣动作起来”,甚至“恨不得连身子化在他身上”。便是这样,贾琏搬回的当夜,还与凤姐“新婚不如远别,更有无限的恩爱”。他去扬州那回,离家几个月。回家的当夜,却是真真的远别之后。雪芹却说:“一宿无话。”
可见这样的“一宿无话”,竟是这个意思。
宝玉在冯紫英家又是喝酒,又是唱淫曲儿,并有妓女尽意调情,“至晚方散”。宝玉回家面对袭人,如何不想那事儿。聪明的袭人“再要说几句,又恐怄上他的酒来,少不得也睡了”。
可见袭人善解人意。雪芹接着便告诉咱们:“一宿无话。”
明白了吧。
此前的那夜里,宝袭两人说话,越说越亲昵,直至“快三更了”,这便“从新盥漱,宽衣安歇”。这回,雪芹没说“一宿无话”,说了句:“不在话下。”
什么事“不在话下”?
已经睡下了,还要起床“从新盥漱”。这是贵族人“上床”前后均要洗洗的。那日,贾琏与凤姐白日亲昵,就是“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丰儿舀水进去”的。
就是这一夜,宝玉竟折腾大了。“至次日清晨,袭人起来,便觉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四肢火热”,传医看视后确诊为“偶感风寒”。
也许,这只是宝玉的牛刀小试,所以才“不在话下”罢。
再看宝玉与袭人怄气那回。宝玉次日醒来,“翻身看时,只见袭人和衣睡在衾上”。
多么清楚。袭人赌气了,和衣睡在宝玉的衾上。平时,又如何不是脱衣睡在衾内的。
再说宝袭仅有“初试”——也好,会把雪芹气得活过来呢。
晴雯
读过宝玉探晴雯一节,有人竟像晴雯嫂子一般,认为宝晴平日“各不相挠”。这便错会了意思。
晴雯也确是说过:“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可这并不等于说,宝玉没有勾引她怎样。那回宝玉邀她一块儿洗澡,她确是没应,但二人一块儿洗澡的事,却是有的。宝玉在《芙蓉女儿诔》(以下简称《芙蓉诔》)中写得清爽:“得于衾枕栉沐之间。”
衾是被子,枕是枕头,栉是梳头,沐就是洗澡。“得于衾枕栉沐之间”,“得”了什么?还用再说吗?
宝玉又说了:“亲昵狎亵,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畸。”
“亲昵狎亵”与那“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竟有多少区别呢?
若言证据,早已有之。袭人奔母丧回来那日,直接说到晴雯的当面:“我烦你做个什么,把你懒的横针不拈,竖线不动。”可是“怎么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这是说的晴雯病补雀金裘。接着,袭人便来了厉害的,“这又是什么原故?你到底说话!别只佯憨和我笑,也当不了什么!”
向来“千伶百俐,嘴尖性大”的晴雯,此时竟不像她自己了,“晴雯笑着,啐了一口”。
这是为何?“原故”是事实,晴雯不敢辩。
不久,宝玉与平儿同天过生日。次日,晴雯对平儿说:“今儿他还席,必来请你的,等着罢。”
这种时候,晴雯是应称呼“宝玉”的。可她与宝玉有了爱事之后,心里的感觉就不自禁地变了。此刻竟一没留神,溜出了平儿对贾琏的称呼——“他”。
平儿又如何不知意思,这便笑道:“他是谁?谁是他?”
结果,晴雯就“把脸飞红了”,一边“赶着笑打”,一边说道:“偏你耳朵尖,听得真。”
再看晴雯跌折了扇子骨那回。她与宝玉斗嘴,袭人便推她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
没承想,晴雯一听她和宝玉是“我们”,这就“添了醋意”,来了一顿夹枪带棒,“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哪里就称起‘我们’来了。”
袭人与宝玉称“我们”,自是她有侍妾之实。便是这样,遭到晴雯挖苦,她尚“羞的脸紫胀起来。想一想,原来是自己把话说错了”。晴雯被平儿奚落,却只恨平儿“耳朵尖”,并不以为自己说错了。这不是她自觉与宝玉的情分,原是高过袭人的吗?
实则,晴雯与袭人是一样的。她也是“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无论如何,总也“不为越礼”。
麝月
宝玉为她蓖头时,晴雯很吃醋,说了两句话,“哦,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了!”“你们那瞒神弄鬼的,我都知道。”
“交杯盏”,大家都通。“上头”是喝完交杯酒后,新郎为新娘举行的冠戴仪式。晴雯虽是讥讽,可也是有依据的,因她知道宝麝那“瞒神弄鬼”的事。
令晴雯想不到的是,她的“交杯盏”“上头”说,恰恰诱发了宝玉的春情,“这里宝玉通了头,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惊动袭人。”
这“不肯惊动”,不是瞒神弄鬼,是什么?“伏侍他睡下”,竟是怎么个“伏侍”法?在“不肯惊动袭人”之后,我们又看到了那四个字,“一宿无话”。
碧痕
她那事儿,偏又是晴雯爆的料。
端阳节那日,宝玉与晴雯吵了嘴,晚上又哄她,请她一块儿洗澡。晴雯摇手笑道:“罢,罢,我不敢惹爷。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足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作什么呢。我们也不好进去的。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么洗了,笑了几天。”
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两三个时辰,即四至六个小时。洗海澡都用不了这么久的。可见这回鸳鸯浴,改了不少花样儿。在浴盆里“洗”了,又在地下“洗”,所以“地下的水淹着床腿”。地下“洗”了,又到床上“洗”,所以“席子上都汪着水”。
且宝玉邀晴雯洗澡,竟那般不经意,对晴雯这番话也全无异议。这就是,他与碧痕、与晴雯、与其他丫头们共洗鸳鸯浴,倒是极随便、极平常的。
可见,怡红院里的丫头,尽在宝玉射程之内,且无一漏网。
宝玉对别处的丫头,亦颇有性趣。
金钏
宝玉搬入大观园之前,贾政叫他。他刚刚蹭到这边来,金钏便一把拉过他,悄悄地笑道:“我这嘴上是才擦的香浸胭脂,你这会子可吃不吃了?”
这便是宝玉时常吃她嘴上的胭脂。
宝玉若以为胭脂好吃,你让茗烟买一包袱来,不拘哪里吃去就是了,何必跑到人家嘴上来吃什么?
原来吃胭脂只是幌子,亲嘴儿才是真的。金钏能够拉住他,问他还吃不吃,这般主动的女孩子,宝玉那般高手,饶得了她吗?
况宝玉跟金钏的事,袭人也是心知肚明。金钏投井自杀,袭人“先是唬了一跳”,遂又“点头赞叹”。
赞叹是赞扬。怎么人家跳了井,她还赞扬?
原来,在袭人这情敌的眼里,主动退出竞争的谦让,自是好的。袭人赞叹之后,又“想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
这个“同气之情”最有趣了。极似今人说的“同情”:
同一个学校叫“同学”,同一个情人是“同情”。
鸳鸯
那次鸳鸯来怡红院:
宝玉便把脸凑在他脖项上,闻那香油气,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便猴上去涎皮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
一面说着,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
鸳鸯便叫道:“袭人,你出来瞧瞧。”
二十四回
宝玉在鸳鸯这里,施展的招式倒也全面:凑、闻、摩挲、猴、吃胭脂、扭股糖、粘。
鸳鸯却非但不惊,竟连半推半就都不曾有,一任他去。只是喊喊袭人,装个样子。这正是她对宝玉的“还是这么着”,早已习惯了。
宝玉这么喜欢她,能与她仅此而已吗?
贾赦娶鸳鸯未遂,便指斥鸳鸯,“多半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有贾琏”。
诸君,大老爷并未说鸳鸯只看上了宝玉,鸳鸯却做贼心虚,遂于贾母面前发狠道:“方才大老爷越性说我恋着宝玉……我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
她怎不说“琏天王”“琏皇帝”呢?退一步讲,如是只与宝玉扭扭股糖什么的,大约也不会这般撒急,日后,也不至对宝玉恼得那样。
许久后,老太太命鸳鸯取来雀金裘送了宝玉。鸳鸯当即撇下宝玉,来到外边,“站在地下揉眼睛”:
因自那日鸳鸯发誓决绝之后,他总不和宝玉讲话。
宝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时见他又要回避,宝玉便上来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这个好不好?”
鸳鸯一摔手,便进贾母房中来了。
五十二回
设若,宝玉没有相强鸳鸯做成什么,便是大老爷说了那么一句,又与宝玉何干?而今鸳鸯见了宝玉,又是淌眼抹泪,又是摔手撒气的,犯得着吗?
故此,鸳鸯想说的,就必是这样话了:人家不愿意,你一回回地强逼着。如今倒好,教大老爷都说出好话来了。我成什么人了?你却乐得逍遥,见了人仍旧涎皮笑脸的。谁稀罕?
(三)风尘类
云儿
宝玉在冯紫英家喝酒那日,有薛蟠、蒋玉菡,还有这个云儿。
薛蟠拉着云儿的手,让她把那梯己新样儿的曲子唱一个来。云儿唱的第一曲是,“想昨宵,幽期私订在荼架”。第二曲是:
豆蔻开花三月三,
一个虫儿往里钻。
钻了半日不得进去,
爬到花上打秋千。
肉儿小心肝,
我不开了你怎么钻。
这就把性事排弄得直白浅露了。然却不仅是黄曲儿。批书人于此连下两批:
此唱一曲,为直刺宝玉。
庚辰
双关,妙!
甲戌
何为“双关”?蒋玉菡念了一句“花气袭人知昼暖”,薛蟠便跳起嚷道:“你怎么念起宝贝来?”接着,云儿便把袭人的事“告诉了出来”。正如批书人说的:
云儿知怡红细事,可想玉兄之风情意也。
庚辰
这便明确了。宝玉“爬到花儿上”“往里钻”的,既“关”袭人,又“关”云儿。
其实,便是不“关”,只看云儿与宝玉之密切,也知他们是何等样的了。况她还是锦香院的妓女云儿。
(四)男宠类
秦钟
宝玉的风情艳史中:“女以可卿起首;男由鲸卿开头。”
宝玉与秦钟一见钟情,当即邀他来家塾里一起念书。如愿以偿后,便有了馒头庵那出床上戏。
秦钟正与小尼姑智能“云雨起来”,宝玉悄悄进来,突然将他二人按住,教人家猝然中断,并“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宝玉遂又质问秦钟:“你可还和我强?”
那潜台词是,你不是说只爱我一个吗?怎又这样起来?
秦钟还有什么可说?只得赶紧移情示爱:“好人,你只别嚷的众人知道,你要怎样我都依你。”
于是宝玉便笑道:“这会子也不用说,等一会儿睡下,再细细的算账。”
雪芹且将宝钟的床上戏,作了幕后处理。批书人却禁不住为之泄露一点。秦钟管智能与宝玉都叫“好人”,批书人批道:
前以二字称智能,今又称玉兄,看官仔细。
庚辰
看官不用仔细便明白得很。秦钟与宝玉上床之后,无非是再与这个“好人”“云雨起来”。因雪芹接着又说了:“一宿无话。”
次日,宝玉又“千姐姐,万姐姐的央求”凤姐,必要再住一夜,“于是又住了一夜”。不用说,这一夜还是一宿无话的。
蒋玉菡
当时的一位歌星,受雇于忠顺王府。初识时,“宝玉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接着又紧紧地搭着他的手,请他闲了往我们那里去。然后问他:“有一个叫琪官的,他在哪里?如今名驰天下,我独无缘一见。”
蒋玉菡说“就是我的小名儿”。宝玉惊喜异常,遂“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玦扇坠解下来,递与琪官”。琪官自是会意,一边说为了“表我的一点亲热之意”,一边当着宝玉“撩衣”,“将系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与宝玉”。琪官道:“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昨日北静王给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
宝玉“喜不自禁,连忙接了,将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了下来,递与琪官。”
汗巾子即裤腰带。琪官那条是“大红色”。宝玉这条是“松花”色,亦即浅黄绿。这时批书人说:
红绿牵巾,是这样用法。一笑。
甲戌
宋人吴自牧曾写书记载过嫁娶民俗:婚礼之上,一条红绿彩绸,中间绾成同心结,由新郎新娘各牵一端,相向而行。
红绿牵巾的典这样用法,岂不是说,宝玉与琪官正经是“拜堂成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