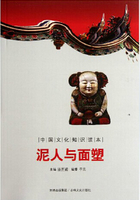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没有拼音字母,古代的识字,均用汉字来注音。古时汉字采用的注音方式有同音字注音(即“直音”)、同音不同调的字注音以及反切法。南北朝时,由于四声的发现,创立了声律理论,音韵研究之风也随之大起,韵书日见增多。如周研的《声韵》、张谅的《四声韵林》、段弘的《韵集》等。但这些韵书都没有流传下来。现存最古的韵书是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公元601年编写)。此后,各个朝代都有韵书出现,它们生动记录了汉语语音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并最终形成了今天所见的汉语语音系统。汉语的字音结构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声母的发音属于子音系统,其发声较弱,时值较短,若不伴随母音发音,就很难创造出更多的音节,从而限制了字音表义的功能。韵母发音则大部分不受阻碍,故声音十分响亮,且可以任意延长,它是构成发音声响、音色与共鸣的基础。
正是由于汉语字音结构的复杂性及其所具有的自然而丰富的音乐性,古代的歌唱家、理论家们十分重视演唱的字音,他们对吐字正音技术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其一,明确了演唱吐字时声母的喉、舌、齿、牙、唇五个发音位置和韵母的开、齐、撮、合四种口型,即“五音四呼”。其二,对汉语字音的特点进行了细致周全的研究,总结了一整套切实可用的吐字正音技术,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实践性。
语言是体现一个民族自身特色的重要标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有着各自的语言体系。任何一个民族的演唱方法都是建立在自身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的,不同民族语言的相异点越多,这种特性就表现得越明显。因而在吐字正音理论方面,中西方的差别十分明显。由于汉语的发音比西方语言复杂得多,演唱时必须做到声、韵、调三者合一,才能吐字分明、字音清晰;同时,还必须与声音的运用相结合,不能以字害声或以声害字。因此中国古代唱技文献中关于吐字的理论都相当丰富,众多论述都将吐字提到演唱的首要位置;在字腔关系上提出“以字行腔”、“字领腔行”、“腔随字走”、“字清腔纯”、“字正腔圆”等精辟见解,要求通过吐字来调整声音,强调字音清晰、音色明亮,这是中华民族的审美共性。这与西方唱技理论重声轻字、将吐字放在次要位置的理论思想存在着较大差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西方吐字正音技术理论的数量相对较少,在字声关系上也多要求咬字必须服从发声与行腔的需要。其原因在于:其一,在西方语言中,元音的吐发一般在口腔后部或咽腔完成,吐字较为容易。其二,在传统审美习惯的影响下,西方人演唱时更为强调声音的连贯、圆滑,而“多种母音要达到音质、音色的高度统一,以及共鸣的混合、声音高位置的安放,须将宽母音(开口音)变窄母音,将窄母音(闭口音)变宽母音,只有达到这种母音的转换才能实现歌唱发音肌体的相对稳定。这个目标的实现,几乎是以将咬字放在次要位置为代价的”。
$第一节 吐字正音技术的全面分析与总结
中国古代唱技理论家们以演唱实践为基础,将便于歌、利于歌作为整个吐字正音技术理论的逻辑中心,进而对吐字正音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当时及后世唱者进行直接的指导,影响深远。
一、对“五音四呼”的分析与总结
在古代唱技理论中,“五音四呼”是理论家们经常论述的要点之一。中国古代较早涉及歌唱吐字发音位置的是南朝梁刘勰,其《文心雕龙·声律》篇中指出了歌唱中声母的四个发音位置:喉、舌、唇、齿。他说:“夫商徵响高,宫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刘勰之后,北宋沈括也曾谈到:“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南宋陈元靓第一次对演唱吐字的发音位置及口型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阐述,其《事林广记·遏云要诀》曰:“字有唇、喉、齿、舌之异……必别合口、半合口之字。”陈元靓此语不仅指明了声母的发音部位,而且对韵母的发音口型也有所涉及。“合口”,指唇敛成圆形,口腔中空,音出咽部,如带韵母u或o音的字;“半合口”,指唇撮起,嘴的两角肌肉收束,音出口腔中部,如带韵母u(鱼)的字。此外,陈元靓在《事林广记》庚集上卷中收录的《正字清浊》一篇里,细辨喉、舌、齿、牙、唇五音与开、齐、撮、合四呼之区别,并对撮唇、卷舌、齐齿、穿牙、引喉、随鼻、合口、开口等不同发音部位及口型的字进行了列举。他要求唱者讲究反切,注重四声,明辨清浊,严分“五音”与“四呼”,以达到歌如贯珠、字正腔圆的审美要求。《正字清浊》一篇不仅是宋代教坊乐工学唱必须练习的要诀之一,对今天的民族声乐演唱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详见上篇第二章第一节)
元代以后,演唱时注意“五音四呼”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其论述不断增多,研究逐步深入。如明沈宠绥《度曲须知·出字总诀》中详细列出不同字音的发声位置及口型,“一东钟,舌居中。二江阳,口开张。三支思,露齿儿。四齐微,嘻嘴皮。五鱼摸,撮口呼。六皆来,扯口开。七真文,鼻不吞。八寒山,喉没搁。九桓欢,口吐丸。十先天,在舌端”等等。试分析其中一二,如“六皆来,扯口开”,该例指韵母的口型变化,“皆”、“来”二字在发音过程中韵母要变换两次口型:“皆”由齐齿呼的i变为开口呼的e;“来”由开口呼的ɑ变为齐齿呼的i,二者的发音都需要嘴的上下开张,故曰“扯口开”。再如“七真文,鼻不吞”,所谓“鼻不吞”指所发字音是前鼻音,因此气息应从舌头两边出来,而不能从鼻腔出来发成后鼻音。此外,沈宠绥在《转音经纬图》中更指明了不同字音唇、牙、舌、齿、喉的不同发声位置与发音的清浊,给予唱者切实的指导,极具实用价值。
清徐大椿对吐字的发音部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规范。《乐府传声·出声口诀》云:“又喉舌齿牙唇,虽分五层,然吐声之法,不仅五也。有喉底之喉,有喉中之喉,有近舌之喉;余四音皆然。”徐大椿指出,虽然演唱吐字发音的部位是喉、舌、齿、牙、唇五个部位,但发音的位置并不仅限于这五个地方。以喉音为例,可以从喉的底部发音,可以从喉的中部发音,还可以从靠近舌根的地方发音,其他四个部位也是如此。又说:“更不仅此也,即喉底之喉,亦有浅、深、轻、重;其余皆有浅、深、轻、重。千丝万缕,层层扣住,方为入细。”不仅如此,即使只在喉的底部发音,也还有浅、深、轻、重之分(而不是完全一样),其余四音也如此。这其中的头绪纷繁复杂,因此,必须系统、深入、细致地一步步掌握住其中的规律和方法,才能真正体会并运用到演唱实践中。可见,徐大椿的见解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对发音部位的分析更加深入、细致、全面。这种对发音部位的细分尽管略显琐碎,但对演唱者唱准字音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二、正五音、清四呼、知归韵、准四声
古代的吐字正音技术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正五音、清四呼、知归韵、准四声。所谓“正五音”指演唱时须唱准字头的声母发音,即咬字准确;“清四呼”指要辨明不同韵母的发音口型,即韵母字腹在延长的过程中需要保持的正确口腔形态;“知归韵”指要按照不同的韵类将字的尾音收归到应有的位置;“准四声”指演唱时要分辨出不同字音的平仄字调变化。以下逐一分析之。
(一)“正五音”
“正五音”即纠正字头的声母发音。明沈宠绥明确指出,在演唱吐字中,字头是必不可少的。其《度曲须知·字头辨解》云:“试听字音乍出,其齿舌间一点微风,略带音响,原天然隐跃字端,虽善淘洗,能去之哉?”沈宠绥认为,字头是一字天然之始,决不可省略。又说:“惟字头有推移之妙,亦惟字头有泾渭之分。”徐大椿曰:“欲正五音,而不于喉舌齿牙处着力,则其音必不真。”意即演唱时如果不将字头的声母部分咬得准确、有力,发出的字音就不会正确。又说:“喉舌齿牙唇,虽分五层,然吐字之法,不仅五也。有喉底之喉,有喉中之喉,有近舌之喉……即喉底之喉,亦有浅、深、轻、重。”可见,字头的发声是很有讲究的,必须仔细揣摩,方能掌握其法。
尽管字头的发音十分重要,但由于其所占时间短,故常常被听者和演唱者忽略。沈宠绥《度曲须知·字头辨解》云:“至字端一点锋芒,见乎隐,显乎微,为时曾不容瞬,使心浮气满者听之,几莫辨其有无,则字头者,宁与字疣同语哉?”沈宠绥对时人在演唱中常常忽略字头,甚至将字头当作字疣,视之为多余无用的东西这一现象深感忧虑:“予向恐世人之认字疣为字头也”,因此特意作“字头辨解”篇云:“吾故作此辨解,以唤醒夫认字疣为字头者,更以唤醒夫认字头为字疣者”。为了使时人分清字头与字疣的区别,突出字头的重要性,沈宠绥在文中将字头与字疣仔细进行分辨:“盖字疣之音,添出字外,而字头之音,隐伏字中,势必不可去,且理亦不宜去。凡夫出声圆细,字头为之也;粘带不清,字疣为之也。”大意指字疣是一个字本身发音以外的、多余添加的音;而字头则是一个字本身发音的一部分,不管其长短,都是字的本身发音,因此决不可以省略。如果吐字时声音圆润细致,是因为字头发得好;如果发音粘滞不清,则是由于有多余的音(字疣)混杂其中,导致字音不清。但对于字头的发音,沈宠绥又认为不能刻意为之,如果过于夸张,则会影响发音的纯净,反成字疣:“夫惟十分涤洗字疣,乃存真正字头,而一意描写字头,反成真正字疣。音本生成,非关做作,有心去之即非,有心存之亦非。”
可见,古人对于字头的发音十分重视。事实上,要想正确发准字头声母,首先须仔细辨认出声母的发音部位,并将发音部位接触准确,再根据不同的发音方法出声,才能使字头准确。同时,字头还要具有一定的力度与弹性,因为字头声母除阻的力度强弱与字的清晰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要想咬字清晰、准确就必须快捷、有力地咬准字头,充分利用喉、唇、齿、牙、舌的力量来调整字音。此外,尚需注意,咬字松散、轻飘固然不好,但若咬死、咬僵也会破坏声音的美感,故正确的咬字应是紧而不僵,松而不泄。
(二)“清四呼”与“知归韵”
二者指的是韵母的发音技术。韵母包括字腹、字尾两部分,演唱中,字腹的音值延长时要求不变形,要保持口型不变,使字腹能充分发挥母音的共鸣作用,避免因口型变化而导致音质不纯,从而影响词义或造成音包字的现象。字尾是音节结构中的最后一个成分,字尾的准确与否不仅会影响意义的表达,还会影响气息的连贯与完善。因为字尾既是一个字的结束部分,又是下一个字发声的先导,具有上下衔接的作用。清黄幡绰《梨园原》云:“唱曲不知发声收声之理,则其字音出口即变。”清李渔曰:“世间有一字,即有一字之头,所谓出口者是也;有一字,即有一字之尾,所谓收音者是也。尾后又有余音收煞此字,方能了局。”徐大椿《乐府传声·出声口诀》曰:“欲准四呼,而不习开、齐、撮、合之势,则其呼必不清。”王德晖、徐沅澂《顾误录·度曲十病·不收》云:“一字唱完,须交代清楚,再唱下字,方是本字之音。如出而不收,张而不闭,是仅有上半字,无下半字,欲其入听,不亦难乎?”可见,古人对演唱的字音特点及运用在理论及实践上均有深刻认识,“清四呼”与“知归韵”在古代的演唱吐字技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最早对“清四呼”的技术作出详细陈述的当属南宋陈元靓,他不仅在《事林广记·正字清浊》一篇中将常用字的“五音四呼”一一列举,又在《事林广记·合口字诀》一篇里详细阐述了部分容易混淆的合口字的发音吐字方法:“(侵寝沁)平上去声皆口噤,(谭非谈)二韵双声合口参……(感和敢)二字合音当一览,(琰忝广)合口动唇堪点检,(赚槛范)合口收来无杂犯。”此外,明沈宠绥《弦索辨讹》里取当时最流行的《西厢记》及其他北曲32套为例,以《中原音韵》为准则,对其字面作了声母、韵母的精确化和“义讹”字词的纠正,并列出六种发声口型及发声方法:“闭口”、“撮口”、“鼻音”、“开口张唇”、“穿牙缩舌”、“阴出阳收”,以供唱者参照。
四呼不准容易把字唱成两截,变为别字,古代理论家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王德晖、徐沅澂《顾误录·度曲十病·截字》中指出:“一字出口,无论几许工尺,必得唱完,口不改样,至尾方收本字之韵,方是此字音节。若中间略一张合,已将字截为两处,单字唱成叠字矣。或工尺未完,收口太早,下余工尺,仅有余腔,并无字面,此病最易忽略,亟宜审究。”大意指唱一个字时,无论它的曲调有多长,都要保持准确的口型唱完,到字尾的时候再收韵停声,这样发出的字音才准确、清晰。如果在拖腔的过程中口型任意变化,往往会将字截为两段,使单字变成叠字。而当曲调没完时就提早将口型恢复原状的话,则剩下的部分就只有曲调,没有字音,听众自然也不会明白所唱内容。如唱“读”字,在延长u音的时候,嘴皮应有劲,口的开度要小,唇成圆形,并一直保持口型不变。若中途嘴唇松劲或口的开度过大,则易变成o音,整个字音也就变为“多”,成别字了。
现以昆曲《牡丹亭·游园》折中《皂罗袍》的第一句歌词为例,试分析其中个别字音韵母的口型处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中的“姹”(chɑ)字占时两拍,由五个音组成,时值较长。在演唱的过程中,其韵母a要注意保持住开口呼的口型,口腔开度较大,发音时着力在口腔后部,而不能在音的延长过程中缩小口型或是只唱两个音就收口,这样容易形成别字或吐字不清。同理,“紫”(zi)的韵母为齐齿呼i,有四拍时值,在后两个音的延长过程中也要始终保持口型不变。但“遍”(biɑn)字的发音与前两字又有所不同,其占时五拍,由七个音组成。“遍”的韵母有两个音素,介母i与声母b结合成字头,要唱得敏捷、短促、有力。在其演唱过程中,韵母要变两次口型,即从齐齿呼的i变为开口呼的ɑn,在延长ɑ音时,要带有字尾n音的成分,但韵母ɑ音的口型要一直保持到音符的最后部分,再归音到n结束,而不能过早收口,否则无法收韵,容易变成“别”(bie)音。可见,“清四呼”是使歌唱字音清晰的重要技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