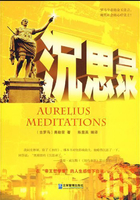《立志说》在最后给企图自暴自弃的人给予了鼓励,并引导人将原本并不正确的志向归入正途。在刘宗周看来,立志虽然重要,但起手处便不错并不容易,即便像阳明这样大根器的人于此尚费周折,何况其他的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正的觉醒,不能自暴自弃。刘宗周为此树立了白沙、阳明、萝石三个榜样以坚定学人志于正道的信心,寓训导于启发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刘宗周对志正确与否的判断是站在儒家的传统立场上的,这等于认定了儒家的唯一正确性,如果对这一点没有认同,这个志恐怕很难立。人只有和他自己的生命有了真实的接触,发心立志才不会流于肤浅,也不易为世风所动,毕竟真正的立志并非去培养一个人的先入之见。
总之,作为工夫的起点或者说准备阶段的立志,其实是在为后面的涵养等工夫埋下伏笔、指引方向、确定内容。因为它潜伏了“意”。
并且,这一阶段已经可能激活人自性中的一些种子,使得它们开始对外部环境中的信息和能量进行有选择的吸收了。不仅如此,在《立志说》中还全息着后面的一些工夫,比如文中所谓“今之学道者,虽十分亲切,觉得此中隐隐一物有以出乎其上,或潜或露,时有时无,此处毫厘走作,彼处十分都是虚假,只为其志在此而不在彼也”是省察;“恶衣恶食”作为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则是应事中的涵养等等。
(第二节 涵养
蕺山的心性哲学非常强调涵养,特别是其50岁前后“终日在韩山草堂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对涵养一路颇有受用,《年谱》谓其“渐见浩然天地气象,平生严毅之意,一旦消融”,“自是专归涵养一路”。可见对涵养的重视可以视为刘宗周心性哲学的一个转折点。
刘宗周心性哲学中的所谓“涵养”工夫,先出“静”字。这是一种求放心工夫,方法简约:
坐间本无一切事,即以无事付之。既无一切事,亦无一切心,无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则放下,沾滞则扫除,只与之常惺惺可也。此时伎俩,不合眼,不掩耳,不趺跏,不数息,不参话头。只在寻常日用之中,有时倦则起,有时感则应,行住坐卧,都作坐观,食息起居,都做静会。昔人所谓“勿忘勿助间,未尝致纤毫之力”,此真消息也……只此是求放心真切工夫。这种方法横说竖说不出“不起念”三字,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是讨到滋味了。这种静其实是在“养和”。在刘宗周看来,人心终日纷纷,唯有艮身心,遣物累,方能不为外境所转,他在《艮止说》中说:
凡人终日纷扰,只为胸中有物累未遣,内而七情为枸,外而五凿为迎,人己之间,动成障碍,虽欲求一息之止息,其得乎?物累既遣,则此心澄然湛然,常复其至善之体矣。一身之中,耳以司听,目以司视,口以宣言,四体以效动,而至此皆过而不留,若堕体黜聪者然,所谓“不获其身”也。身且不有,而况于庭除之地,更有人境乎?我返其视,而天下之为色者空矣;我却其听,而天下之为声者寂矣;我收其言动,而天下之为事物者化矣。虽金珠百万,不殊疏水曲肱也;虽天下之大,九州之远,不殊几席也。未尝无身也,未尝无人也,止于至善而已矣。终日止而终日行,其生机之融融于宇宙者,固未尝有一息之间也,此圣学之本也。这一段工夫虽从《易经》艮卦中化出,但其方法与境界颇有些道家意思。但刘宗周并未因此转向道家,因为他点出了此工夫的最终目的“止于至善”,所以他仍是提灯照路:灯是道家的,路是儒家的。
由于艮背之学也是禅门捷径,为了防止禅学倾向,刘宗周在此特别强调了静坐中性体的确立,并提醒说:“学者苟不识性,而求内外之两忘,鲜不流于禅者。”但是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刘宗周当然是通过静坐使性体呈露(意),如果通过静坐性体会自然呈露的话,那怎么会有陷于空寂的可能呢?这一点刘宗周没有说清楚。
刘宗周还有四首《静坐》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宗周静坐法的主脑和受用:
学圣工夫静里真,只教打坐苦难亲。知他心放如豚子,合与家还做主人。隐隐得来方有事,轻轻递入转无身。若于此际窥消息,宇宙全收一体春。
万法论心总未真,精神一点个中亲。不求坎离还丹诀,且问乾坤成位人。亘古生生惟此息,只今惺惺亦非身。请观声臭俱无处,毕竟谁尸造化春?
有物希夷气象真,多从血肉认非亲。闲来拭拂尘中镜,觉后方呈梦里人。呼吸一元通帝座,往来三复得吾身。憧憧思虑成何用?月过中秋花又春。
圣学相传自有真,舂陵一脉洛中亲。惟将敬字包终始,恰与几先辨鬼神。黑浪岂随初乘佛?嵩山应误再来身。凭君决取希贤志,口诀虽然不度春。这四首诗可以视作刘宗周对自己静坐法的总结,其中包括了与其静坐相关的所有内容。“知他心放如豚子,合与家还做主人”是说求放心;“且问乾坤成位人”、“请观声臭俱无处,毕竟谁尸造化春”是慎独;“精神一点个中亲”、“若于此际窥消息”、“恰与几先辨鬼神”是诚意; “隐隐得来方有事,轻轻递入转无身”、“憧憧思虑成何用”、“闲来拭拂尘中镜,觉后方呈梦里人”是治念;“惟将敬字包终始”是持敬避空;“黑浪岂随初乘佛?嵩山应误再来身”是左袒非佛;“不求坎离还丹诀”是右袒非老。宗周的静坐法于此便“一体全收”了。至于刘宗周的受用,可以用这四首诗韵脚的几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真、亲、春。真是真实,亲是亲切,春是满腔子的生机与和气。
如此看来,刘宗周通过静坐使得严毅气象得到了不少化解还是比较可信的。
需要指出的是,刘宗周虽然以静坐为根本,“静时不得力,动时便走作”,但他所说的静并不是只指静坐,从更高层次上讲,日用之间无不是静,也就是说“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即静即动,无动无静”,并以此为“君子尽性至命之极则”。这样便将周子“主静立人极”之说贯穿于后面各层次的工夫之中。
刘宗周心性哲学中的“涵养”工夫,次得一“养”字。那么养何物,如何养?他说:
孟子言“养心”,又言“养性”,又言“养气”,至程子又言“养知”,又每谓学者曰:“且更涵养”,养之时义大矣哉!故曰: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涵养之功,只在日用动静语默之间。就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一衣一食理会,则谓之养心;就时动时静、时语时默、时衣时食理会,则曰养气;就即动即静、即语即默、即衣即食理会,则曰养性;就知动知静、知语知默、知衣知食理会,则曰养知。其实一也。如果说静是偏重于呈露端倪,养则是偏重于护持苗芽、聚集能量,动静语默间都是用功道场,其微妙处皆在“理会”二字上。在刘宗周这里,心、性、气、知是打通的,养一可以兼四。其中刘宗周尤重养浩然之气,以养气兼养性之功。他在给沈石臣的一封信中就说:
“养气即养其性之别名”,可见他对人精神境界与体内气机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十分敏感的。他的养气说强调了志对于气(能量)的驾驭作用:
浩然之气,即天地生生之气,人得之为元气而效灵于心,则清虚而不滓,卷舒动静,惟时之适,不见其所为浩然者。及夫道义之用彰,而冲塞之体见,浩然与天地同流矣。处富贵而不淫,处贫贱而不移,遇威武而不屈,皆是物也。集义所生,是此气根柢萌动处,精义入神而后谓之集,非零件凑泊。零件凑泊,正所谓义袭也。勿忘勿助,打成一片,工夫只在持其志。
志之所之,即是气之所之;志不可夺,即是气不可御,非有二也……志之所之,本乎心之所存……学者当求放心,此志自然有运量,不怕无浩然作用。若心放,则志气游荡,终成消靡。
不翕聚则不能散发,故曰:“夫乾,其静也专;坤,其动也直。”这一段是刘宗周对孟子养气说的阐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宗周自己的养气方法。首先是集义以生发、招集此气息;其次是持志,用意志控制住这股能量以防其消散。集义和持志都是为了使所聚集的能量“正”和“大”,而“正大”正是浩然二字的注脚。最后是用志调动这股能量,便是浩然之气的发用。由于不论是集义还是持志,都必须本之于心、守之以静,因此所谓的养和静并非截然分开的,二者虽各有偏重,但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刘宗周又说:
“善养浩然之气者,尤在主静以立极乎?”
养浩然之气“勿忘勿助”四字最为要紧,其中“勿助”最容易被忽视。因为常常有其他的气息夹杂在浩然之气里,但却并不容易辨认,比如杀气、骄气,等等。并且,对浩然之气的过度体验会产生一种自我迷恋,以及对气象的刻意追求。究其原因,乃是潜意识的冲动经过装扮,以符合于志的形式,通过志对能量的驾驭暗地里表达着自己,其结果便是助长。所以养气尤要小心,因为气作为能量,如果发用不当,就会产生破坏性。“勿忘勿助”四字文中虽也提到过,但这却正是刘宗周这种性格的学者最容易出的问题,他容易过于“助长”,因为他过于“勿忘”。他也提醒过别的学者要注意助长的问题,但这并不能说明他自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反而可能是由于自身存在问题而产生的心理投射。一般证道心切的人都容易有助长的毛病。
养又有对某种状态的保持之意,是为了培养某种素质。这种养护相对于前面的更具体,是前面修养工夫的细化。刘宗周说:“清明以养吾之神,湛一以养吾之虑,沉警以养吾之识,刚大以养吾之气,果断以养吾之才,凝重以养吾之器,宽裕以养吾之量,严冷以养吾之操。”这种涵养工夫已渐渐摆脱静坐,而行于日用行事之间。
此外,刘宗周又以养性兼养命。他说:“寡思虑,绝嗜欲,薄滋味。三者,养身之要也。”由于刘宗周一生皆在病中度过,对于药理病理皆有研究。这从他给学生祝渊(开美)的一些书信里就可以看出。在信中,他谈论了对许多药方的改进方案,并对一些庸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表现出了很高的医学素养和自信度。他虽然不弃药石,但在他看来,身病是标,心病是本。欲无身病,关键在于调心。《会录》中记载了他对此的一些体会:
癸未四月十七日,舟次津门,子汋病气上升,先生语之曰:
“终日说降气,曾不肯将心来降下。学者只因一种飞扬跋扈之性不曾放下,因此一时拘束,未免不得发舒,遂郁而成火。在舟不安,因思从陆;从陆未安,因想抵家;抵家后一事未了,又复一事。从中憧憧,终无歇息,遂汩没至老。若是者,何也?
盖因此中纷纷扰扰,皆是有所为而为底。若是安土敦仁,自然随遇而安。吾只劝女放下罢,即此是却病之方,即此是养心之法。”他在给弟子祝渊的几封书札里也时常提及这种见解:“心病之外别无形病,治心之外亦别无调理血肉工夫。”由于在刘宗周这里,万事缘由总在心,心性的修养工夫小则安身立命,大则齐家平天下。真是“养之时义大矣哉”!
静和养这两项工夫对刘宗周的身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过这种训练,刘宗周的省察能力变得非一般人可比,他的心更加细密,对气的驾控能力也非常的强,不至于使本能冲动乱了体内的气机,身体也因此得到了受用,气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但从另一角度看,这种工夫只是一种自我控制的手段,再成功的压抑也还是压抑,如仍不能和自性对话,那么这种工夫还是半得半失的。
刘宗周的另一涵养方法乃是一“学”字。他在韩山草堂读书时,便是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为功课,由是而归涵养一路。那时的刘宗周虽开始受到阳明学的影响,但此两项功课却是由朱子“学者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是三五年,必有进步可观”那里学来的。读书学习在刘宗周涵养工夫里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它不同于一般为寻求知识和应举业而进行的学习,而是通过学习发明本心、印证本心、护持本心。他在《读书说》中说:
学者诚于静坐得力时,徐取古人书读之,便觉古人真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于我,而其为读书之益,有不待言者矣……夫圣贤之心,即吾之心也,善读书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因此,在刘宗周看来,既然我的心和圣贤的心等无有二,从圣贤的心中流出的义理,我的心中自然也有,因此通过读书,我们可以和圣贤心心相印。善读书的人就是善于将书中的义理求证于我心的人。
这是典型的心学路数。所以,如果按刘宗周的说法,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启发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将外在义理内化的过程。此即是说,人是被点化出来的,而不是被塑造出来的。他在另一篇专门开示儿子的《读书说》中写道:
夫书者,指点之最真者也……先之《小学》以立其基,进之以《大学》以提其纲,次《中庸》以究其蕴,次《论语》以践其实,终之以《孟子》以约其旨,而所谓恍然于心者,随在而有以得之矣。于是乎读《易》而得吾心之阴阳焉,读《诗》
而得吾心之性情焉,读《书》而得吾心之政事焉,读《礼》而得吾心之节文焉,读《春秋》而得吾心之名分焉。又读《四子》以延其流,读《纲目》以尽其变,而吾心之无不自得焉。其余诸子百家泛涉焉,异端曲学诛斥之可也。这一段是论述在以《小学》立基之后,通过《四书》启心,而后知《六经》等书非是我心外之物。但这一段中“得吾心之”四字非常值得探讨。此四字的意思是孟子所谓“非外铄我,我故有之”之意,是说我心中之理在《六经》那里得到了印证。但我们是否可以用《小学》以来的筑基阶段来解释部分“我故有之”的东西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义理就仍然可能是“由外铄我”的内化结果,而未必是“我故有之”的了。这也就使得部分义理的先天性出现了问题,成了习得的了。
之所以对这一点提出怀疑,是因为这一点似乎可以被反证法推翻,即假设这些义理的先天性可以成立,那么如何解释不同时空内的人们何以有不同的观念、信仰以及行为方式呢?如果这些义理节文都是人先天存在的,那么它在时空上就应该有普遍性和永恒性。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倒是心理和情感相对于义理更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所以在刘宗周的无意识里一定存在一个先入之见,这个先入之见是“由外铄我,故我有之”,虽然刘宗周否认知识的被内化,但知识的确被内化了,只是这个被内化的过程是无意识的。
刘宗周希望通过学习发明本心,认识心体的广大和无所不包,但由于那些先入之见以及对先贤的崇拜使得这种学习反倒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同时使得心体受到束缚而未能广大,也使得其学术缺乏开放性而趋向保守。他不能相信有圣人之外的义理,就是一个证明。
并且,他会用先入之见的“本心”去衡量其他思想,态度简单粗暴,如所谓“异端曲学诛斥之可也”。刘宗周的哲学思想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即他所反对的东西常常就是他自己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他经过深入的自我反省和体察后发现的,他的一些议论常是对此而发,其根源处是一种内部的自我教育。如他反对“识神用事”,反对“以识为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