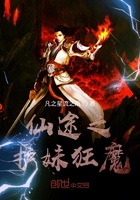黛玉闻言太阳穴簌簌的跳了两下:“可有看的清楚,确实是她?”
“衣服鞋袜都是,年纪也像,就是因泡了许久,都发了胀,容貌看不得十分真切。”
黛玉凝眉不语。
云姨娘已经诧异道:“好好的,她跑到护城河边洗什么衣服?”
黛玉心中已经有数,敛容道:“去认下,说是咱们府中的人,然后拿薄棺殓了,好好安葬。”
“是。”
“姑娘真是好心的人。她一个落难人,若是当日不是被姑娘救回,已经做了路倒尸,如今枉死了,还有口棺椁殓了。”
黛玉轻叹一声,不语,轻轻攥紧了那半枚指环。
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八月初六,是西羌使团离京的日子,司徒娬儿也就是在这一日,披上华丽嫁衣,在宇文承彦的护送之下,以公主之礼离京,排场摆的异常的大。
听说是京城闺秀中的第一人,才貌双绝,且有公主之名,嫁资丰厚。那西羌使团自然是欢天喜地的谢恩,也不再计较是不是正经公主。
十里红妆,自城门蜿蜒着铺开,如同一路血染。
水溶率京畿卫一路护卫,一身利落银色王袍,倜傥俊雅,杂在一群红衣之中,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轿中,司徒娬儿自大红轻纱之下,望着他,带了几分割舍的痛楚,华丽的嫁衣之下,她的手里攥着什么东西,攥的那么紧,紧到指节都在哆嗦。那仿佛那是她最后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
水溶,是你待我无情,那就别怪我无义。
她的嘴唇紧紧咬着,樱唇殷红如同滴血。
路行一日,到了傍晚,便歇宿在京城三十里外的驿馆。一切都是早早安排好的,自有随嫁的宫女伺候司徒娬儿回去休息。
宇文承彦随便看了看周围,便哈欠连天的向水溶道:“北王,一切都交给你了。这一日骑马,孤实在是倦的了不得。”
水溶也只道:“请殿下安置。”
宇文承彦拍着他的肩头:“多累了,北王。”
“不敢。”水溶微微一躬身道。
宇文承彦点点头,离开。
水溶目送他离开,目光霎时变的冷峻,这时,他的身后一道黑影无声飘了下来:“王爷,京中秘报,魏王悄悄潜回京中,似乎带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入了宫。”
水溶眯了眯眸,精芒一闪而过:“知道了。京畿内外,都盯紧了,但是非到关头,不必露出行踪。”
“是。”黑影如猎鹰一般霎时又隐没无踪。
就在这时,一声凄厉的喊声,自司徒娬儿住的内院响起——“有刺客。”
驿馆内外,立刻发出骚动,连带出一阵乱。
连水溶身边的贴身侍卫们都是浑身一紧,齐刷刷的望向水溶。
唯一没有任何动作的,便是水溶。
他负手而立,遥遥的望着那座小楼,嘴角挂上一丝绝冷的讽刺的笑,低低道:“戏还不错。”然后这才道:“过去看看。”
“是。”
二层楼阁都是一片凌乱,司徒娬儿的卧房外,几个随嫁的宫女被刺死在当场,血涂了一地,凌乱不堪。
一个宫女脸色煞白的跑来:“王爷快去看看吧,公主受伤了。”
水溶面色甚冷:“公主受伤了?太不小心了,来人,去请随行的太医来此。”
宫女的脸色更白了。
“王爷!”一个带着哭音声音响起,一个人一道风似的出来,直直的撞向水溶怀中。
在她出来的时候,水溶的眉峰就是一沉,剑鞘一横,便将她逼在了一尺之外,然后利落的收回:“公主,出什么事了。”
司徒娬儿一怔,不得不站住,她的脖颈上果然有一道伤痕,血淋淋漓漓的滴在寝衣之上。单薄的寝衣勾勒出呼之欲出的曼妙曲线。
水溶冷冷道:“令公主受惊了。本王今夜会多加派人手,守着这里。”
“刺客的武功很高,恐怕再多的人也于事无补。”司徒娬儿道:“恐怕也只有北王在此才能无恙。”
水溶微微挑起眉:“公主的意思是……”
“北王受父皇之命保护娬儿的安全,若是刺客再来,护卫不利,恐怕王爷也难以置身事外。”
水溶敛眸,淡声道:“既然如此,今夜本王会在公主房外保护公主。”
司徒娬儿低头道:“那多谢北王了。”
“请公主回去休息,放心就是。”
司徒娬儿点点头,自回房去,眸中不可抑的闪过一丝喜色。
她并没看到,身后,水溶冰寒彻骨的眸子。
月绯霜幽,抹过横斜曲回的扶廊。
白衣的男子在如水清华中静静的负手而立,月将他的白衣勾出萧冷的轮廓,仿佛有皓雪纷垓落了一身。
水溶静静的看着那月一寸一寸的升至中天,直到,一个娇柔的声音自耳畔响起:“王爷。”
那声音带了三分妩媚,七分撩人。
同时,一股异样的香气,萦上鼻息,水溶并不回眸,眸色锐冷犀利,声音里亦透着些许魅惑:“这么晚了,公主还没休息。”
“娬儿睡不着。”司徒娬儿轻笑着走近,几乎要贴近的他的身后,却不担心有人,她早已将伺候的人都驱走了,此时,这座小楼的二层之上,只有她和水溶二人。
“是么。”水溶似是一笑,不无讥诮道:“本王倒是有个办法,能令公主安眠。”
他左手轻轻一抬,司徒娬儿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觉得眼前起了一层薄烟,她的视线开始便的模糊不清,身体亦是晃晃悠悠的欲倒。
两道黑影从屋檐之下掠下,若大鹏展翅一般,一人拧住司徒娬儿的一只胳膊。
水溶声音绝冷:“带回房去。”
“是,王爷。”
房门,无声的在他身后合拢,几乎是同时,将楼上最后的灯笼和灯盏尽行灭掉。黑暗中,只剩微茫的月光,水溶趁机身体一弹,足尖轻轻点过,扶栏,翻身越上屋脊,若一道白光,轻轻一晃,便消失在夜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