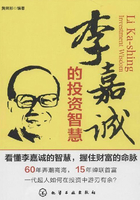过了些天,我们搬到一座大些的房子里。楼上有好几间睡房,我占了一间最小的,常阿姨也过来住了,还空着一间,我知道是给秋阿姨儿子准备的。大董和老王都住在一楼。我已经开始念三年级课本了,等下学期开学时,我想进四年级——按我的年龄应该进的班级,我可不愿意和那些比我小好多的同学坐在一个教室。所以这个夏天我好用功,一天一课地赶,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好时光——可以不做永远做不完的家务而专心念书,我怎么能不珍惜呢?这是周围人都不明白的。所有人看着我那么用功,那么拼命,又那么有成效,都暗暗吃惊。常阿姨带我去附近的一个小学参加考试,是按进四年级考的,结果我考得很好,让学校录取了。那是后来常阿姨对秋阿姨说的。说默写的二十个生词我写对了十八个,我的造句也很好,老师给了九十二分。七十分就取了。秋阿姨一听又高兴了,连说:“我说柳伢子不笨吧。这叫做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听了又高兴又不高兴,我知道我没给秋阿姨丢脸,让她高兴,我也高兴;不过我想我从来没有当过鬼。
就在我有了新书包,准备上学的时候,秋阿姨的儿子来了。那天所有人都很紧张,其中最紧张的就是秋阿姨本人。听老王叔叔说,秋阿姨的儿子刚断奶时,她爱人就被捕了,是在家里被抓走的,还把家里的人统统抓进监牢,其中就包括这个刚一岁的儿子。那天秋阿姨正好不在家,她逃脱了,可是再也没有见过儿子的面。后来听说她爱人很快被枪毙了,可是却找不回那个一岁的儿子。老王叔叔说:“那个时候,也不敢去探监啊,人家就等你去好抓你,能轻易去送死吗?不光是自己送死,还牵扯到组织呢,那会儿做地下工作可跟在前线打仗一样危险,只是现在的人只知道在战场上的人多么勇敢,哪里知道那些做地下工作的难啊!”我还第一次听说“地下工作”,它的真实含义是以后才慢慢懂的。
我没想到秋阿姨的儿子是那么高、那么大的一个男孩。他们说他有十四、五了,可是我觉得是郝叔叔走来了。我一眼就看出他是秋阿姨的儿子,因为他长得和他爸爸一个样,我对秋阿姨屋里的那张照片太熟悉了;大概除了秋阿姨,就数我看那张照片看得多。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个人也是那么帅气,那么英俊,可是他身上却少了点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只能感觉到。秋阿姨那天又高兴又着急。因为这个儿子来了既不叫妈,也不肯说一句话。陪他来的是个老农民,大董说那是孩子的爷爷,也就是郝叔叔的爸爸,秋阿姨的公公。没多一会我就听到秋阿姨在对她的公公高声说话,我听得直害怕,那声音就像那天在我们家她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话一样。听了半天才明白,原来她的这个儿子从没上过学,他是个文盲。秋阿姨气得大声斥责她的公公,怎么能不让孩子上学?那个老农民哆哆嗦嗦地说:“俺能让他吃口饱饭就不容易了,儿子没了,还盼些甚啊!”常阿姨又劝又拉,把秋阿姨压了下来。那个大男孩只肯坐在他爷爷身边,让他上楼去看他自己的房间,他也不肯。最后没办法,只好把他和他爷爷一起安顿在一楼的一间房里。
没过两天,那个老农民就回去了。秋阿姨的儿子一定要跟着走,让那个老人狠狠地训了一顿:“你都十五了,再耽误不起。爷爷管了你饭,没让你上学,爷爷心里愧着呢。别再闹腾了。跟你妈过吧,有你出头的日子。”我心想,这个老农民心里明白着呢,说的句句是实话。秋阿姨的儿子留下了。他叫郝中凌,他成了一个烫手山芋,不理人,不讲话。谁也不知道他想什么。不过我倒猜着啦,他在怨他妈。他一定在想,为什么你不早点接我出来;也许他还会想,为什么你身边会有一个小女孩。对了,他一定会这么想。我真想跑去跟他讲,我不是你妈的女儿,我是你妈捡来的一个小孤女。你要让我走,我就会走,只要你好好地跟着你妈。我知道秋阿姨现在看着和郝叔叔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心里会多么难过,怎么能让她再伤心呢?可是我该走到哪里去呢?回家?不,我不愿意回去。对了,我可以参加革命队伍,让老王叔叔和大董带我到哪个部队去,他们总有收小兵的地方。我现在认识那么多的字,我都十岁了,一定可以做好多事情。我打定了主意,睡了一个囫囵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