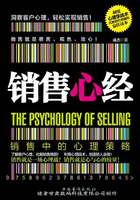人生再难,也只能面对,
两年一晃就这样过去了。
本以为之前的遭遇已然荒诞,
没想到那不过只是开始,荒诞才是我生命的男主角。
1
人生再难,也只能面对,两年一晃就这样过去了。
本以为之前的遭遇已然荒诞,没想到那不过只是开始,荒诞才是我生命的男主角。
其实想想也不奇怪,荒诞也是和世界的一种沟通方式,这世界太圣洁,需要荒诞来反衬,有人崇高,就有人苟且,而所有的不如意,说来说去,还是自己太幼稚。
我本以为可以一直在那家工厂待下去,虽然工资不高,也看不到什么前途,每天的日子都过得无比寡淡,但那里安逸,简单,可以修身养性,还有大把时间写作,也算自得其乐。
反正怎么过都是一生,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英雄。
我就喜欢做一个小人物,蝼蚁一般度过此生,有什么不好?
说起来,我还想过好好奋斗多赚钱让何诗诗出国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所以,我付出了代价,我罪有应得。
只是我如此卑微的要求都没有能够得逞。两年后,随着新任总工程师和厂长的不对付,我也被迫卷入了一场刀光剑影的人事斗争中,并且最后成为炮灰,光荣出局。
2
本来神仙打架和我这种小喽啰是没啥关系的,可是我文笔好,会写作,这在全厂近乎一半都是文盲的背景下必然显得很突出,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反正有一天我被总工程师叫到小黑屋,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他特别欣赏我,决定栽培我,但前提是要帮他先搞垮厂长。
这事放古代就是谋反,抓到是杀头的罪。可是我没法不答应,因为总工是我的直属领导,他放个屁我就得走人,为了保住饭碗,我只好铤而走险,我没的选择。
具体需要我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都要编写厂长腐败淫乱的故事。总工要拿着这些材料去董事长那里告密。厂长确实腐败,每年的利润恨不得一半都进他自己的腰包,厂长也确实淫乱,全厂三百多名女工,和他有床笫之欢的不下三分之一。这些人人都知道,但谁都没有真材实料。所以这时候我的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
在斗争的前两个月内,我写了十多万字厂长的黑历史,线索之丰富,细节之曲折,都能出本书了。总工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许诺等他当了厂长,我一定前途无量。只是好景不长,总工光顾着进攻,忘了防守,自己那些不检点的事被厂长抓到人赃并获,最后一击必中,成功将总工送了进去,然后自然是大清洗,我们这些党羽通通被扫地出门,我人生第一份工作到此为止。
回望工厂两年时光,没有赚到钱,也没有学到什么真本事,除了领悟到了职场斗争之残酷,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取名为“那时年少”,内容当然是关于我的青春我的大学,也关于何诗诗,虽然我对人生的第一段感情态度极其复杂,但除了将之写下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纪念方式。
小说边写边在网站发表,竟然积累了不少人气,到最后更是收到了一家出版社的出版邀约,这对彼时已处人生最低谷的我而言,不失为一剂强心针。
联系我的编辑姓李,是一位北京大姐。李姐水平不咋高,但人特别爱激动,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听到她在电话那头用夸张的口吻说:“小伙子,我要把你包养成第二个韩寒。”
“什么?包养!”我惊愕万分,心中顿生悲凉之意,难道这就是我们写作者的命运?罢罢罢,既来之,则安之,还是接受生活的一切安排吧。于是我温柔地回答:“谢谢,那就请你好好包养我吧。”
“没问题,包养你——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是包装你。”电话那头李姐刚反应过来,“苏扬,李姐我要把你打造成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青年作家,相信我,没问题的,李姐认识很多人,作协那帮老家伙,我都熟得很呢。”
“好好好……”我热情应允着,心想只要能给老子出书,不管包养还是包装,我都来者不拒。
第一次通电话,我们亲热交谈了两个多小时,电话的最后,李姐让我放一万个心,她会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我的小说,两个月内保证出版,随后在全国展开盛大巡回签售,接下去还要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协,明年就把我介绍到法兰克福全球书展,后年就要申报诺贝尔文学奖。
“小伙子,你就等着出名吧,哇哈哈哈……”通话的最后,李姐突然大笑起来,仿佛她刚说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3
人生的悲剧或许在于你总是把一件事想得太好,然而结局往往会很糟糕。
出书的事根本不顺利,按李姐意思,《那时年少》会在9月出版,但到了11月还悄无声息,其间我给李姐打了不下一百个电话,每次她都笃定地对我说:“快啦,快啦,再过半个月肯定出!”
每一次我都选择了相信,但事实证明每一次她都在撒谎。
12月底,小说仍然没出版。此前我已和全天下认识的人都说过我要出书了,所有人都祝福我,让我请客,并诅咒不请就是王八蛋。为此我把工作两年攒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最后当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工作赚钱,这个冬天很可能会活活饿死时,我才对出书心如止水,决定还是先好好上班。
我本以为有了两年工作经历,找份凑合的工作应该不难吧,结果好家伙,赶上毕业生越来越多,整体形势又不好,求职难度简直比刚毕业那会儿还要高,而且工作也特别不靠谱,大半年内我差不多换了四五份工作,长的不过两三个月,短的只有四五天,日子过得要多悲催就有多悲催。直到2008年2月才在一家成天嚷嚷着“今年过节不收礼”的保健品公司谋到一份文案的差事,算是暂时稳定了下来。
对于这份工作,我十分满意且珍惜,因为办公环境相当高大上,在卢湾区的一栋顶级写字楼,身边环绕的全是电视上看过的那种时尚靓丽的女白领,十米外香水味就能把你熏一跟头的那种,见面打招呼开口就是英文,特洋气有没有?
我具体要干的活儿和写作有关,就是通过软文来讴歌公司的产品有多神奇:闻了就能回到十八岁,吃一次终生不感冒,坚持服用长生不老……虽然很夸张也很low,但是并不难,身为给厂长量身定做过小说的我,对此甚至有点得心应手,说起来这也是那场职场斗争留下的政治遗产吧。
只是妾有意,郎无情,我在这家公司也不过只待了小半年——因为时下保健品市场已经进入了衰退期,早期那种靠诱惑或恐吓的营销手段早就过时了,消费者越来越理性,监管也越来越严格。老板最后见好就收,将这款给他至少赚了一百个亿的神品打包卖给了别人,自己转头去做网络游戏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部门就地解散,也就是说,我又失业啦!
而经过这一年多的折腾,我除了虚长一岁外,仿佛什么都没有获得,更别说成长了。更可怕的是,如果继续这样埋头找工作,除了试错估计不会有太多改进。虽然以前我也没有过雄心壮志,但现在前景真的堪忧。想想寒窗苦读十数载,也曾意气风发过,现在竟然被现实捶打成这样,心里还是会很失落。
我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从我个人到这个社会都有问题,但具体是什么问题,该如何改善,又说不上来,也没人告诉我。
所以,我决定干脆先放一放,既然怎么着都是不如意,还不如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安安心心再写点东西吧。
以上就是毕业后三年的故事,没有爱情,没有事业,没有幸福,没有未来,毕业了我们一无所有,听上去多少有点悲怆。
4
就是在这种境遇下,一个名叫叶子的女孩走进我的生活,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个女孩。
叶子当然不是她真实的姓名,事实上她叫什么,我一直都不知道,不过那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一起相互取暖,彼此安慰,度过了各自人生的低潮。
叶子时年二十岁,天蝎座,眼睛大大的,鼻子挺挺的,个子小小的,皮肤白白的,头发长长的,说话嗲嗲的,耳朵上有很多洞,肩胛处文了朵很大的莲花,眼神时而欲望遍布,时而空洞无物。
就是那种典型的文艺女青年。
我俩认识时,她和我一样,属于无业游民。这个身份奠定了我们能在一起消磨时光的充分必要条件。
我们相识在一次文学沙龙上,虽然我还没有出过书,但那并不妨碍别人认为我是一个作家,开始我还不好意思,后来发现其实这对别人更重要——知道吗,我一兄弟,作家,老牛×了!
我谦虚过好几次,发现根本没用,于是只好以作家自居,然后公然出入各种聚会,骗吃骗喝,感觉挺不错。
这不,当号称上海80后一哥的蒋玮玮组织午夜文学研讨会时,我自然被邀请出席——说到80后,在那个年代特指一群文学小青年,因为正赶上文学青黄不接、网络又兴起的好年代,我们这些80后,热爱写作的孩子纷纷登场,受到了远比我们实力高得多的关注。
我们本以为我们很幸福,却没想到后面要承受的苦远远大于这些收获。时也,命也,这句话真的一点都没错。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当年置身其中时,我们真以为自己可以扛起前辈传下来的大旗,并且继续猛进高歌。
而对于蒋玮玮的邀约,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主要是因为知道蒋玮玮的德行,文学只是他泡妞的遮羞布,而我们不过是助纣为虐的道具——遮羞布都算不上。
结果我不去蒋玮玮还不干了,电话里,他振振有词说这一次来真的了,不仅要研讨我国未来二十年的文学走向,还会选举出非官方作协主席,以此抗衡日趋腐朽的作协官僚机构。
“那些老家伙,早该让位了,现在是我们的天下。”蒋玮玮义愤填膺,“苏兄你必须参加,你可是80后知名作家,是我们上海文艺圈新生代的扛鼎人物,除了我就数你最牛×。你要是不来,我国未来的文学史将会有很大缺陷,为了祖国和人民,你责无旁贷。”
我看蒋玮玮把“人民的名义”都搬出来了,吓得赶紧屁滚尿流去报到。
5
和以往N次一样,那场聚会从头到尾连文学他妈的影子都没提到,全部内容只是喝酒吹牛讲黄色笑话。到场的文艺青年倒不少,二十来个男男女女将蒋玮玮那小破屋塞得满满的。绝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甚至听都没听说过,不过这些人个个看上去无比自负,鼻孔朝天,翻尽白眼,仿佛都身负盛名,不容亵渎。虽然我知道,他们其实都和我一样,只是来吃白食的。
“喝,今儿个谁不喝高,我和谁急。”酒过三巡,蒋玮玮挥舞着小胳膊,摇晃着大脑袋对所有人豪气冲天地如是说——蒋玮玮是上海人,却喜欢学北方人讲话,又学不像,真滑稽。
喝酒吃饭不是干苦力,不用动员也会全身投入,众人积极响应蒋玮玮的号召,甩开腮帮子大口吃菜,大口喝酒,完全没了文学青年的儒雅作风。不过这帮孙子看起来威猛,实则无用,没过一小时纷纷喝高,且丑态百出:主人蒋玮玮撅着屁股一个劲往桌下钻,说要爬到泰国去嫖娼;一个笔名叫无名公子的哥们喝醉后要给大伙表演钢管舞,然后脱得只剩条内裤,舌头伸出三尺长,抱着门槛一边狂舔一边猛地往上蹿,跌倒在地后干脆一个劲地打滚,边滚还边用手拍打自己白花花的肚皮,说这才是正宗肚皮舞……
我酒量尚可,加上一直感觉游离在外没豪饮,所以头脑一直很清醒。静静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突然觉得很有意思,心想这个世界真他妈病态,虚伪和丑陋充溢着生活的每个角落,社会在进步,真实和美丽却变得前所未有地脆弱。
你看这些人,平时个个衣冠楚楚,张口哲学闭口诗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知识分子,并且依仗着这层浮华的外衣到处行凶作恶,得逞后还沾沾自喜——我承认,我说的这些话多少有点刻薄,或许这些人并没有我说的那么坏,而我也不见得比他们好多少,可当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那一刻,我想到的只是腹诽和诅咒。
我一点不为自己的用心险恶感到脸红。
6
那场饭局一直到午夜两点都还没有结束,蒋玮玮成功泡到一个小粉丝,不知道躲到哪里淫乱了,剩下的也大多结双成对,女人不够男人凑。
我突然开始厌倦这样的场面,觉得反胃,于是赶紧起身离开。
门口,无名公子还在激烈地扭动着身体,表情兴奋得狰狞,他身边多了一个漂亮女孩,女孩满脸惶恐,似乎是被吓到了。无名公子跳至酣时要拉女孩的手,女孩不情不愿可是怎么也挣脱不开,只得小声哀求:“你快放开我,我害怕!”可是女孩的示弱给了对方更大的享受,他干脆直接将女孩抱了起来。如果不是旁边还有人,估计更变态的事他都做得出来。
我迟疑了会儿,上前将女孩从无名公子怀里抱了下来。
“苏扬,你他妈什么情况?”无名公子借着酒劲狠狠瞪我。
我小声说:“哥们早看上了,你别坏我好事,否则跟你没完。”
无名公子的表情瞬间又变得猥琐:“了解,了解。兄弟如手足,我找别人玩去。”说完扭着屁股到别的角落发骚了。
我轻轻对女孩说:“走吧!”
女孩似乎惊魂未定,乖巧地跟着我离开。
我们一直走出小区才停了下来,午夜的上海很冷,别有一种感觉。
“你没事吧?”
“谢谢,我很好。”女孩对我微笑,昏暗路灯的映射下,我看到女孩有着很美的一对小虎牙。
“那就好,其实……大家平时都挺好的,就是喝酒给闹的,你不要怕!”
“我一点都没怕呀,我只是觉得那些人都挺好玩的。”
女孩的话让我很惊讶,我不得不重新认真审视她,有些事是不是我先入为主,自以为是了?
那一瞬间,我情不自禁想起何诗诗,第一次遇见,我不也是这样?
女人是复杂的,狡黠的,言不由衷的,善于伪装的,怎么才过了两三年,我都忘了呢?
我情不自禁冷笑了起来:“看来,我还坏了你的好事。”
“当然没有了,苏扬,你怎么那么玻璃心?”女孩点燃一根烟,细长的520,空气中立即充满了薄荷的淡淡味道。女孩看了我一眼,“简直比我还要敏感。”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看过你写的小说啊,《那时年少》,很喜欢。”女孩认真地回答,“只因那时年少,才把未来想得太好,只因那时年少,爱把承诺说得太早。如果那个故事是真的,那么你真够可怜的。”
“全是假的!”我故作轻松,“这样的小说,我一年能写一百本。”“嗯,我也觉得是假的,都什么年代了,哪里还会有那么全心全意为爱付出的男生?”女孩说完轻叹了口气,“其实呢,真又如何?假又如何?真真假假都一样的,生活就是一场戏,早就注定了结局,我们都是戏子,只要按照既定的剧本,将这部悲喜剧演完即可。”
女孩的这些话再次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她的认知。我想其实不是女人太复杂,而是我太幼稚。
“你是干吗的?也写小说吗?”
“哈,我可写不来,我看看还差不多。”女孩嘴角飞扬,表情越发轻快,“我呀,就是一无业游民,搁家闲着呢。”
“那和我一样,同道中人。”
“我怎么能和你一样呢?你是大作家,不上班是因为不用工作。哪里像我,爹不疼娘不爱的,烦也烦死了。”
“这有什么好烦的,以后会上班很久的,现在不过忙里偷闲,及时行乐。”
女孩眼睛一下亮了起来:“这话我爱听,要不说你是大作家呢,总结得就是精辟,我想说也说不出来。”
“呵,可千万不要盲目崇拜。第一我不是作家,我连一本书都还没出过呢,其次,作家也不是什么好人,跟流氓属于同一阶级范畴,刚才你也看到了,多危险啊!可得当心点。”
女孩眉毛一扬,满脸不在乎地说:“我才不要当心呢,男人那点险恶用心我不要太熟悉啊!无所谓咯,反正我玩得起,再说了,还不知道谁玩谁呢,我什么没有经历过?”
我没再说什么,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接。唉,为什么现在的女孩一个个都仿佛历经磨难,看透人心,那些本该有的单纯和美好,都到哪里去了?
“苏扬,我发现你和他们不一样哦。”女孩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尴尬,第二次微笑着看着我,“感觉你一点都不装,这应该是一种自信吧。”
“应该不是,而是我一直认为,在女人面前伪装,是件特别可笑的事,还不如坦荡如砥,赤诚相见。”我也对女孩笑,“都说这么多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方便吗?”
“叶子。”女孩轻快地回答,“我是一棵植物哦。”
“叶子,叶子。”我轻轻咂摸,“那你很脆弱咯?”
“才不会呢,没人可以伤害我的。”叶子深吸了一口烟,然后长长吐出,11月的夜风很快就将烟雾吹得支离破碎。叶子突然大笑了两声,叫了起来,“我百毒不侵,耶……”
“真是个傻丫头。”
“嘁,你才傻呢。”叶子突然抬脚踢了我一下。
我侧身一闪,没踢到。
一辆飞驰的汽车从我们面前高速擦过,叶子的长发在空中激烈飞扬,遮住她的脸。
“不早了,回家吧。”我突然兴趣全无。
“不,我不想回家,苏扬,我们聊天吧,聊到日出时,肯定很有意思。”叶子依然一脸兴奋。
“好吧……不过聊点啥呢?”
“人生啊,文学啊,男人啊,女人啊……我们应该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你不都看透男人的险恶用心了吗?还有啥好聊的!”
“我说过啦,你和他们不一样。”叶子盯着我,认真强调。
“有啥不一样?说不定我比那些人还用心险恶呢,古人对我这种人有一个总称,叫啥呢?我想想,对,‘衣冠禽兽’,你最应该提防的就是我这种人。”
“嘁,不管,反正我现在特想和你聊天。”
“那好吧,聊就聊,聊出问题来,你可别怨我。”
“能聊出什么问题呢?”叶子似乎很好奇。
“问题可大了,比如说聊出感情,你会爱上我。”
“为什么不是你爱上我?”
“也有这个可能,嘿,不一样嘛!”
“不一样的。”
“有啥不一样?”
“我可不想再爱别人了,要是别人爱我的话,我才不在乎呢。”
“好啦,我说咱就别啰唆了,开聊吧,反正有啥后果你自负。”
“行,告诉你,我可不怕你。”
那个夜晚,我和叶子就坐在路边的护栏上,哆嗦着,依偎着,一句接一句地瞎聊天,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破晓前才说再见。
那也是我继何诗诗后,第一次和一个女孩聊那么多,让我多少有点意外的是我竟然还可以说那么多,更让我意外的是,叶子似乎还挺愿意和我说的。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和叶子聊天挺舒服,至少可以觉得在那样单调寒冷的日子里,不那么寂寞。
7
回到家已是六点多,这个城市刚刚苏醒过来,又要精神抖擞地迎来它新的一天,而我却经常在白天感到不知所措。
一点睡意都没有,肚子却突然翻江倒海地疼了起来,蒋玮玮肯定买的是打折的过期食物,加上生生冻了一夜。我冲进卫生间,趴在马桶上剧烈呕吐了起来。
刷好牙,趴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眯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肚子居然饿了,于是煮了包方便面,然后边吃边看电影。看完碟,洗好碗,坐在阳台上抽烟,眼看着街上慢慢热闹起来,小学生手拉着手蹦蹦跳跳去上课,中学生撅着屁股骑着单车飞速驶过,买菜的中年人兴高采烈向市场走去,数十名老头老太太在一块空地上翩翩起舞,放声高歌《走进新时代》。
初冬的阳光很快就懒懒地照在我身上,我接连打了几个哈欠,可还是不想睡,也完全写不出任何东西。于是把十几天积攒下来的衣服通通洗干净,还把最起码半年没擦过的地板擦了一遍,地板上面灰尘多得快能种庄稼了。如此一直忙到下午,又吃了包方便面,然后把窗户关上,把窗帘拉紧,把手机调成振动,把被子摊开,然后,自己像条过冬的小虫子钻到被子里,美美地睡了过去。
晚上七点醒过来,天已全黑,喝了两口水,水冰凉,流过喉咙时却感觉很爽,流到肚子里又感到很痛,我看了眼手机,上面有条消息:苏扬,在干吗呢?
居然是叶子发的。我想了想,不知道回什么,于是把手机塞到枕头下,接着睡觉。
夜里三点再次醒过来,这次彻底精神了,赶紧跑到电脑前写作,可依然全无状态。只得继续躺在床上看电视,一个台正在放一种能够让女性胸部迅速变大的保健品广告,一群平胸女人集体高歌从此命运大改变;另一个台更夸张,说吃了他们重振男人雄风的保健品,不痛苦,无副作用,从此床上运动一小时起;还有个台在放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我没再换台,《大话西游》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看过十来遍,但每次都还能饶有兴致地看下去,边笑边难受,没人比我更能体味热闹与荒诞背后的落寞和悲伤,无数次,我对着无尽的黑夜放声大吼:“苏扬,你看起来好像一条狗。”
看完《大话西游》已是凌晨四点半,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我心一惊,突然想起手机,赶紧从枕头下掏出来,上面又有条新消息,还是叶子发来的,写着:明天能见你吗?时间是午夜一点,三小时前。
我给叶子回消息说:什么时候见我都可以,我啥也没有,就有时间。
消息发出去没十秒钟叶子就回消息过来:几点,在哪儿见面?
她速度之快让我惊讶,我忍不住问:还没睡还是刚睡醒?
十秒后再次收到她的消息:没睡,我睡不着,黑夜让我很害怕,我总是睁着眼睛到天明。
她的回答让我有点心疼,短短、冷冷的文字表达了多少无助,只有同样失眠的人才知道。
我赶紧给她回消息,告诉她:上午九点,F大门口,不见不散。
8
离见面时间还有三四个小时呢,除了看碟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于是乱七八糟一顿瞎看,总算又耗去了不少时间。八点刚过,我简单捯饬了一番,换了身新衣服,将乱七八糟的胡须刮干净,对着镜子一看,居然感觉年轻了不少。
半小时后,我出现在F大的正门口。
邯郸路不知道是修地铁还是高架,反正乱得一塌糊涂,卡车、公交车、小轿车、三轮车、助动车、自行车无一不可怜兮兮地从F大门口那狭窄无比的小道上缓缓驶过,不时传来因剐蹭而引发的叫骂。
我走了进去,站在不远处的领袖雕像下,缩着脑袋,四处打量,心情竟然没有丝毫激动,想想当年还在上学时,每次等何诗诗时都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那个人——唉,怎么又想她了,怎么什么时候都放不下,我真恨我自己。
九点不到,叶子就出现了,远远看着她穿着一身偏运动的休闲服,围着围巾,戴着帽子,轻盈地走了过来,给人的感觉和那天夜里很是不同,我是说,现在走在阳光下的她年轻,漂亮,鲜活,完全没有半点颓废和沧桑——我喜欢这种状态,因为我做不到。
“Hi!”叶子朝我热情地挥挥手,笑容竟然有点羞涩。
“听不懂,说中文。”我白了她一眼,故意没好气地说。
“讨厌,你什么时候到的?”
“刚来。”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就在学校里面走走,里面风景挺不错的。”
“好啊,我还从没进去过呢。”叶子看起来很欢快,和我并肩走进F大。
我们从教学楼走到宿舍楼,接着走过燕园,最后来到相辉堂前面的草坪上,背靠背坐了下来。
然后谁也没说话,仿佛真的在欣赏风景。
“这学校可真大呀!”好半天,叶子突然自言自语,“可我们坐这儿干吗呢?”
“我也不知道,随便坐坐呗,反正也没其他事好做。”
“这倒也是,我在家,就经常坐着发呆,一发呆,就是一天,也不觉得无聊。”
我笑了笑,没有接话。于是我俩就那样继续背靠背,不再言语,眯着眼睛看着前方。
已近午时,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周围的风景色彩斑斓,感觉很是温馨。路上学生渐渐多了起来,三五成群,说说笑笑,去吃饭,或玩乐。在我们旁边不远处,一对情侣先是坐着窃窃私语,过了没几分钟就抱在一起卿卿我我,最后干脆躺到了草坪上,女孩趴在男孩身上,男孩一只手紧紧搂着女孩,另一只手从女孩的腿部不停抚摩到脸上,他们把草坪想象成了床,把白天想象成了黑夜,把身边最起码一百个活人想象成雕像,勇气实在可嘉。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对叶子说:“走吧。”
“好!”叶子从地上蹦了起来,接着原地轻跳了两下,抖落风尘,然后走到我面前,伸出手,把我拉了起来。
走出F大,我们又在附近的几条马路上晃荡了会儿,那些马路很干净,也很安静,弯弯曲曲看不见尽头,大大的梧桐遮盖住了马路上方的天空,路两边是便利店和面包房,传来阵阵香味。路上是一对对缓步行走的情侣,他们彼此含笑,眼中只有对方。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充满了美好和温馨。
在其中一条马路上,我买了几串羊肉串,味道很赞,卖羊肉串的新疆帅哥笑起来真的超帅。
在另外一条马路上的四川小餐馆,我们点了一份麻辣烫,吃得满头是汗,叶子伸出舌头,不停用手扇,很可爱。
吃完后我们来到一家卖女孩衣服首饰的小店,叶子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各式耳环顿时走不动道,一个接着一个试戴,她一只耳朵上得有三四个耳洞,所以比较来比较去,特别麻烦。
“苏扬,你快说,哪个更好看?”叶子噘着嘴问我,她是真有点六神无主了。
“都挺好看的。”我是真的比较不出来,而且我总是想,耳朵上打那么多洞,该多疼啊!
“那总不能都买吧。”叶子讪讪地将那些耳环放回原处,“我有选择强迫症的,要不还是算了吧。”
“怎么能算了呢?”我赶紧从中挑选出几只,然后抢着付了钱,“送给你!”
“谢谢啊!”叶子很开心,“这几只都是我最喜欢的,你眼光不错嘛!”
从店里面走出来后,感觉我和叶子的关系近了很多,过马路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拉了下她的手,她也没有拒绝。
“我们现在去哪儿呢?”叶子仰头看着我,小声问。
我鼓足勇气,微微颤抖着说:“去我那里,好吗?”
9
推开家门,叶子感慨:“真没想到你家还挺干净的。”
我顿时庆幸昨天收拾房间擦地板是多么明智的一件事。
我们都有点局促,叶子假装饶有兴致地欣赏我精心收藏的数百张电影光碟。我则坐在椅子上摇摇晃晃,不停想去洗手间。
最后还是叶子选出了一张光碟,说想看看。
那是一部十多年前的法国电影,年轻漂亮的女孩有着一个高大帅气的海员男友。一次男友出海后音信全无,女孩开始通过放纵自己以缓释悲伤,从此床上人来人往,有男人,也有女人,直到有一天以为自己终于可以重新去爱并且也找到了新欢时,旧爱却又突然出现。
这部电影我看过好几遍,主要原因就是女主角实在太漂亮,还有,电影是限制级的,里面表现灵与肉的场景很多,而且很真实,很唯美。
所以,看着看着,当屏幕上出现限制级画面时,叶子发出“咦”的一声,不过并没有表示不想看,甚至,脸都没有转过去。
就这样,一部电影看完,天已微暗。叶子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仿佛意犹未尽。
我提议再看一部,叶子表示很乐意。
于是我找了个尺度更大的,以暴力和情色闻名于世,号称世界十大禁片之一。看的时候叶子说有些害怕,于是我自然而然地坐到她身边,轻轻拥住了她。
后来,我们开始接吻,相比何诗诗,叶子更小巧——×,怎么又冒出来了,回去——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叶子骑到我的身上,我将她抱了起来,她在空中用胳膊将我的脖颈紧紧缠绕,双腿更是用力地夹着我的腰,头发垂落在我的脸上,一根又一根,一层又一层。
“等一下。”当我将叶子放到床上时,她突然推开我,“我们第一次约会就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我立即停止所有的动作,她说得也没错,尽管这种事根本没法用好和不好去评判,但强人所难,总归不可取。
“苏扬,”叶子在我身后轻唤,“不是我不愿意,只是,我觉得快了点。”
“其实,快和慢没有什么区别,结果都一样,不是吗?”我努力压抑着,确保自己的声音很平静,仿佛根本不在乎。
沉默!尴尬的沉默!
就在我快穿好衣服时,叶子突然起身拉住我,然后坚定地对我说:“你说得没错,有些事迟早都会发生,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面对。苏扬,我好冷,请抱紧我。”
10
风轻云淡后,我和叶子各自点燃一根烟,依偎着聊天。
叶子变得特别温顺,她紧紧搂住我问:“你说,我们会不会恋爱?”
“呃……不想谈这个话题。”
“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想了也白想。”
“可是,我们做爱了。”
“做爱和恋爱没有必然的关系吧!”我转过脸,实在无法看着她的眼睛如是说,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的头脑完全一片空白,只是恋爱在我心中实在太重,我根本无法轻易再承受。
“呵,也是哦。”叶子轻轻冷笑了声,“我根本不该问这么傻的问题。”
“没关系,我不会介意。”我本来是想开玩笑缓解下气氛,可说出来却又是另外一番味道,“我听说女人的灵魂是跟着身体走的,所以做爱后总归会头脑不冷静,说错一两句话实在很正常。”
“哈哈。”叶子突然大笑起来,“苏扬,你很了解女人吗?”
“还行吧。”我将浑身肌肉尽量放松,又一次无可避免地想起了何诗诗,内心深处的伤感已开始肆无忌惮地向全身蔓延。
叶子转过身,冷冷地说:“千万别太自信,你永远都无法真正了解一个女人,哪怕你们每天都在一起,哪怕她什么都给了你。”
“其实了解不了解,都没什么区别,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根本不受大脑控制。”
“你是想解释你刚才的行为吗?”
“不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觉得自己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了。
“那就什么都不要说。”叶子转身再次将我紧紧缠绕,“我也不想那么多了,只要这一刻是真实的,就很好。”
11
叶子走后,我无可避免地再次失眠了。
原来失眠虽然很煎熬,但至少还能写作,哪怕断断续续,支离破碎,也不觉得有多苦,可是那两天完全不在状态,经常是对着电脑连句完整的话都写不出,只能一根接着一根抽烟,一声接着一声长吁短叹。
叶子显然也睡不着,她不停给我发短信,文字里她显得更为坦诚,除了告诉我她很想我,还不停问明天能否再来。
看着这些消息,我陷入了深深的犹疑,我怕我会喜欢上这个女孩,更怕我不会喜欢上她。如果是前者,那么意味着我很可能又要经历一次磨难;如果是后者,那么我自己就是最可恶的那个人。除了回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真希望这个叫叶子的姑娘可以幡然醒悟,知道我根本不值得托付,哪怕只是暂时的停靠都不行,最好能够主动消失,从此互不打扰。
可是没有,尽管我一条消息都没有回,叶子还是不停地发。
我想我们都是奇怪的人,都是那么固执和坚持,又那么喜欢自欺欺人。
12
第二天一大早,我好不容易刚睡着,门铃就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一开始我装死,反正不给开门,但按门铃的人特别坚持,足足按了十分钟都没有放弃的意思。
没办法,我只得穿着裤衩去开门,门刚开,叶子就闪了进来,瞪了我一眼,说:“懒猪,都几点了还睡?”然后把手中的鸡蛋灌饼和豆浆递给我,“快吃吧,还热着呢!”
我接过,重新缩回被子里,伸着头把早饭吃了,打了个饱嗝,然后继续美美地睡觉。
叶子也不管我,先是玩了会电脑上的小游戏,然后趴在阳台的窗沿上抽烟,接着又躺在沙发上发了半天呆。看我始终不闻不问,最后干脆脱了衣服钻进我被窝,抱怨说:“我也睡会儿,真讨厌。”
她的发香让我的床变得生动起来,我们相拥而眠,一直睡到下午三点才醒过来,叶子给我煮了包泡面,我们分而食之,然后继续睡觉,晚上六点起床,我送她到公交车站。
路上我给她买了包糖炒栗子,等车时我俩合力吃掉大半包,栗子壳扔满一地,行人纷纷对我们怒目而视,我和叶子则哈哈大笑,不理不睬。车来时,叶子在我脸上重重吻了下,然后跳上车,朝我挥挥手,我则等车消失后慢悠悠回家。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