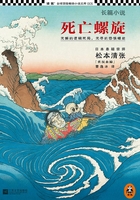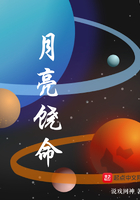年终总结会到了,市里分管领导也来参加了我们整个系统的表彰大会。会在市里大剧院召开,场面隆重,各单位发言、颁奖,等等公式化的流程进行完毕,市领导客气了一下:今天,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鼓劲的大会,欣欣向荣的大会;大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下面请问县区的同志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补充?
谁都知道,这是一句对县区表示尊重的客套话,并不是真的让县区的同志说话。本来以为到此为止了,天知道还真有“二”的!说时迟、那时快,刁爷腾腾腾地飞身跳上了主席台!“走过南、闯过北、帽子鞋子眼镜一大堆,铁道口上闯过道,火车厢里尿过尿,天下人谁不认识刁贸辉!”曾经一度在圈子里流传的有关刁爷的段子,一瞬间在人群里窃窃地传播着。此时的刁爷身着大红羽绒西服,头戴白色椭圆无沿礼帽,尖头皮鞋擦得乌光贼亮。刁爷在主席台上站定片刻,抹下帽子,朝台下挥挥手:“大家好!我很高兴参加市里的这个大会,这里也说说我们县里人的感受:市管县、不合算;吃的都是八五面、招工数字卡一半;一天到晚尽停电、下派干部到处窜;麦豆不分的管农业、拎包倒茶的当县干!工资户口都不转,招待所里住几年,白天众星捧月有人陪,夜晚酒醉裙裾觅新欢;不问干得好不好,捞它几年拔腿跑!”
刁爷到底演过戏,那喷口不亚于现在的若波儿。又加上他那一口地道的淮北乡土话,轻重缓急,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真正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曲终人散,参会的各自走开。我们的分管县长头都没回,上了乌黑的奥的,扬长而去!只有我和李小霞默默地跟在刁爷的后面,朝着汽车站急急地走。
看着刁爷凝重的脸色和目光,我小声地说:“爷,你惹祸了?”
“不就是说了几句群众都在说的话吗?爷怕谁?走,带你们去吃烧饼夹里脊!他们说假话快活,我窝在心里窝囊不快活!现在我说出来了,我快活他们不快活,我们为啥愁眉苦脸,拿别人的过失惩罚自己呢?”
这天晚上,我们没走,跟在刁爷后边在汽车站边上的大酒店唱歌跳舞疯了一晚上,刁爷疯起来真是不要命!热舞、太空步、提臀、送胯、探戈儿、恰恰;一曲《我的太阳》,高音区穿云破雾;低声部闷雷轰轰鸣响。最后都是刁爷自己买的单。
刁爷喜动不喜静,平日最怕开会。刁爷说,谁要想犯疯病,那就去听那些空洞无物的官员报告吧!看看机关里的“老太太裹脚”是怎样又臭又长的!所以每次机关开会听报告,领导在上面讲,刁爷在下面讲。刁爷百无聊赖时喜欢拿烟盒捏纸蛋子,有一次竟捏了一百多个,散会时,刁爷刚一起身,哗啦撒了一地,滚得坐椅周围一片花白。部长给局长发话:管不了他,以后不再让他参加会议了!
不开会可以,但许多具体的业务还是离不开刁爷。刁爷在圈子里混了这多年,不是白混的,人头熟,经验多,碰上棘手的事情,只有刁爷亲自出马斡旋,才能搞定。刁爷的诀窍是:脸皮薄,吃块馍;脸皮厚,吃块肉!会哭的孩子多吃奶,刁爷的经验就是放之大院而皆准的真理!
我们这个单位在大院子里属于穷单位,投入多,收益慢,一办事就得伸手要钱。地方财政基本属于吃饭财政,想挤出钱来投资社会公益事业,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局领导想汇报工作,在县里都排不上队。负责人不想见、不愿见!别的局汇报都是产值,只有我们局一汇报就是要钱。要钱难、难要钱,连县长都半开玩笑地生气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年年穷,年年窘,这个软摊子,没有硬指标,就是撑撑门面足矣!会干的,多报喜,少报忧,躲在边缘过自己的小日子,虽不富裕,但还是吃不愁,喝不愁,蛮清闲的。闹心的是:省里年年在硬件建设上搞评比。今年搞个喇叭花,明年来个芙蓉花。上边提法一条线,下边忙坏一大片。提口号的轻松无比,落实的比吃屎还难!况且一比就是一竿子到底。没法子,只好想点子拜门子,朝有钱的单位和企业伸手。那几年比较流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玉米节、高粱节、辣椒节、花生节、桃李柿子节、鸡猪牛马节等等,饮食文化、厕所文化、石文化、玉文化,还有失传多年的癫痫文化……诸多的由头邀请诸多的明星大腕,或唱或跳或说或闹,利用名人效益向社会募捐。碰上了好时机,刁爷的民间混事能力终于遇到了释放的空间。
县里决定要举办茼蒿节了。这几年茼蒿价钱看涨,县里想推出一条龙生产系统,扩大生产面积,将来把简单的粗放经营变为集约经营;把种茼蒿研发成办茼蒿罐头厂,茼蒿干菜厂,茼蒿乡村游基地,建万亩茼蒿园,办万家茼蒿连锁分厂等等。县里招商和省里不一样,各大局都要一起上。我们局由刁爷运作,具体以什么方式、请什么人全是刁爷定。刁爷请来的名人是二线歌星,连着唱了两晚上,最后一顿接待晚宴,把县里能出钱的全都请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刁爷领着歌星满桌敬酒。歌星浅尝辄止,而刁爷必须大盅满上,那满脑袋的汗粒儿,足见刁爷的热情和真诚。各单位头头都是酒精沙场蹲点的高手,频频举杯,兴趣盎然。刁爷字正腔圆,毫不退缩。坚持到最后,刁爷亮出自己的拿手好戏:独门兰花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