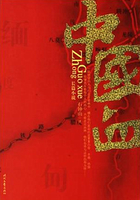月儿提着一个大竹篮从敞开的门口走进来:“食堂已经停火了,你去也是白跑。”嘴里说着,手里从竹篮里往外取东西。“做饭的师傅都去闹革命了,没有人还在厨房当保皇派。你父亲活着的时候,只要牛富贵出差去乡下收猪,我就会做几个菜过来和他‘单碗儿’。”
原来月儿的丈夫,那个屠夫叫牛富贵,真是名如其人,肥壮的身板、满脸流油的横肉,浑身处处显摆出大富大贵且牛气冲天。
陈云亮不懂怎么个“单碗儿”,傻傻地比划着问:“是要我单独端碗吗?”
月儿扑哧笑弯了腰:“我们这里‘单碗儿’就是‘欺酒’和‘干杯’的意思。”月儿用手拿酒杯往嘴前抿酒示范。
这下轮到陈云亮乐了,弄半天“单碗儿”就是喝酒干杯。“欺酒”“欺面”就是喝酒、吃饭。这个地方的方言还真有意思。
边饮边聊,陈云亮从月儿的口中知道了许多,父亲常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居住在周围的人,修修水笼头、补补锅,什么活到他手里都能做好。谁家里两口子打架扯皮都爱来找他评个理,清官断不了的事情他能断。月儿说大家还吃过他从山东带来的很香的煎饼。他的善良诚实赢得了这里居民的爱戴。
“来,单…碗儿!”
酒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月儿说唯一敢开口教训牛富贵的就是你父亲,他在这里的时候,牛富贵也知道老实一些。月儿给陈云亮的酒杯里斟满酒说,我们还知道你的小名叫亮亮,以后我就叫你亮哥哥好吗?
陈云亮好像又听见了父亲亲昵的叫声,他忍不住灌下一杯酒压住心里的酸楚,岔开话题问月儿怎么不见她去上班。月儿说工厂早就停产了,牛富贵就是“东方红”造反派的司令也到外地串联去了。仓库里如果有值钱的,哪天他们来抄家可要提早注意喔。
陈云亮的心陡然提起,不能光顾喝酒把晚上的事情耽误了,送走月儿,陈云亮开始换装。依旧是一身旧军装,背篓里装着捆扎的东西,步履沉重地朝深山走去。
接下来的时间里,陈云亮常常晨归夜出,好在与周围的人还没有怎么接触,所以也没有人好奇。
夜晚的活终于忙完了。陈云亮锁上门走出一段路,转过身回顾自己的住处和月光下的仓库,匆忙的脚步一下变得蹒跚犹豫。风声中由前面的湖边传来悲痛的哭声……这哭声很熟悉……他还没有走近,就听见扑通一声有人投水了。不好,陈云亮来不及脱衣服,不顾一切地跳下湖朝落水者游去,把昏迷的落水者救上岸,实施人工呼吸,借着月光这才看清楚是月儿。
月儿醒来,哭泣着倒出了从未对人言说过的满肚子的苦水。丈夫变态的性虐待,无休止的打骂,要命也不离婚的威胁,如今又当上了“东方红”造反派的司令,这一切让她只有去死才能解脱。
“月儿,你愿意跟我走吗?”陈云亮还没有拿定主意地问。
“去哪里?”月儿抬起泪眼,望着陈云亮。
“我也说不出是哪里,只知道那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
“只要不再见到他,我跟你走!”月儿从地上爬起来,尽管是晚上,还是很明显地看出她湿漉的衣服紧贴在身上。
陈云亮从背包里翻出自己的衣服扔给月儿换,然后走开,隐在树后把自己身上的湿衣服也换下来。陈云亮背上行李,带上身穿男儿装的月儿朝深山走去。
晨曦中,两人来到了深山中的一个岩洞。月儿疲倦地瘫坐在地上,环视四周:“亮哥哥,这段时间你就是忙着往这里搬运东西?”月儿疑惑地问道。
陈云亮忙着打开包袱,点头表示回答。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选择到这儿来生活?”月儿无法理解也找不出这样选择的理由。
陈云亮好像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他从杂物中找出斧头和锯子,告诉月儿拿上昨晚换下的湿衣服,带上水桶,去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河沟,清洗完衣服带桶水回来准备做饭用。他要去伐树。月儿拿上衣服水桶跟在陈云亮的身后走出了山洞。
这个冬天特别暖和,眼看就要到年关了,山里的树木还全是一水的绿。月儿在清澈的溪水边清洗着衣服,眼睛四处打量着周围的景色。这是一个狭长的山谷,山洞就在山谷中间的半山腰上,不熟悉的人看不见洞口,它巧妙地被厚厚的绿色植被遮掩着。亮哥哥的选择显然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他早就做好了准备,那条用锄头挖过,石板铺垫的通向山洞的路说明了这一切,自己只不过是恰巧在死神面前被他拉回到这里来的。
月儿提着一桶水晃荡着回到洞里,陈云亮已经扛着第一捆木材回来开始搭建木床。月儿把洗好的衣服晾好,在石头垒砌的简易灶台里把已经风干的枯枝点燃,将潮湿的先塞在两旁烘烤着。不一会儿树枝燃烧的炊烟让山洞里飘荡出了些许温馨。
晚上躺在被窝里,月儿把昨夜到今天的经历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昨天牛富贵回来时又是喝得醉熏熏的……不去想,想到他那丑恶的嘴脸,那双邪恶的熊掌,月儿就感到腹部痉挛,手心冰凉,一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等待宰割的柔弱控制了全部的身心……
迷糊中,月儿看见父亲抱着家里仅剩的被褥往外走要拿去换酒喝。没有了被褥,冬天怎么过啊!月儿是吃百家食长大的,衣服薄可以钻到被窝里,可是哪里还有被窝呢?月儿伤心地哭泣着从一个高坡上跌落下来,把自己吓醒了。
睁开眼睛半天才醒悟是在做梦,四下里看看,外面已经天亮了。月儿起身穿衣,轻轻移动脚步,开始张罗着做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