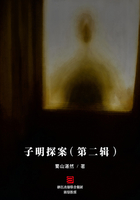对多宝来说,仙岩街是他第一个向往的远方。
每隔五天就一个集市,村里的人都要沿着溪坑边的小路去仙岩街赶集。一路上都是人,并且都是挑着可以卖的东西,几只竹篮或一担洋芋,几斤苎线或一担小鸡,一篮鸡子或一担劈柴。大家都很开心,脚步矫健,有说有笑。贩牛人赶着一头牛,去镇上卖掉,改天又去外县的集市买回一头。各村的脚踏车(自行车)都出来了,骄傲地不断打着铃声,风一样地从路人身边呼啸而过,让步行的人羡慕。有些村庄还有拖拉机,载着满满一车人风驰电掣地经过,让步行的人神往。
到了街上,人流正不断从四向八面各个路口汇聚而来,马路上也挤满了人,汽车凶猛地叫着,阳光似乎都被惊得非常纷乱。人们弯进鹅卵石光滑发亮的老街,街上挤满了人,就好像涨满了洪水的溪坑。妈妈拉着多宝的手,或者多宝拉着爸爸的衣服,跟着他们往前走,大人见到要买的东西就问一下价钱,讨价还价的声音不断,见到亲眷或者熟人了就大声打招呼或停到边上互相询问一番。多宝闻到了咸鱼干刺鼻的腥味,看到了簇新的锄头、菜刀,还没用过看上去木乎乎的,看到没有脚的人坐在一个轮盘车上,整个人扑在地上,手里拿着一个洋铁盆讨钱,看到算命先生一溜儿在街角坐着,其中有两个还到过山根陈村的。这一切在多宝眼里都那么新鲜,那么让人好奇和开心。多宝还看见自己的爷爷在一户人家门前坐着卖生姜,悠闲地抽着老烟,和边上的卖东西老头聊着天,和买的人讨价还价。多宝走了过去兴奋地喊爷爷,爷爷给了他五分钱,说让他去买根油条吃。挤挤挪挪地走到头,他妈妈买了几个洋葱,几斤海带,几斤咸鱼干。
妈妈再带他去参观供销社。供销社没有街上热闹,但比街上洋气,这里卖的都是城市里生产的东西。妈妈如果要问什么东西,就好声好气地先叫声:“喂,同志。”夏天的时候,供销社里的吊扇呼呼转动,很洋气、很凉快。妈妈小心地指给他看里面的各种高级东西:上海手表、上海踏脚车(自行车)、上海糖、新毛巾、新手电筒。他看到各种各样的布,各种各样吃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连环画,每样东西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
爷爷给他买油条的五分钱他花了三分钱,买了一粒钢珠回去可以做陀螺,买了两粒糖,自己一粒,另一粒带回去给妹妹吃。
街上没亲戚的人要赶回家吃中饭了。回家的时候人们都像看戏回来,有点累了,懒洋洋地往回走,但作为孩子,则仍旧一边走一边非常满足地回味着街上的一切。
仙岩街其实也就是一个大村庄,但公社在他们村上,每个村都属于公社管的。如果说整个公社是一棵树,那么仙岩街就是树桩,其他村就是树枝,每个家是树上的小树枝,每个人就是树上的一片叶子,大家就这样生活在同一棵树上。每到集市,叶子们都集中到树桩。
差那么五里路,人的口音就不一样,脸上的神情就显得开阔多了。街上的人,即使没钱,每天也可以闻到油条的香味,看到油条那金灿灿的样子。每天都可以看到汽车,这些汽车可都是每天从上海、宁波、临海、温州过来的,世面见得多了。村里的信息来自仙岩街,就是比仙岩街更远的信息也要先传到仙岩街再传到村里。就像一部电影,必然先县城再到仙岩街,再从外面到里面一村一村放进来。一首新歌、毛线的一种新花样、一个新的笑话,都是从仙岩街传进来的。村里谁长得漂亮,也要以仙岩人的评判为标准。
村里人很把集市当回事,街上的很多人倒本来干吗的继续干吗,那一天照样有人担粪上山干农活。按多宝爷爷的说法是,“山村里也有员外,街上也有穷人。”但街上的人却说,“你山上员外不如我洋下扫街。”读过初中的叔叔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他说:“人生哪个地方是注好的,生的不是好地方,生的不是好人家,那么你一辈子就是苦的命。”
更多的时候,爸爸妈妈去赶集了,多宝就在家里等他们回来,等到快要到中午了,就跑到村口的大樟树下等,一直等到他们回来,看看他们到底买来什么好吃的或者好玩的东西。他们总是给多宝带来一粒糖或者几只小麦李。
有时候妈妈跟多宝说:“今天买的是好东西,到家里再给你。”
多宝一路上问:“什么好东西?让我看看。”
妈妈就是不告诉他,还带着一脸神秘。
终于到了家里,妈妈说:“你准备好了?拿住啊。”
多宝用力挽开妈妈的手,里面什么都没有。
多宝还以为妈妈在捉迷藏,继续问:“妈妈,东西在哪里?”
妈妈说:“好东西给你了,它叫‘捉不住’。”
多宝知道上当了,就大哭。哭久了,爸爸就烦了,他说:“你再哭我就给你‘五瓣栗’吃。”于是,多宝就停下哭泣,他才不要吃五瓣栗呢,不就是拳头钉吗?
大人们总要骗小孩子,但小孩子的注意力就被这些神秘的说法迷住,忘记了失落。
村庄前面的溪坑水一直流到仙岩街,一路上汇集各山各村的溪坑水,在仙岩街那里汇集成大溪坑。这条溪坑一直流到海东县城,再流到大海洋。多宝有点羡慕溪坑里的水,甚至羡慕小河里的鱼,能顺水而下,一直游到县城。村里就有童谣唱去县城的一些地点:“老倌头,卖猪头,卖到岭口歇一歇,卖到海东吃馒头。”
多宝经常思考:外婆为什么不是仙岩街上的人呢?否则就可以去街上住几天。他就希望姑妈嫁到仙岩,希望几位姐姐快点长大,嫁到仙岩去,这样,他就有街上的亲戚了。有一个街上卖豆腐的人,妈妈说她本来也是山根陈村人,但多宝看她不像是山根陈村的。嫁到街里就变成了街里的人,走路就慢起来了,对一些狗屁小事情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多宝爷爷有一个姐姐,他叫姑婆,嫁在外村。他姑婆有一个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宁波做官。因为有宁波亲戚,全家就觉得比村里人活得通气。爷爷讲起宁波,神情总是很满足。多宝经常问爷爷:“宁波有山吗?宁波人每天看电影吗?宁波人的菜是谁种的?宁波城要几天才能走出头?听说宁波人不用挑水,水直接流到家里的水缸里?”
宁波对多宝来说,还有更特别的含义。奶奶告诉多宝:“你宁波姑婆年纪很大了还没有孩子,就去多宝寺拜佛求子,结果有了你表叔,他就叫胡世宝。你妈妈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我就去多宝寺拜佛,你是我在多宝寺拜佛求来的,就叫多宝。两个都是多宝寺送的宝贝,希望你也像世宝表叔一样考上大学,将来到大城市去做大官。”
在多宝的心里,最美好的还不是仙岩街,不是宁波,而是北京天安门。如果什么时候能去北京天安门,那就是神仙了,那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他只能从两个地方看到北京,一个是他经常出差的大叔叔的那只手提袋上,还有就是他堂弟的一张照相里,堂弟站在天安门城楼前,是在仙岩街照相馆里拍的。
多宝还很想去的是南京长江大桥,两角钱钞票上印着的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他床上的木板壁上贴着一幅画,画的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他每天一睁开眼睛就看到画上的雄伟的桥头,他很喜欢桥头上红色的火炬。他盼望长大,盼望长大后去很远的地方,看很好玩的世界。
老百晓好像从来不赶集。他要卖的草药、劈柴都托聪明人带去卖。他要买的烟酒、种子都叫聪明人给带回来。
多宝问他:“百晓公,为什么从来不去赶集?”
他说:“我不像你小孩子,那么想去仙岩街,我哪里没去过?仙岩街不就是人多、房多?你没钱,供销社的东西也不会自己进你的家,没意思。”
最后他感慨道:“走过四向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走遍天下,不如山根陈樟树脚下,我是哪里也不想去了。”
后来,他确实哪里也没去,也去不了了,因为他去了坟山。这个人就是死亡也搞得像他讲的大话。死之前,他先到生产队算来工资,然后到道士那里挑好出丧的日子,在抬棺材的伕子那里付好钱,余钱都交给聪明人,让聪明人负责他的后事。棺材是十年前就做好了的。然后,他自己把自己吊死在家里。抬棺材的人按照他说的时间来到他家,他果然已经死了。多宝听他奶奶说,吊死的样子可不好看,口舌吐得长长的,就像他以前描述过的吊死鬼的模样。
他出丧的那个晚上,多宝梦见了他。他经过多宝身边,准备去山上望山,多宝问他:“百晓公,你为何要自己死掉?”
他说:“鬼生了很多小鬼,小鬼们也想听我讲大话啊。”
然后多宝看见老百晓会飞了,一闪就闪到山顶,山顶上他一辈子养过的所有狗的鬼魂一起背着他飞起来,就像一朵云。他还向多宝挥了挥手,跟多宝说:“小鬼,我要到天安门赶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