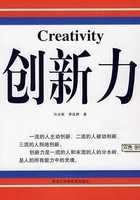王龙山感到意外的是。第二天,李培堂他们一个都没上乡井来推煤炭去卖。他以为过两天就会来的。他对他们的经济状况摸得清清楚楚,这些人如果一天不出工,家里人就得饿一天肚子。
第五天。李培堂来了,与他同来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尚武,尽管他穿了矿警服王龙山还是认识。另一个头戴草帽,个子清瘦,王龙山也认识,他是安源地下工会袁主任。王龙山奇怪了?袁主任开门见山说:“王掌柜,我们是来讨公道的。”
王龙山当然明白他说的公道,心里不高兴,嘴上不便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从内心怕工会的人把事情放大,他毕竞是小业主,不能跟安源矿局相比。他们很快谈妥,李培堂四个人煤款按百分之五十结算,因为煤款全让当兵的掠去,路上又耽误几天时间,各自承担一部分费用,利息全免。李培堂说:“我把自家烧煤卖了,不还你的钱,我难受,从现在开始,我们两清了。”王龙山说:“老李呀,我只是说说而已,那要你还三分利。希望你继续推煤去卖,跟此前一个样,卖了煤后再付款。”
李培堂说他知道了。路上跟侄子和袁主任分手后,遇上姚、张俩伙计也来还煤钱,他们学李培堂的样,将自家的烧煤推出去卖了变钱还帐。
王龙山煤场上的煤堆成小山似的。至今没买主上门要煤,最让人头痛。他托人四处活动,第一个目标盯准矿上的销售股宋得一股长。按约定,他叫儿子王柳生在明月楼宴请宋股长。要出门应酬,他让姨太太吴秀玲把他的白绸缎短袖衫和蓝绸缎宽松裤找出来,又让姨太太帮他梳理一下头发,脚上换上特意从上海买回的黑皮鞋。这样的装束,跟他上乡井时,穿的普通长衫袍布鞋相比,判若两人。除了那张脸和稀疏的头发,能显出人的老态外,是个典型的满腹学问的生意人。
明月酒楼在安源大街东头,安源河离它只有50米远,下暴雨时,河水会漫过不高的堤岸。在靠河边的一端,砌了一排麻石挡水。酒楼临街的一面是敞开式的大厅屋,一次可容纳十桌客人的宴席。门、门坊、窗口格都雕着那种古老的兽花纹,而不是另一种花纹。有人说,这一带原来是乱坟岗,原来的房东以兽花纹来压邪气。王龙山购买这座房子,已是几易其主。这里取名叫明月楼,是因为二楼原是摆香案,烧香拜月的地方。现在除了一间专门供香火外。还有三间房定为包间,是宴请贵客的地方。
王柳生早给厨房下了菜单。王龙山到明月楼时,儿子和宋股长都不在。酒楼总管过来见过老爷,总管是个三十岁的年青人,见了王龙山不知说什么话,很别扭很拘谨。王龙山不难为他,说你下去吧,等客人一来,你安排上菜就行了。
倪狗儿在楼梯口守着,客人来了好通风报信。
王龙山无心闲坐,站在包间窗台前。这里是个好地方,可以把安源大部分地方景致收入眼底。从安源河看过去就是铁路,过了铁路看见的盛公祠,一座德式建筑耸立在山上。山下是矿局所在地公事房,再过去是总平巷,洗煤厂。每当他站在这里看时,总会产生一些遥远的回想。他父亲王吉义是光绪二十一年到萍乡的,最初在萍乡北正街开家杂货铺,生意一般。萍乡煤矿开埠后,王吉义盯住矿上木材生意,他从赣西湘东山里贩运木材。十年不到,赚个钵盈满贯。在城里和矿区连开几家店面。谁料想1906年12月,萍浏礼同盟会反清起义,萍乡成了主战埸。清政府出动五万兵丁来镇压,战事月余,杀人过万,血流成河。城镇凋落,商铺十之毁七八。其父一病不起,撒手人间。
那时,他二十五岁,因他生性风流,不务正业,每日酒足饭饱,根本不懂生意。多亏他有个办事利落,颇有主见的内人黄氏相帮,生意才逐步上正道。二十多年来,他的商业矿业生意,远胜其父。基本上也算个风声水起式的人物了。
然而,大千世界,繁杂曲折。这一生中有两件事让他震动很大。1905年5月当时德国监工随意克扣矿工工资。民众激怒,暴打德国人。再一件是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沸沸扬扬,惊奇于世,让他不得小视工人的力量。这几年中国发生的许多事,让他迷茫不知所措。按说他是个商人,不问政治不谈国事,而身边发生的哪件事不是以政治的国家的面貌出现呢?
前年,安源操场上北洋军阀杀害工人领袖黄静源;去年,北伐军进入萍乡;今年,上海“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今年五月,十万工农围攻长沙。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每一件事情的出现,对商人利益都是极大的打击,处在这个动荡的时期,也是商人的悲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的胆小慎微了。安源远不是十年前的安源,工会组织一直在安源半公开活动,工人学会保护自己,任何跟工人有利害关系的事,往往工会出面。还有地方上的洪帮会、清帮会,天主教会,各种形形色色的帮会派系组织,打着为帮内人谋利的旗号充沛市面。他学着跟各类人打交道,按时发饷给点福利,送保护费。去年北伐军进驻萍乡,工会查封推毁游斗一些商铺时。他反而受到保护,说他是开明人士,他现在是萍乡商会付会长。这乱纷纷的世道中,要想做一个成功商人大难了,你得学会生存。以他家办的煤井为例,这段时期煤炭销路不好,井是他儿子办的。儿子望着卖不出的煤炭发急,特意要他找他的老熟人宋股长出面,帮着销点煤炭。萍矿毕竟是棵大树,销路好时,大量收购煤炭。宋股长成了各个乡井窑主的香喷喷,现在是销煤旺季,他希望早点联系这棵大树,做到处事不惊。倪狗儿来报,说客人来了。
这顿饭下来,他们谈得很融洽,双方的利益摆在那。宋得一那有不接捧的道理。不过,快四十岁的宋得一在接棒时,提了个要求。他最近跟婆娘闹矛盾,原来他在外养得一个女子被婆娘发现了。他想找个地方先将女子安顿一下。他说,他这个女人怀孕了,他想叫她生个儿子,他至今生有三个女儿,他不想断了宋家的香火。王龙山满口答应,不就是找个住的房子吗?他有。分手时,他拜托他在销路上想想办法,宋得一满口应承,跟他向他保证的那样。
楼上留下父子俩。王龙山对儿子说,我总感到这顿酒席白请了。儿子问怎么会呢?你们都是老朋友了,他做不倒的事,还会骗你不成?王龙山说,你没看到他那双眼睛,他的眼神在应承时,总给一种漂浮不定的感觉,他以前可不是这样。他交代儿子,答应的事你先给他办,把五福巷的那间屋子捡拾一下,让他的女人住过去。煤炭销路上的事,要两头抓,你抽空去醴陵,那边瓷厂多,把去年的客户再接起来。王柳生说他知道了。
送走父亲,王柳生这才松口气。办公地点是楼下左侧的一间偏房,房子不临街,窗台也小,进屋光线不好,显得有点暗。他本想开个窗户,但后墙紧靠邻居后墙,只好放弃开窗想法。酒楼总管在等他。
“少爷,不好了,出事了。”总管说。
“出什么事?”王柳生问。
“冯三接货的船在隘口冲关,船翻人落水,淹死一个,货全部掉水里。”
王柳生一听,“冯三他人呢?”
“在五福巷瓦屋等你,死的人是他老弟,现尸体还没运回。”总管说。
王柳生感到恼怒,好端端的人,怎么说死就死了。他交代总管,要他妥善处理这事,多给总管点钱。冯三货没搞回,要他记好翻船地点。他会安排人去捞货。他说,如果安源缺货,要从萍乡运点货过来。他所说的货,是政府明文禁止的烟土。他秘密做地下烟土生意,连他父亲都不知道。他父亲反对他做这些生意。然而,这烟土生意因为有暴利。萍乡不产烟土,所有的烟土都是从云贵经湖南过来的。这次他进货比较多,动用了煤井和酒楼的流动资金。本以为过一下手,就能够收回现金,没想出了这档事,把他急坏了。他怕夜长梦多,连夜带人上老关去了,冯三自然跟去。
在萍乡产业中,王龙山安源占有一半资产。除小煤窑、酒楼外,还有两家布店。另外他合股跟人办了家土焦厂。直觉告诉他,富人敛财,跟穷人敛财的方法不一样,但欲望是一样的。安源存在着某种暗物质,嘈杂纷乱仅存在于表面,其实质的内容却是很残酷的。前些日子,儿子王柳生回湖南乡下外婆家,给老人做70大寿,给他带回的消息是湖南乡下极不稳定,农会活动频繁。他一直琢磨一个问题,但总琢磨不透,就是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希望了解什么?
从新老街口处,进了一条胡同,在胡同的中间位置,有一栋坐北朝南的大屋。青砖灰瓦,两扇大门降紫红色,青石门框,一边有一只挂铃小狮子把门。屋檐桃瓦,两个小窗户是大理石缕花而成,是典型的赣西建筑风格,大屋是王龙山十五年前建的。二进七舍,一个天井,两眼水井。前些年,他有翻修房子的念头,由于姨太太吴秀玲反对,他放弃了。这栋大屋本来就是为吴秀玲做的,吴秀玲不让翻修。她说她对这屋子产生了感情,一切都熟悉了,看了舒心,他依了她。王龙山进门时,看门的许老倌子告诉他,在外疯了半个月的小丝婷回来了。“啊!她还舍得回来。”王龙山笑道。
听到他的声音,吴姨太从客厅迎出来,她素色细叶斜襟短袖上衣,深色绸缎裤,脚上一双女式布鞋。她容颜娇媚,体态均匀。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头胎生得儿子,是王家老二,取名叫王丝宇,今年十七岁,现在广州读书。小丝婷是她生的女儿,也是王家唯一的女儿。
“回来了,没喝多吧?”
“还好!”
吴姨太叫佣人泡茶给老爷。王龙山问女儿呢?吴姨太说她吃过中饭睡了,这回到乡下玩疯了,还跟表姑跑到长沙。人瘦了倒长得更精神了。看得出,吴姨太对女儿的爱是溢于言表的。王龙山说洗个澡,身上粘糊糊的不舒服。
吴姨太忙叫厨房林妈给老爷打热水。又唤莲儿叫她备好老爷的换洗衣服。莲儿是她老家远房亲戚的女儿,来她身边帮她打理内勤的。莲儿备衣过来,她又要莲儿去把丝婷叫醒,说下午睡得大久,晚上又不想睡。莲儿去了。吴姨太拿起桌上蒲扇扇风。小丝婷揉着眼睛来到厅屋:“娘、我还想睡。”
“别睡了,你爹回来了,他要考考你。”
小丝婷听说爹回来,精神来了。莲儿用毛巾给她洗过脸。
“娘,爹考我什么?”
“我哪知道。”吴姨太说,“赶紧把你的作业做完,再过几天开学了。”
“我会的。”小丝婷八岁,二年级学生。说到暑假作业,她心里不高兴。
洗过澡的王龙山,在厅屋门口见了女儿很高兴。“你怎么黑得像挖煤人?”
“没有哇?”小丝婷看看手臂摸摸脸。没感到自己变得跟下井炭估佬一样黑。她发现是父亲骗她。“爹,你不是说,派人接我,怎么没人接我?”
王龙山笑着说,这是考考女儿出外办事走路能力,女儿能平安回来,证明考试及格。他问女儿到过什么地方?小丝婷说到长沙火宫店吃臭豆腐,到城隍庙烧过香,到岳麓山爬山,在湘江上划过船。说到最后,她从脖颈上摸出一块丝线吊着十分精致的玛瑙玉佩给父亲看,这是一尊观音菩萨宝莲坐像挂饰。她说:“这是外婆送的礼物。外婆说,菩萨可以帮人消灾,保人长命。”
女儿的话,惹得王龙山开怀大笑。王龙山视女儿为掌上明珠。他是安源少有的几个商界中将女儿送进学校读书的人,他不媚外不陈腐。这与他几十年生存环境有关。二十世纪初的萍乡煤矿,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大工业设备,发电厂、洗煤机、鼓风机、锅炉、水泵、铁路、火车,而且设备都是从德国、日本进口的,他甚至还跟各式受过西学教育的国人或洋人打过交道,交往多了,视野开阔,心情豁达,人也变得大度、宽容、勤奋、狡黠了。王龙山对女儿有一个美好的设想,这设想他是从另一个女性身上感悟出的。
几年前,安源路矿工人夜校来了一个叫何宝珍的女先生。年青美丽,学识渊博。他听过她的课,被她博览群书通俗易懂的书生意气,和女性文尔雅致气质所折服。在当时,他就想到自己的女儿,他尽管不同意何先生的某些观点,但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有志向有知识的人,是他早酝酿好的计划,女儿现在大小,如果长大了他会将她送出去。
“丝婷,听你娘说,你还有十天开学,作业还有一半没完成,爹可对你有意见。玩可以玩,但你每天订的计划必须每天完成。”
小丝婷噘着小嘴。王龙山说:“明天开始,每天做了作业才能玩。”
道口被火车堵住,蒸汽机头吐着白烟,轰隆隆的串过铁路道口。司机半个身子伸出机车窗口,眼睛盯着前方。攀在车厢边的信号员,一手抓环,双脚踏在铁环上,斜着身子,镇静自如地举着小旗。当他手中的小红旗上下挥动后,刹车声响起,只见火车咣咣的停了下来。于此同时,站在道口两侧的行人,不待火车停稳,呼啦的上了铁路。行人自顾自得,不时用眼扫一下喘着粗气的黑机头。行人也不管它,紧走慢走的下了铁路。汽笛再次响起,机头突突的吐着白烟,火车又轰隆隆的开过来。
李尚明和他的伙计被堵在道口边。这回堵路的时间可长,火车头将车厢送到洗煤台下,煤仓下有六个出煤口,火车要将一个个空车厢装满煤,才会让开道。有人不想等了,想从车厢接头处钻过去。
立即被铁路工人喊住。“不要命了,不能过。”
李尚明也不想等,三人沿铁路往西边货场走去。装满煤的车厢不断地从车厢缝里往外淌着煤浆水。煤浆水溅在路基上,水被路基上的石子吸收了。煤留在了石子的表面,这是很好的煤,太阳晒干了,会被捡煤渣的孩子拾走。他们走到人工卸货车场,远远的看见有四个车厢上堆满了麻袋,其中两个车厢有工人卸货。
有人喝住。“哎,干什么?”
他们站住看着货场。
雪苟说:“在卸大米。”
“要是偷一袋米,可比偷煤划得来。”叶炳杰轻声说。
这玩笑很受用。偷米跟偷煤受得处罚都不一样,他们没心情往回走。
远远的路基上,出现一群捡煤的孩子,男孩女孩都有。李尚明见两个熟悉的小身影。“雪苟,你看!你老妹跟我老妹在捡煤渣,还一股劲的抢。”雪苟想叫住妹妹,叶炳杰说:“你叫什么?让她们捡,如果你有呷得,就叫她们过来。”
李尚明说:“走吧,她们有她们的事,我们有我们的事。”喻雪苟还是喊他妹妹,要妹妹带着红玲到煤矸山去捡煤,这里有火车大危险。雪香说:“我马上回去。”两个蓬头散发的小女孩,挎着小竹篮跑走了。
“两个癫婆子样。”雪苟说。
几个人离开铁路,乘无人在巷口撒泡尿,出了巷口,来到堆放许多原木的木材厂。木材分等级大小码在一起,天热不见一个人。李尚明站在场中央,从口袋表掏出一块光洋。这是他们几个人卖煤后,攒的零钱。他们商量如何花这块钱,三分之一分了,三分之一花了,再拿三分之一去赌场碰碰运气。铁路道口,石鼓说既然去买东西吃,把两个癫婆子找来,让她们也饱饱口福。于是几个人又去找他们的老妹。很快,两个小妹在总平巷前露面了,听说叫吃东西,兴奋极了。石鼓要她俩洗洗手,“把头发用水拢一拢,别像癫婆子样。”
雪香说:“不许骂人,这是做事,不是去逛街。”
“现在逛街。”叶炳杰说。女孩在水沟边洗过手,又将头发拢好。
石鼓要她俩找个地方把蓝子藏好,吃了东西再回来取。
中午,安源大街上百货和杂货店铺冷静了。没回家的人,都挤到饭店酒楼小吃店。他们五人进过馆子店,吃什么?上哪家店?最终他们选了这家只有两张桌子的小店。坐下才知道是家面店。店家看是小孩,不想让他们走,说可以烧菜,不过慢一点,看他点什么菜,随时准备也来的及。石鼓问大家吃什么?有的要吃肉,有的要吃鸡。店家说要不你们一人点一个菜,挑最喜欢吃的。这样他们点了鸡、肉、猪肚、牛肉四个菜。石鼓点了炒黄鳝,都没点疏菜。这顿饭吃下来,一算帐吃了三吊钱。几个人吓一跳,每吊钱十五个毫子,可以买一担米。石鼓掏出光洋,让店家找钱,店家跑了两个店才把找得零钱凑齐了,找回375个毫子。红玲和雪香眼睛都直了。在一个糖果饼干店,石鼓买了两斤糖果分给大家。
河边槐树下,叶炳杰、雪苟石鼓各分75个毫子,红玲、雪香各二十个毫子。拿下30个毫子下次用。还有75个毫子准备上赌场玩。炳杰说这是拜师钱,输赢都不算。雪香反对去赌博,说如果去赌博,她会告诉大人,红玲也称赞。
“不赌就不赌,回去捡煤,妹子也回去捡煤。”石鼓说着跟伙伴使眼色,众人往回走。在铁路道口石鼓按着肚子,说他要去解大手。炳杰、雪苟也说解手,要妹子先走,他们去去就来。等两小姑娘过了铁路。三个小子抽身往九十间房跑去,那里有安源大赌场南庆堂。
南庆堂是座赣西民居格式大屋,三进三厅两个天井十八间房。公开露面的老板姓廖,暗中有两大人撑腰。一为县署局长刘富,一为清帮头目傅德诚。这里小赌天天有。无论小赌大赌都是赌场的客人。远的赌客可涉及长沙、南昌,出手大方,动辄几万十几万一盘的赌资。令人目瞪口呆,大呼过瘾。在大门口被人拦住,看门的汉子问干什么?
“我们来下注的。”石鼓说。
“毛头小子下什么注,回家抱孩子去吧,这是你们来的地方吗?”汉子凶道。
石鼓还想说什么?被汉子赶下台阶。巷子口有一个摆地摊的赌盘,吸引了他们的眼球。石鼓说,既然要赌在哪都一样,玩转盘弹子也是赌。不妙的是,不到半个小时,约定的赌钱全部输光。石鼓还想把分给自己的75个毫子拿去赌。被炳杰拦住,说明天再说。但他还是放了20个毫子进去,没几分钟又输了。这天晚上,三个人都在家跪了搓衣板。是妹子告的密,石鼓挨打最重,父亲用扁担打的,屁股几天都不能落凳。母亲埋怨丈夫打儿子大狠,也埋怨儿子不听话,母亲用药酒给儿子擦伤口,石鼓感到有一滴热泪落在屁股上。
几天后,李培堂要出一趟远门,目的地又是万载县。李培堂很不放心婆娘临产的身子,愈近产前,愈让他担忧。本来只做些附近的活,好照看家里,想着家中的困境,他还是想抓紧时间把这趟活打理好。
李培堂对婆娘说:“我出去这几天,你好好照顾自己,别累着。有事让石鼓、红玲兄妹帮着做,要不将母亲接来照看你?”
“我没事,有孩子在家帮着,娘家也有事,弟媳要生了,比我早,就在这几天内。再说,你出去也就几天时间,我能照顾自己。”
“石鼓还在生我的气吧?老大不小,你有事叫他去做,别什么都护着他。”李培堂叹口气,“明早出门时,还得说他几句。”
“你用扁担打他,下手大狠。屁股现在都是痛的。”周氏说。
第二天大早。周氏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叫丈夫吃饭。拿出丈夫昨晚织的五双草鞋包好,又将路上的中饭装在竹筒里。竹筒有碗口粗,竹节八寸长,去了外皮的竹筒呈黄色。推脚人出门常用它途中备饭用。随后周氏用汗巾扎个包。李培堂饭后喝口水,提着包上井口去。
昨晚装好煤,这趟出门八部土车,全是王龙山的煤炭。赶到高坑时,还不到九点钟,小歇后一路往宜春大路上去。谁知张水生的土车出了芦溪不远,车轴出了毛病。李培堂等人帮他卸下煤筐,张水生推着土车到镇上修好车轴。一来一去,两个小时过去,把大家早起赶的时间给耽误了,赶到宣风,天已经黑了。姚景云忙了晚饭,各自拿出自带的番薯酒,痛快的喝了几口。走一天路,累了睡得早。不过,李培堂却无法入睡,说来说去,还是家里的事不放心,又没办法改变它,他叹了口气。“还没睡着?”
躺在旁边的姚景云也没睡着,他问:“还在想什么?”
“有点心烦意乱,想睡,睡不着。”
姚景云理解这个伙计的话。“也难怪,婆娘要生了,你却在路上赚吃,根本无心做事,只能怪我们命苦,反过来想既然是受苦的命,不求发财,但求平安。”
“我们相识有十二年了吧?”他问姚景云。
“对,十二年差三个月,真快。”姚景云说。他们曾是矿上的工友,多年前一次井下事故,他俩死里逃生。从此,干起推脚炭的活来养家糊口,他们怕下井,说起下井的话题,是辛酸和苦涩的,他们极少提起那时的往事。
“你怎么想起这事?”姚景云问。
“我在想,人在世上没多久,一转眼都四十岁的人了。”李培堂说。
“我记得你说过你是萍乡彭高人,老家还有不少亲戚吧?我是排上人,你记得吗?我有十年没回去了,去年老家续谱,我没回去只是交了点钱,我总认为,这续谱没什么意义。”
“话不能这么说,我也是两年前续的谱,还把儿子带回去,让他看看老家是个啥样。听听老年人说点古话,我们家族好大的,只是后来跟陈姓一族争水,打了十年官司,山田耗光了。陈家最后买通官家,最终我们败了。从此,上辈人纷纷背井离乡,出外谋生,这是同治年的事。”
“穷人就怕打官司,越打越穷。这次出门,不会再遇上倒霉事?上次差点跟王龙山打官司。不打官司也白干半年,要不是你的点子,还在白忙活。”
鼾声此伏彼起,张水生的鼾声最大,有人说着梦话,还有一个磨牙齿。姚景云磕睡上来了。李培堂起床小解,将薰蚊子的烟火往外移了移,躺下也慢慢睡了。李培堂起床后,感到不舒服,以为昨晚没睡好,吃过早饭,众人纷纷上路,他让姚景云先走,他自己断后。这天赶到宜春时,他比别人晚了一个时辰,进得路边客栈,饭也不想吃,倒头睡了,姚景云给他煮好一碗姜汁水,让他喝下。迷迷糊糊中,李培堂作了一夜的梦。他梦进自己在矿井里干活,突然一阵沙沙声,整个工作面冒顶了。他眼前是残肢断臂的工友,一只带着鲜血的手向他伸过来,血肉模糊抓住他的脚时,这手再也没劲了。李培堂身子猛地弹起,他醒了,身上出虚汗,四周的伙计们还在鼾睡中。他定一定心,又沉沉入睡了。一阵清爽的风迎面吹来,他身子动了动,像被风托起似的,不一会,眼前出现一座村庄,村庄上空炊烟缭绕,一群孩子们在村口的晒谷坪上嘻戏游乐。从一条巷口里跑出一个手拿风筝的孩子,看上去似曾相识,当男孩展开手上的风筝往天上放飞时,他大惊失色,那男孩明明是童年时的他。一个老太婆撑着手杖出来,嘴里喃喃地叫着:“又输了,又输了,祖宗的脸面都丢尽了,完了,全完了。”
是他婆婆,他想向前去搀扶她,婆婆随手一手杖打来,击在他胸口上。李培堂醒了。这回醒了,他隐隐的感到心口有一种针刺样的疼痛,李培堂不禁用手按着胸口。姚景云被呻吟声惊醒,赶紧问他怎么哪?见他用手按着心口,知道犯病。赶紧到厨房找来一块生姜,在病人的胸脯上不停地擦着。其他的同伴也过来帮忙,张水生找来热水,让李培堂连同生姜一并吞吃下。忙完这些,李培堂好多了。又过几个时辰,天大亮。姚景云问李培堂怎么样。“如果不好,你歇着,我们回来时接你。”
“好了。”李培堂说着坐起,走了几步。
“你这心气痛,得好好治一治。”姚景云不放心道。
吃了早饭出了宜春城,李培堂推着土车慢慢地跟在后面。
晨曦中的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钻出来。圆圆的红红的,红艳的光束一点点地从山峦、树梢村庄上抹过来,掀开的面纱似的,美丽的阳光倾泻在广袤无垠的田野上,给人以洁净、舒心、光明的感觉。
李培堂突然想起,得给出生的孩子取个名字。“叫晨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