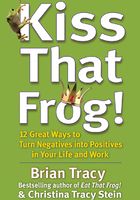15日。泰坦尼克号在这一天沉没。
仅仅因为有了一座冰山,便有了许多为女人和儿童谦让出生命的男人,便有了一顶尘封于海底某处破裂的甲板下不放弃的船长帽,便有了一段让整个世界一次次打捞和慨叹的爱情故事,便有了席琳·狄翁的一首歌,唱出来让后人怀念,怀念古典。
冰山却被我们忘却了,不在画中。
我从清晨坐在这里,坐到黑夜降临,怀念并且感动。玛丽亚号在我的对面,颠簸在风暴之间。真实在咫尺之外,伸手可触。这是怀念之外的真实,而我仍在怀念。我为怀念而怀念。我的怀念于我而言是一种真实,是真实的真实。
席琳·迪翁在《我心永恒》中这样唱到:我知道你仍活着,穿过了遥远的距离与空间。你在,我无所畏惧。你停留在我心深处,我心依如往昔。
这是永恒,但不是所有的永恒。还有多少永恒是我们不曾知道的?譬如还有多少爱情在15日那一天从泰坦尼克号上滑落,坠入冰海而不曾被我们知道?因为没有一首歌。一首歌唱不尽所有。而我们唱歌的时候,一定是某件事情结束的时候。我们只能靠唱歌来表达我们的怀念。
没有冰山的狩猎,没有大海的颠覆,一切都不复可信。香槟酒的温度可以控制得很适口,宫廷音乐和晚礼服可以温文尔雅,这是一种我们向往的文明,一种虚伪。我们正在由野性的真实向虚伪的文明过渡。我们已经说服了自己,并且已经在抵近。障碍是与生俱来的,但完全可以放心,它会被超越。现在有谁来告诉我,超越后的抵近是否真实?
15日只是一次偶然,我的悲哀是,这样的偶然太少太少。
我知道,夜消去之后,15日将隐去,成为人们争相传诵的经典故事,成为人们不断阐释的虚拟历史,那首有关爱情的歌已经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不再是生命浸泡在冰海中呢喃的嘱托。15日之后将是缅怀的时代,即便是15日那天从高高的甲板上坠落进冰海的人,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到15日。一切都是一瞬,留待日后回忆。
冰山不会总是出现。没有冰山的年代,谁来成就爱?
我将在下一支歌中唱到冰山。在它临近的时候,我愿做那个热爱弓弦的琴师。我是乱糟糟逃亡的人群中唯一不歌唱爱情者。
黄昏从窗外轻轻地走过,它是15日最后的信使。我坐在窗前,用香烟支撑,怀念近在咫尺的15日。我知道15日此刻在心疼。我也心疼,为我自己的支撑,更为我无法靠近的15日。
在风平浪静的飞翔之后,有一句台词应该被我们永远记住:活下去,生一大群孩子。
而那群可爱的孩子,他们会不会像我一样,在15日这一天怀想一个不是他们父亲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