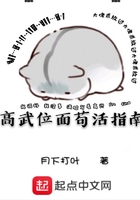一想到四日之后,断臂男坐立不安,眉眼紧锁,思绪万千。
“师父,怎么了?”向榕见断臂男徘徊在床头,疑惑道。
断臂男眼珠转了转,“我还有事,先走了。”
话音刚落,断臂男便急匆匆而去,向榕端坐在床上,望着他的背影,无奈撇撇嘴。
白茉莉出了医馆,直奔居住的客栈,客栈里比较冷清,只有老板娘和伙计。
“唉,白姑娘,你先别走!”老板娘叫住白茉莉。
白茉莉停下脚步,扭过头,“怎么了,老板娘?”
“刚刚有两个陌生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老板娘递给白茉莉一严严实实的包裹。
白茉莉略微迟疑,仔细打量着,见并没有什么特别,言谢老板娘,接过了包裹。
她提着包裹直奔二楼客房,一推门,先是检查了一圈有无异常,才进入。
包裹被她随手放在桌子的中央,并没有重视它。
她推开窗户,探出头,似乎在搜寻着什么,一声口哨,一只白鸽向她飞来。
白茉莉伸出手接住白鸽,熟练的拆掉鸽子腿上绑的卷筒密信。
她拿出卷筒里的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四日之后,井弦县城西郊区。”
白茉莉俊眉微皱,随手抽出一张纸条,写了两行字塞回卷筒,绑在白鸽子腿上,将其放飞。
断臂男大步流星,走路带风,脚下像踩着两朵翔云,神色匆匆奔赴一只耳住所。
恰逢一只耳推门而出,“前辈?”
断臂男不由分说,一把拉过一只耳,躲进屋内。
“我都知道了。”
一只耳莫名其妙的望着断臂男。“前辈知道什么了?”
断臂男眉宇间肃穆庄重,“我知道你也知道,可是我还想知道更多。”
“前辈真是把我说糊涂了。”一只耳微微歪着头,故作匪夷所思状。
“虽说此事与我无关,但我想知道这事会不会牵连到井弦县!”断臂男凝眉注视着一只耳。
一只耳别过头,不去对视断臂男那锐利的眼神,强颜欢笑道:“前辈这是在强人所难啊!”
断臂男恨得牙根直痒痒,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妥协道:“那你开一个条件吧。”
一只耳抽出身子,向后倒退几步,面上虽波澜不惊,实则有些心虚。
“我也知道前辈生活拮据,掰着手指头过日子。”
一只耳同情的看着断臂男,无奈说道。
断臂男直勾勾的看着一只耳,面不改色,一只耳心惊不已,咽咽喉咙,继续道:“或许前辈可以和我做个不用钱的交易。”
“什么交易?”断臂男迫不及待的问道。
一只耳欲言又止,还有些羞答答的模样,过了一会儿才继续说道:“我想知道前辈的尊姓大名。”
“我的名字?”断臂男有些诧异。
一只耳点点头。
他的名字早就被他舍弃了,就像自己的双臂一样,只剩下空荡荡的回忆。
崇祯一年,暗香阁爆发内讧,几千个昔日情头手足兄弟姐妹瞬间反目成仇,成为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这种结果是让人懊恼的,让人难以置信的。
而断臂男也就是在那时被向妹儿砍掉了双臂,从此他便隐姓埋名,四处逃窜,苟延残喘于世。
那个名字和他的过去绑在了一起,他不想再想起那个名字,也不想再回忆起不堪的往事。
一只耳见断臂男沉默不语,目光躲闪,心中不免有些气愤。
断臂男却说道:“可否问些别的?”
一只耳又轻松写意的坐在椅子上,斩钉截铁道:“不行。”
“这......”断臂男左右为难,一时间屋内肃静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断臂男见再与其纠缠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便妥协道:“夏侯义。”
“夏侯义?”
一只耳眉眼上下打量着断臂男,“好名字。”
断臂男无奈一笑,站在原地问道:“你可以说了吧!”
“当然,我怎么会欺骗前辈。”一只耳恭敬笑道。
“前辈不知,那伙起义军确实存在,而且已经聚集到井弦县周围了,晚辈劝前辈莫要趟这浑水。”
断臂男张口结舌,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前辈放心,战场并不在井弦县,您可以继续安享这闲逸。”一只耳笑道。
断臂男这才松了口气,既然不在井弦县开战,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他别了一只耳,心安理得的回到家中,坐在炕头冥想。
他这样安慰自己,自己不过一草民,根本管不了太多,就算是管得了一时,还能管得了一世,只要与自己和向榕无关,他只当不知道。
街上的百姓愈发稀少,先是无缘无故有人失踪,后是青天白日大爆炸,换做是谁能接受?
惶恐不安的气氛不断蔓延升级,一些人家干脆门窗紧闭,不与外界来往。
断臂男自是看在眼里,他无奈哀叹,“芸芸众生,何去何从?”
一眨眼四日已到,断臂男这期间终日活在内疚与自责中,他来到医馆,不顾高郎中阻拦,执意将向榕接回了家。
向榕只感觉莫名其妙,好好的为什么要把自己带回来?
断臂男只是沉默不语,一直低着头,望着窗外。
“师父,到底怎么了!”向榕坐在炕上,伸着脖子,叫嚷道。
断臂男还是不予理会,独自一人坐在那喘着粗气。
“师父!”
“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去就回!”断臂男猛地站起,一双粗壮有力的大腿蓄满了力量,直接从窗户飞出。
向榕一脸茫然的看着已远去的断臂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