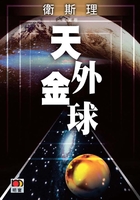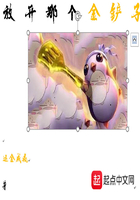因了同样的爱好和感悟,洛北自然而然和希非走得近些。慢慢地洛北知道了一些希非的往事。
希非来自偏远的四川农村,在那个叫诺水的地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希非无奈之下参了军。
在农村,参军可能是心高气傲没有出路而又不想当农民的年轻人唯一的选择。希非当兵的地方就在离西安不远的临潼。那里离他自己的家乡很远很远,听希非说,在他当兵的第二年,母亲就得了胰腺癌,在希非的叙述中,洛北知道了希非母亲得了胰腺癌后还强支撑着身体下地干活,为了不影响希非的进步,他母亲一直不让家人告诉希非她的病情,直到感觉来日无多,怕再也见不到儿子的面才让希非的弟弟给他拍了电报。
希非借遍了战友,拿着三千元钱赶回老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
希非说,他买了母亲最爱吃的柿饼,可母亲已经汤水不进。看着母亲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的身体和那双无神的眼睛,希非号啕大哭,并且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把妈妈背到了县城,胰腺癌晚期的诊断打碎了希非所有的幻想。
希非在和洛北说这话的时候也是凄然泪下。他说:“洛北你知道吗?我还想着等我出息了带着妈妈到处走走,让她好好享享清福,而这一切,我都实现不了了。”希非噙着泪。他说:“洛北,你知道吗?我的妈妈怕花钱,坚决不肯上医院,疼得用手使劲地捶打自己的胸部。看到母亲那样,我的心都快碎了。因为你不知道洛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上面有一个姐姐,已经好几岁了,长得非常漂亮,因为得病没钱医治而死掉了。又过了很多年,妈妈才有了我。”希非长到十一岁的时候,才有了另外一个弟弟。希非十一岁之前的童年里,他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吃妈妈的乳汁,不管妈妈在做什么。妈妈对希非的爱,是任何人替代不了的!
每当说到这儿,希非就会抓着洛北的胳膊哭。从希非眼里流淌出来的泪,一次又一次打湿了洛北的心。
洛北小时候在农村待了很多年,理解希非的境遇和感受,听着希非赎罪般的讲述,洛北总忍不住和他一样流下眼泪。看着这个和自己出身不一样但小时候经历相差不多的男孩,洛北的心里就泛起了许多共同的感受。
希非说:“洛北,你不知道,当我那天背着妈妈从家里一步一步走向县城的时候,四十里的山路没有车,我就这样背着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因为妈妈轻得在我的背上还抵不上一袋米沉。可是我知道妈妈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她可能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上不能活多久了,她就这么依赖地趴在我的肩上。洛北你知道吗?我多想妈妈趴在我的肩上一直趴下去,我希望妈妈看着他的儿子长大、有出息,能为她养老送终。可是在那一瞬间,我知道我的妈妈等不到了,妈妈的肚子长了很多很多的肿瘤,多得数不胜数。洛北,在走那四十里山路的时候,在我的家乡诺水是一年四季温暖如春,其他的东西都不多见,但油菜花漫山遍野都是。记得我们走出家十多里路的时候,妈妈怕我累,坐在道旁一块石头上休息,她央求我说,希非我的儿子,妈妈没求过你什么,能到地里给妈妈采一朵油菜花吗?就是最黄的那种,妈妈想戴一戴。”希非噙着眼泪到地里找到一朵又大又黄的油菜花插上了妈妈的头。希非又背着妈妈继续走,虽然他看不见妈妈的表情,但他知道妈妈是哭了,因为泪水顺着希非背上的衬衣渗到了他的皮肤上。
希非说:“洛北,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尽管我只有十八岁,我觉得我要替妈妈扛起这个家,替爸爸养活弟弟,你能理解吗?洛北!”洛北含着泪点了点头。在那一瞬间,洛北和希非觉得自己彼此的心都贴得很近很近。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有着共同的人生感受。在西北这座陌生城市里,仿佛就有了亲人和依靠。
希非说:“洛北,我妈妈死的时候,很长时间都闭不上眼睛,你知道她为什么闭不上眼睛吗?”洛北摇了摇头。
希非说:“洛北,在我的家乡,男孩子十六七岁是要娶亲的,妈妈看到我没有结婚,她死不瞑目的,她希望看到我成家立业。”当时洛北是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的,她觉得每个做父母的都有这样一个卑微的心愿。现在想起来,洛北才知道希非想向自己表述什么。
因为在不久后的某一天,洛北就是寻着希非说这些话的足迹来到这个叫作诺水的地方。
两个人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每天早晨,洛北还在洗漱,希非的早点就从食堂打好送到了一楼的传达室。这时,洛北在洗漱间里就听到传达室的李大妈用喇叭喊:
“神经系的王洛北请下来拿早点,神经系的王洛北下来拿早点。”喇叭声在刚刚睡醒的宿舍里就成了绕不过去的笑谈。以后见了面,好多男生就会在洛北的后面喊:神经系的王洛北请下来拿早点。
洛北不止一次纠正李大妈:大妈,我是神经生物学系的,你叫错了。
大妈可不管那一套:那么长,我记不住。
此后,大妈依然喊洛北是神经系的。喊久了,洛北也就不再计较,神经就神经吧。
两个人像飞蛾般爱着。洛北很享受被人呵护的感觉,希非是霸道而热烈的,洛北虽然不习惯,但她更喜欢做依赖的一方。
爱情让人弱智,这话不无道理,可恋爱中的人谁能那么理性?洛北这个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生手就这样沦陷在希非狂轰滥炸的追求中。
后来,洛北的闺蜜四丫就忍不住数落洛北:怎么不好好留神?干吗那么实在?一猛子就扎进河里,也不怕淹死?
现在洛北想起来,可能那是自己一生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情感投入。
尤其上解剖课,希非娴熟而平静地在尸体上分离组织,仿佛那不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尸体,每当这时洛北就想起中学时学过的一篇课文:庖丁解牛。洛北就崇拜得不行,因为洛北第一次面对尸体的时候当场晕倒。
洛北常常问自己:究竟希非是什么打动了自己?是那头硬硬的泛着光亮的头发,还是那双漆黑的不沾一丝杂质的眼睛?抑或是他的孝心和独立?洛北着实说不大清。
洛北记得自己当时摸着希非的头发开玩笑地说:“希非,你的头发好滑、好亮啊,苍蝇上去都劈胯呢!”希非就看着洛北傻傻地笑。
洛北和希非虽然出生环境不同,在军医大学,虽然戒备森严且明文规定不准谈恋爱,但怎么也挡不住年轻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年过后,到处都是成双成对的恋人。
没了生命中最初的激动,洛北渐渐地被希非一点点地打动着。虽然来自农村,但希非做事果敢;虽然个子不高但很健硕,还有走着走着突然回转身来微微一笑。这样简单的爱情让洛北觉得踏实可靠。
洛北也对希非付出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她忍不住俯下身来,为希非做她所能做的一切。希非不喜欢洗床单,而他又是油身子,经常是床单铺到一个星期,白白的床单就变成了黑色,每当到周末,洛北亘古不变的事就是在男生宿舍下等希非把他穿脏的衣服、袜子甚至鞋垫拿给洛北,洛北抱着这些东西回到宿舍的水房里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晾在水房中。
有时洗完衣服,洛北坐在小凳子上看希非的衣服在行军绳搭起的晾衣架上随风荡来荡去,洛北就对自己和希非未来的生活多了很多很多的想象。
单恋过、被爱过,仿佛都成了过眼云烟,实实在在拥有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感情还是第一次。
洛北愿意替希非洗衣服,哪怕洗到老。她渴望着和希非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一世。洛北现在想想,自己从当初就错了。希非是一个强烈吸引女孩子的男人,尤其成熟之后。他的眼睛、双唇,笑起来丰富多彩的脸,让一些情窦初开的少女忍不住浮想联翩。洛北想,这些都是希非在今后的生活中打动其他女人的重要因素吧。
冬夏转换,春秋位移,在和希非轰轰烈烈的爱恋中,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最让洛北欣慰的是,希非竟然和自己一样喜爱文学。
在上军校之前,洛北点点星星地发表过一些作品,希非要比洛北强很多。希非曾把对母亲的爱和思念写成小说,发表在了《西北军事文学》上,也就是从那篇文章里,洛北读到了希非内心深处非常丰富而又复杂的情感,在自己只有二十岁的年龄里,洛北分不清爱、崇拜,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情感。她只觉得一个爱母亲爱到骨子里的男人,将来对老婆必定是不会错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心念,洛北傻傻地、痴痴地,甚至有些悲悲地爱着希非这个从四川诺水走出来的农村孩子。
有时候,洛北也很彷徨困惑。她觉得希非对自己远没有自己对希非那般执着和坚定,既然爱,她就想知道希非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很多次在学员队拿信的时候,洛北都能看见来自诺水的信件,字迹非常娟秀。
有一次,洛北很高兴地拿起信件给希非送去,可希非却变了脸,然后莫名其妙地冲洛北发了一顿火。他说:“以后我的信件不要你拿。”洛北非常委屈,倔劲一下就上来,对他说:“为什么?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希非说:“我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可是我不想让你对我的生活干涉太多。”洛北非常生气,冲着希非喊道:“为你拿一封信怎么了?你是不是太多疑了,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呀!”希非冷冷地看着洛北说:“我就是有,你怎么样?”洛北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她想不到希非会这样野蛮地对自己,她把所有的愤怒化作了哭声。在希非的面前,毫无尊严地稀里哗啦地哭了起来。希非恨恨地沉默着,也不去劝哄洛北,洛北哭了一阵,见希非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抹了抹眼泪跑了出去。在跑出校门的那一刹那,洛北就开始替希非向自己作了解释:“嗨,也许家里有什么事,希非不愿让别人知道吧,否则他不会生那么大的气,他只有十九岁。十九岁能有什么秘密呢?”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洛北这样一想,对希非的恨意就小了许多。
在外边溜达了半小时,洛北一次次向校园里张望,希望希非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可终究她失望了。
也许希非有什么难言之隐吧?西安的冬天荒凉而萧瑟。洛北站在夜晚的马路上,茫然不知所终。终归是付出了真情,洛北不想也不愿失去希非,她不知道自己真的离开希非后,漫长的求学生涯该怎样坚持。
洛北顾不上自尊,她转过身又跑到了希非宿舍的楼下。这一次希非没有对洛北张牙舞爪。看见洛北跑来,希非的脸色恢复平常,他跑下楼走到洛北的跟前说:“洛北,我还以为我将要失去了,我的心好痛。”希非的哽咽让洛北彻底投降。
希非抚摸着洛北洁净的脸:“亲爱的,别生气了,我一看到家里来的信,心里就不痛快!”洛北小心翼翼地问:“为什么呀?”“嗨,能有什么呀?这是我堂姐给我写的信,说我父亲想要娶后妈了,我心里不舒服,所以一看见就生气。洛北,你不知道我有多烦,我怕接到家里的信和电话,因为妈妈去世不到三年,爸爸就要娶后妈,我的心里接受不了,你能明白我吗?”希非仿佛刚刚哭过的眼睛满是伤痛,泪花闪动的眼眸烧痛了洛北的心。
洛北用力地点了点头,把脸埋在希非的胸前,一边哭一边说:“希非,我明白,我知道!以后我再也不会帮你拿信,再也不会问了,我知道你难过。”希非拥洛北入怀,在西安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里,两个孤独的人注定只能相互取暖。两个人又重归于好。
这种感情让洛北的生活多了许多许多鲜亮的颜色。除了上课之外,洛北把所有的时间都和希非绑在了一起。他们利用课外时间和周末玩遍了西安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旅游景点。
记得有一次,希非牵着洛北的手来到了秦始皇兵马俑,在那样一个斑驳的、有着浓厚古代韵味的大坑边,看着各种各样、神态各异的兵马俑,或立或倒,或卧或笑。
洛北就对希非说:“你能想象得出,几千年前的那个国家、那个皇帝,还有他宠爱的杨贵妃,你想过吗?你觉得他们的爱情纯真吗?”希非拍了拍洛北有些苍白的小脸,心疼地说:“洛北,你就会瞎想,古代的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洛北不乐意了,噘起嘴说:“当然有关系,我觉得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不那么纯粹,可是杨贵妃多傻呀,她就这么一直爱着自己的那个三郎。”希非说:“洛北呀,你就是多愁善感,一年前你的想法可不是这样的。你想,杨贵妃既然选择了唐明皇,她就知道唐明皇不是只属于她一个人的,他还属于所有的人,当她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就应该有这样的心理承受力。”洛北不认可希非的看法,她觉得无论何时,这样的爱都应该是更纯粹才对。
希非只好摇了摇了头,看着洛北说:“你呀,我的小傻瓜。”洛北说:“其实,说到三郎与玉环的爱情,你还记得白居易的《长恨歌》吗?”希非点了点头。洛北说:皇帝难道和普通人不一样吗?难道他不需要纯粹的爱吗?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在开元二十五年的时候,武惠妃病重,唐明皇决定去骊山过冬,第一次遇见杨玉环,她那令人着迷的青春活力、她那种放松的心态,对于中年已过的皇帝而言,是一个多么致命的诱惑。唐明皇和杨玉环虽然属于黄昏恋,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恋情,都应该是受到尊重的。
希非不同意洛北的话:“爱,都是有条件的!”洛北看着希非没有再往下去问。
在那样一个有些清冷的午后,洛北和希非站在骊山脚下的兵马俑旁想了很多很多,洛北想不到希非是那样的冷静。他对自己也如此吗?
洛北的心跳了一下,但仅仅是一刹那,洛北就释怀了。
偶尔洛北和希非也会有争吵,多半是为了希非多看了哪个女学员一眼,或者是大大咧咧的洛北说的某一句话。在越来越长的相处中,洛北和希非两个南方和北方出生在不同环境中的男孩女孩显示出了个性的差异。洛北天生大大咧咧,说话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而希非是一个心思细腻而又敏感自尊的男人。在这样的相处中,两个人免不了吵架和好,和好又吵架,可是热情却丝毫也没有减退。
学期过半,两个人的饭票就混到了一起。
去食堂吃饭,也是一个人排队打饭,一个人过来吃,当然多半都是洛北主动去做这些事情的。在洛北看来,一个女人为男人多做些事情是理所应当的,而希非也特别享受这样的生活。他觉得生活中有了洛北,一切都变得有点不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洛北越来越多感觉到希非有许多心事,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希非有时会呆呆地望着桌面一句话不说,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有时候洛北会生气地喊一声,希非仿佛从梦中清醒了一般看着洛北,有些不高兴地对洛北说:“你喊什么喊?吓死我了!”这样的时光一点一点地往后挪走,可洛北的心就有了一点点的不踏实,很多次洛北拍着希非的肩问:“希非,你爱我吗?”希非说:“当然!”洛北就摇着他的肩不停地说:“什么叫当然,你要回答我是爱还是不爱?”每当这时候,希非就有些不耐烦,抓住洛北的手抛向一边说:“你烦不烦啊?为什么老问这种无聊的话,我已经回答过你了!”可是洛北并不喜欢这样的回答:“你没有说爱呀!”“我说当然!”“当然是什么意思?当然就能代表爱吗?”“那是!当然难道不是爱吗?”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洛北和希非就这样不间断地争吵。
直到有一天,希非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