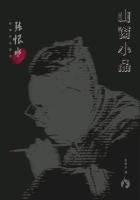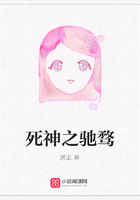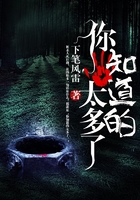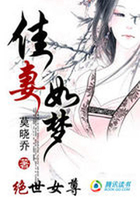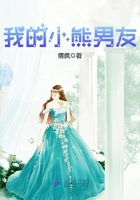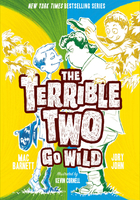说起“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侮,说起近现代史上中国人所受的外国人凌辱,人们总要提到曾经出现在上海公园门口的那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可能存在过的牌子,早已成为一种象征。中国百来年受欺侮、被凌辱的历史,就浓缩成这样一块牌子。许多文艺作品,电影、戏剧、小说、电视剧等,在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时,都要亮出这块牌子。没错,这真是铁证如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寥寥七个字,胜过千言万语,极大地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至今,还有许多同胞提到这块牌子、听见这七个字,便血脉偾张,便咬牙切齿,便揎拳捋袖。
许多人以为,当时上海滩上到处是这样的牌子,这肯定是误解。历史上,只可能有过一块这样的牌子,它曾经出现在当年的上海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门口,存在的时间也并不很长,因为在中国人的抗议下,牌子后来改掉了。熊月之的《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1] 黄艾禾的《上海百年: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2] 等文章,把这块牌子的前因后果说得很清楚。1845年,英帝在上海拥有了租界。为了把这块小小的土地管理好、利用好,英国人成立了“道路码头委员会”。1853年,洪杨的太平军占领南京,上海租界里的帝国主义者感到了威胁。英国领事提议,英、美、法三国联合起来,改变在上海各自为政的局面,共同管理上海租界。这当然就要产生一个市政机关。1854年7月11日,全体租界人会议通过了《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工部局”理事会——在上海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工部局”就是这样出场的。
外滩属于英美租界范围。1868年,外滩公园建成,此后的十多年间,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华人入内。工部局只是关照门卫,只准许“高等华人”进入,“低等华人”则禁入。但怎样判断是否是“高等华人”呢?“红头阿三”一类人,自然只能看穿着打扮了。但走眼的时候肯定会有。有些“高等华人”,是以不修边幅为习惯的,而一向注重仪容者,也会有偶失检点的时候。“高等华人”而衣着不高等,要入园就会遭到拒绝。在这样的时候,中国人,哪怕是“高等”的中国人,一般也就算了。不让进就不进呗,反正被西方人歧视也久矣夫已非一日了,比这更严重的欺侮还多着呢,生什么气?较什么真?但1881年4月5日这一天,公园的门警却遇上了一群生气、较真的华人。这一天,虹口医院的华人医生恽凯英等八人路过外滩,想进外滩公园却被门卫阻止。他们算是“高等华人”,当然有理由愤怒。愤怒之余,他们用英文给工部局总董韬朋写了一封信:“先生:我们都是租界的居民,而且是纳税人,想请问你有什么条文规定中国人不可以进入公共花园?"4月20日,恽凯英等人收到了韬朋的回信:“公园不大,不可能让所有中国人都进来游赏。门警曾得到过指示,只让文雅的衣冠整齐的中国人进入花园。“4月25日,韬朋又来一信,这次态度更强硬:“工部局并不认为中国人有进入花园的权利。”并强调,不许中国人入园,是得到了清政府任命的上海道台的认可的。韬朋说,1868年6月20日,外滩公园将建成时,当时的英国驻沪领事温斯达给上海道台写了一封信,强调:“这块地方(公共花园)是给在上海的外国社区的居民作为娱乐场所或公园之用。”而上海道台并没有表示异议。恽凯英等人质问韬朋依据什么条文限制、禁止华人入园,韬朋便搬出了道台的默许做挡箭牌,这自然很管用。
四年后的1885年,工部局要扩建外滩公园,于是引发了华人的又一次抗议。这一回领头的是唐茂枝、唐景星、谭同兴、李秋坪等八人。唐茂枝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唐景星、谭同兴等七人,或为海关总翻译,或是房地产富商,或当教堂牧师,总之,也都属“文雅的衣冠整齐的中国人”之列。11月25日,他们联名给工部局写信,指出:“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使用公共花园方面遭受到不同的对待是令人不满的,希望工部局想些办法来消除这种招人怨恨的矛盾。”并强调:“工部局拒绝华人入园,仅仅是从种族方面来区别,这不管以权宜之计或国际礼仪作为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要求给一些“高贵阶层的中国居民”颁发入园劵,让一部分“高等华人”享受入园的权利。以《申报》为首的沪上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抨击工部局,声援唐茂枝等人。工部局采纳了唐茂枝等人的建议,决定向部分“高等华人”发放入园券,自1886年5月4日起,华人可凭券入园。但矛盾并没有消除。既然有人能领到入园券,那没有领到而自认为也是“高等华人”的人,就有理由也去闹。1890年,公园管理机构“上海公共娱乐委员会”向工部局报告说,一年来,“申请入园的人逐渐多起来”,使得“迟来的外国观众几乎无立足之地”,还说,发现中国人在入园券上捣鬼,更改日期、过期券再用等手法都出现了。也就在这时,工部局正筹划在苏州河边再次填滩造地,扩建公园,此举遭到上海道的阻止。后来,经工部局与上海道协商,将苏州河边一处河滩建为“华人公园”,专供华人游乐,华人可随便出入。1890年12月,这华人公园正式开放。华人有了一处去处,对那外滩公园的限制华人入内,也就不怎么计较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6月1日,在日益高涨的中国人的反帝声浪中,工部局宣布外滩公园对所有中国人开放。
历史学家熊月之在《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说,上海外滩公园的那块可能存在过的牌子,在中国人心中,引起过两种反应。一种是对西方列强的愤怒和对中国人基本权利的要求,熊月之称为“外省型反应”。这种反应十分普遍,也广为人知。但还有另一种反应,即自我反省,熊月之称之为“内省型反应”。“内省型反应”比“外省型反应”要少得多,少得甚至让人觉得无法相提并论,但毕竟出现过。熊月之列举了数个“内省型反应”的例子。
1909年第8号的《图画日报》,发表了《外大桥公园》(“外大桥”即外白渡桥,外滩公园又名“外白渡桥公园”)一文,说外国在人烟稠密区域,往往建多个公园,供市民呼吸新鲜空气,也是“各国人”工余游览之所。中国则“未之前闻”。外滩公园,“溯当时建筑之始,并不分中外,无华人不准入内之禁”。这篇文章强调,外滩公园刚建成时,并没有限制或禁止华人入园的规定,只是因为中国人入园后,“往往不顾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卧,甚而至于大小便亦不择方向,西人恶之”,便有了对华人入园的限制和禁止,西人并另建一园,专供华人游息[3] 。
1917年,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说,如今租界中外国人的“公共场所”,每不准中国人进入,这实在可谓喧宾夺主之极,以跑马场和外滩公园最具代表性。但是,这与国家强弱无关,只关乎“国民教育”。姚公鹤指出,本来洋人并无对华人的禁令,但屡见华人在公共场所“折花驱鸟,糟蹋地方,无所不为”,于是便有了对华人的限入与禁入。首先对华人下禁令的是跑马场。至于公园禁止华人入内,毕竟道理上有些说不过去,于是另建华人公园。但工部局也须派巡捕在华人公园内照料,否则也会被弄得一塌糊涂[4] 。
1919年,沪上报人陈伯熙在《老上海》中也说,二十年前,外滩公园是谁都可以进入的,“初无分畛域也”。后来,洋人因为华人“多不顾公德,恒有践踏花草之事”,便禁止华人入内,而另建华人公园,专供华人驻足[5] 。
1924年,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韩祖德的《上海租界公园开放问题》一文,也说外滩公园,“以前是公开过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同胞”太没有公德心,遭到洋人的厌恶,才被禁止入内的。文章说,导致洋人下决心对华人下禁令的,是欧战和平纪念开庆祝会那天,公园的花都被摘尽了。文章作者说:“我不敢担保不再发生我们华人的弱点,所以也不敢完全要求自由地开放公园……我愿上海的华人,快教你们子女们去培养些公德心,不要叫他们贪了些花草,便被自私和自利战胜,连累全体的居民都得不到应享有的权利。”[6]
上面说到的几个作者,都强调外滩公园刚建成时,是并没有限制或禁止华人进入的,只是因为华人在公园里太不成体统,才有了限入或禁入的事情发生。1890年,《申报》发表文章说,外滩公园华人凭券入园后,“夏令纳凉者颇不乏人。然有挟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爱花成癖,往往一见鲜花,必欲折取,此非爱花实妬花也”,而华人公园建成后,自然成为华人的乐园,“华人之游于此者,时有滋闹”。文章举了一个例子。公园的长凳,是供数人共坐的。但前日有一人进园后,非要独自占有一凳,不肯与人共享。你既然独霸一凳,就必得有人无处落座。走累了,屁股找不到安放之处,便要巡捕评理。巡捕当然斥责那独霸一凳者,但他并不服气,反对巡捕“骂詈不绝”。游园的华人,见有吵架可看,岂能不看。而既然是同胞与巡捕争鸣,自然站在同胞一边,于是,“咸助此人,大有与捕为难之势”[7] 。
在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产生“内省型反应”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昌济,也就是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的岳丈。杨昌济曾留学日本、欧洲,回国后先在湖南任教,后任北大教授,是教育家、伦理学家。1913年10月,杨昌济在《湖南教育杂志》发表了《教育上当注意之点》一文,其中说:
吾国人有一大弊端,即不洁是也。衣服不洁,口齿不洁,体肤不洁,器具、书物不整,随地唾涕,当道便溺,浴室、厕所尤为不洁,较之西洋、日本,真有自惭形秽者。无怪乎西人自以为文明,而吾国人为野蛮也。试观汉口、上海之洋街,皆宽平洁净,而一入中国人街道,则狭隘拥挤,秽污不洁,相形之下,判若天渊,而彼处居民,终古如斯,毫不知变。此真可为叹息者矣。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曰“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此真莫大之奇辱而安之若素,此日本人所嘲笑以为大国民之大度者也。
杨昌济进而说:
平心论之,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西人所为,虽欺人太甚,亦吾国人有以自取之。不急改良习惯,养成与西洋人平等交际之资格,此等耻辱终无湔洗之期。[8]
杨昌济这话就说得更坦率了:西洋人那样对待华人,其实是华人活该!杨昌济点明了与西洋人平等交际之“资格”问题。你要别人平等待你,自身先要有让别人平等待你的“资格”。
熊月之先生在《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中慨叹,自1928年外滩公园取消对华人入园限制后,外滩公园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就只有“外向一面的歧视与反歧视”了,至于内省的一面,则不见了,“在历史教科书中不见了,在学者的笔下也不见了”。外滩公园的限制和禁止华人入内,那块可能出现过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不应该仅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材料,也应该成为公德教育和培育公民意识的材料。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它只是被片面地利用着。
说1928年后没人对这块可能出现过的牌子产生“内省型反应”,也不尽然。近读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我有些惊奇地发现萧军也是一个对外滩公园产生“内省型反应”者。
1941年7月3日,萧军在日记中写道:
晚饭后独自去桃林坐了一刻,看见一个人跳过栏杆去小便,回来我向他讲:“同志,你不对嗳,外面有厕所,为什么在里面小便呢?
那里有门,为什么要跳栏杆呢?”我是微笑着说的,那人向我惨惨地点了一下头,脸色不好看地背过去了。我看着他那发气的背影,用“啪啪”装作自然的样子把扑克牌摔在石桌上的声音……过了一刻他赸赸地走了,大约他受不了我的精神压迫了。我知道这会给予他一个好的启示,这是比辱骂更有力的刑罚。从此我联想到中国人的国民道德,以及在上海外国公园不许中国人进去的故事,从这很小的事,那是可以观察出一个国民的自制力和自尊心。起始要说他时,我也迟疑着,但一转念,觉得这“不管闲事”的观念不对的,就说了。[9]
萧军也认为上海外国公园不许华人进入,与中国人的“国民道德”有关。萧军是铁血男儿,是坚定的爱国者,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过切实的贡献。他能在上海外国公园不许华人进入一事上有清明的内省,而且是在抗战时期有这种内省,令我对其刮目相看。上面说到的“内省型反应”者,在今天是极容易被骂作“汉奸”的。但是,今天活着的人,有几人有资格说萧军是“汉奸”呢?那些“五毛”,那些“自干五”,那些“愤青”,你们有资格吗?
我屡次说“可能”有过那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因为是否曾经有过这样一块牌子,一直有着争议。洋人的确限制和禁止过华人进入外滩公园,也的确限制和禁止过狗进入公园,但是否明确把二者放在一起作为禁入的对象,是一个悬案。在历史资料中查不到这样的条文,更无照片为证。据熊月之先生在《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中说,1885年工部局颁布的公园游览规则,共六条,译成汉语是:
(1)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
(2)小孩之坐车应在旁边小路上推行;
(3)禁止采花捉鸟巢以及损害花草树木,凡小孩之父母及佣妇等理应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
(4)不准入奏乐之处;
(5)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
(6)小孩无西人同伴则不准入内花园。
这样的规定,当然歧视华人的意味已经十分浓重。虽然没有资料证明工部局挂出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的牌子,但一些人在文章、讲演中说亲眼见过这样的牌子。对此,熊月之在《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中解释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公园的确曾经挂出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第二种可能是,人们把规定的第一条“脚踏车与狗不准入内”与第五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搓揉在一起,归纳、概括、演绎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的“规定”。对于华人来说,第一条和第五条最刺眼,一眼看去,只记住这两条,并且把两条合并成一条,是自然而然的、下意识的行为。我以为,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于情于理,工部局都不大可能在游园规则中明确把“华人”与“狗”紧紧放在一起。
1924年9月,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倒掉了,原因是附近的民众总去挖取塔上的砖。在北京的鲁迅闻讯,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两文。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说,中国向来有着两种破坏行为,一是“寇盗式破坏”,一是“奴才式的破坏”。“寇盗式的破坏”出现在所谓的乱世,暴民造反、历史上所谓的“农民起义”,总体现为“寇盗式的破坏”。而“奴才式的破坏”则以日常现象的方式出现在太平时候。鲁迅说,雷峰塔砖的被挖,只不过是眼前的一个小小的例子。龙门石窟的佛像,大半缺膊少腿;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往往被撕去。凡是公物或无主的东西,能够移动的,则被偷走;不能移动的,则被损坏。人们仅仅因为一点微少利益,也会毫无顾忌地破坏一个“完整的大物”[10] 。
抗战期间,费孝通在昆明写了一系列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后来结集为《乡土中国》。在《差序格局》一文中,费孝通说,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便是“私”的表现。但能够扫清自家门前雪,“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一般人家,是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便完事。苏州人家往往后门临河,听起来诗意盎然,文人墨客比作威尼斯。但“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这水道本来就不畅通,而人家却什么东西都往河里扔,把河道当作垃圾桶,甚至当作厕所,居家临河,“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为什么呢?——这种小河是公家的”。因此,在中国,“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一个院子,也只有两三家合住,但总是荒草丛生,公共走廊上也照例是尘灰堆积,厕所更是难以插足。没有一家肯管这些“闲事”。谁若管了,连半声谢意都得不到。于是,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公德心就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费孝通说,中国人,从上到下,没有不害“私的毛病”者,而“现在已成外国舆论攻击我们的把柄了”[11] 。
上海外滩公园的限制和禁止华人入内,如果从宏观方面说,当然也与国家强弱有关,因为如果不是中国处于弱势,就不会有“租界”这样的地方出现。但如果不那么宏观地看问题,如果就事论事,那这件事,还真与国家强弱没有关系。外滩公园门前的华洋冲突,是一种“公德”意义上的中西冲突。百多年过去了,中国毕竟“强大”了,现在,这种“公德”意义上的中外冲突,移到了国外。跑到国外,到人家的地盘上去与人家冲突,这确实是“扬眉吐气”了,变化确实很巨大了,但没变的是公德心的缺乏仍然是“外国舆论攻击我们的把柄”。这些年,中国的游客在国外出了多少“洋相”、惹来多少鄙视、厌恶、憎恨啊!以致国家领导,都要亲自呼吁国人在国外少吃方便面,勿乱扔垃圾!就是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间隙,上了一下网,就看到一条消息:“中国大妈在泰国机场晾内衣”。泰国媒体播放了视频:鲜红的胸罩、黑色的内裤,晾在机场的椅背上。泰国媒体在惊叹,在嘲笑。仅是在泰国,中国人这些年干下的“丢人”、“丢国”事,就颇不少。人家路边的三轮车,骑着就走;王宫面前的栏杆也敢推倒,受到指责不认错反恶语相向;在飞机上对乘务人员耍泼、撒野、发飙,也有“国人”与“国人”在飞机上打架甚至打群架……百多年来,八九十年来,六七十年来,如果谈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时不只是愤怒谴责帝国主义的欺人太甚,也反省一下我们的公德太差,如果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块牌子时也讲一讲我们自身的问题,到今天,情形是否会好一点呢?我们是否会在国外少出一点“洋相”,少做一点“丢人”、“丢国”的事呢?
十年前,当我在东京小巷的电线杆上,看到警视厅张贴的用简体汉字书写的“严打入室盗窃!”的告示时,很有些愤愤然。这不明显是特意针对我这样的从中国内地来的人吗?当时很想去警视厅抗议,想想,抗议的理由不充分:人家在自己的地盘上贴什么,你管得着吗?便只得“国骂”一声后作罢,算是“好汉打落牙和血吞”。我想,如果有一天,外国人在自己国家的公园门前挂出“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们再去抗议,就被动了。
2015年2月2日
注释
[1] 熊月之:《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见《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版。
[2] 黄艾禾:《上海百年: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见《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0期。
[3] 《外大桥公园》,见《图画日报》1909年第8号。
[4]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5] 陈伯熙:《老上海》,上海泰东图书局,1919年版,第一册第9卷。
[6] 韩祖德:《上海租界公园开放问题》,见《时事新报》1924年4月14日。
[7] 《中西异好说》,见《申报》1890年7月8日。
[8] 杨昌济:《教育上当注意之点》,见《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9] 萧军:《延安日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上卷,第206-207页。
[10] 见鲁迅《坟》。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6月版,第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