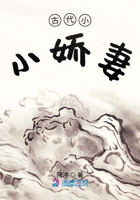温暖的阳关洒在脸颊上,让奕歌从混沌中挣扎着醒了过来。看着破旧而肮脏的大牢,她似乎有些恍惚,她记着昨天夜里好像巴尔来过,随即又像是嘲笑自己般,自己怕是疼得失了理智,巴尔怎么会到国公府的大牢里来找自己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昨日险些就死掉了,今天竟然不是被痛醒的。可身体似乎不满她这天真的想法,几乎在她意识回来的一瞬间,从小腿到手指尖,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在叫嚣着,撕裂着,乞求着让主人找大夫来医治。
奕歌闻到了自己身上有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那味道就如同她儿时在街上碰见过的乞丐,当时她还颇为嫌弃地跑开,却被悟念师太拉了回去,放了一个包子到他面前的破碗里。等走远了,悟念师太才开口说道,“他身上的疮破了化了脓,没有银子看病,过几天便会死了。”
她那时尚且不知道化脓是什么,这时瞧见自己臂膀上被抽裂开的地方起着恶臭,黏糊的淡黄色的液体覆盖在上面,心里却没有半点厌恶的意思。她只是奇怪自己这瘦弱的身子,竟然比她想的还要坚韧些,果然像悟念师太说的,自己有九条命啊。突地,微凉的液体便从眼眶里滑了出去,她都还不来及弄清楚自己为何哭,这泪便藏入了身下的稻草,没了踪影。自己能在这大牢里挨几天呢?三天么?或是四天?最好是明天便再要不要醒来了吧,身上的伤实在是太疼了。
可一边任性地想着就这么死掉罢了,心里却仍有个地方执着地扯着自己的意志,呼喊道叫自己活下去。她还没有来得及报答悟念师太,没来得及和何大娘还有刘爷道别呢,还有滁州那么多的伙伴,她连一句道别都没说,怎么就能死掉呢?她见多了身边的朋友,因为没吃的,总是突然在某一个夜里便没了去向,她总是时常怪罪他们不讲义气,去了别的地方也不同她说一声。直到有一日清晨,她去山下帮悟念师太买香烛,亲眼看见昨日还在一起说笑的伙伴,倒在城墙角,尸体都已经僵了,来来往往的行人就好似没看到这死掉的孩子一般,只顾赶自己的路。她那个时候才第一次感觉到人命是不值钱的,最起码他们这些人的命是没有人珍视的,倘若不是有悟念师太,有何大娘,有刘爷,有梨洛姐姐,自己也会同无数个伙伴一样,在某一夜便突然消失了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吧。
想着自己的死讯要是传回了滁州,不知道悟念师太是不是会哭得痛昏过去,还有那些总是平日里逗她玩儿的大叔大婶们,他们会哭么?他呢,会哭么?她多想看看啊,看看那个说想陪自己一辈子的人,如果知道自己死了,会掉一滴眼泪么?若是时间能重来便好了,她绝不会在那日跑进献王府里,便也不会落到这般境地,仍旧是那个无法无天的小乞丐,那可多好啊。
偌大的房里,能让人静神养心的檀香一点点飘散进或站着或跪着的每一个人鼻间,稍稍安抚了每一个人焦急的心。只是一直站在床侧的宋玉隶仍然紧紧皱着眉头,死死地盯着正在为七弟把脉的大夫,等大夫一把完脉,便开口道,“如何?”
这大夫正是先前想出以毒克毒的那一位,他当日走了一招险棋,成了便能让自己飞黄腾达,败了就人头落地,可他原以为自己能过几天舒坦日子,还没舒坦几天呢,就被请到了这国公府,一看还是献王,当即便觉着不妙。又见献王脸色煞白,嘴唇发紫,更是不敢接这活,可这是在国公府,旁边站着大理寺少卿和三皇子,他就是有十个脑袋都不够拒绝的。可这一把脉,便知道这毒已入心肺,怕是使什么法子都来不及了。可他哪敢把这话明了说,那不是直接拿刀子往自己身上砍么,但要是不说明白了,日后这献王出了半点差错,那自己全家都得跟着陪葬。
“王爷的情况怕是不太乐观,这毒本是两相克制,慢慢调养便能化解了,可如今却失了平衡,致使毒入心肺,实在是极难医治。”
宋玉隶不愿多浪费时间,“不管是药材难还要药引难,你只管说别是了。”大夫擦了擦额间的细汗,躬了躬身子说道,“草民倒是知道一个方子,这苗疆有一类蛊师,他们养的蛊虫能进入人的身子里吃毒,只是这蛊虫向来是苗疆人自己养着,草民也是听别人说起过,具体有没有这种虫子,草民可就不敢担保了。”
“你可知道在哪儿能找到这养蛊虫的蛊师?”
宋玉隶虽从未听说过什么能吃毒的蛊虫,但此时已是到了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传信去给父皇,来回便要耗上数十日功夫,七弟这才只不过过了一日,便嘴唇发紫,再多等几日恐怕就。。。
“草民村里倒是有这么一位,只是平日里从不见他出门,至于他养的蛊是不是这吃毒的蛊虫就更难说了。”
宋玉隶知道这大夫是怕到时候找不到这能救命的蛊虫,自己会迁怒于他,便开口道,“你只管带人去,不论他养的是什么蛊虫都叫他带过来,若是能治好,本皇子定有重赏。”
大夫领了命,便同一众侍卫即刻出了国公府,往自己村里赶去。宋玉隶屏退了在底下跪着的一众大夫,顿时这房子里便空旷起来。宋玉隶知道秦淮阳有话要同自己说,示意他到房外去说。
“你这几天问出了什么没有?”
“奕歌只说那玉镯是自己买的,我看一定是她背后的人同她关系匪浅,否则她不会如此费尽心思保护他。”
“本皇子可是交代过你的,切不可用刑,她若不招,先关着便是,等七弟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了,本皇子自会亲自调查。”
“是。”
秦淮阳微微低垂了头,不让宋玉隶瞧见自己眼里的狠戾和不顾一切,若是等献王身体好起来,恐怕就没有机会让一切水落石出了,就算日后要被问罪,他也一定不能让老师死得不明不白。
国公府的下人们瞧着渐暗的天色,心里不禁有些雀跃起来,总算是又熬过了平安无事的一天。这两天,府里被关押的宾客也都陆陆续续被放走了,留下的也都是些那日到过厨房附近的,但都没找着什么实际的证据,估计再等两天也都能放出去。就是那个叫奕歌的,自己一个人做的坏事,倒叫这么多人都陪她受苦。只是大家都不明白了,这奕歌被抓起来,翠萝和厨子都做了人证,她自己手里戴的镯子是物证,这人证无证都齐了,怎么还留着她的命呢。但这案子交给了素来有“断案如神”之称的秦少卿,想必用不了几日便能给大家一个说法。
可还没等来一个说法,国公府的大牢便在子时突然涌入了一帮黑衣人,这帮黑衣人倒像是凭空出现的,杀了狱卒们一个措手不及,等想到要拔剑抵挡时,已经被一剑封喉没了气息。几乎是在眨眼的瞬间,看守大牢的几名狱卒便悄无声息地没了性命,这群黑衣人似乎并不想多招惹是非,解决了狱卒后,便步调统一地走向了最里的牢房,用剑一劈,牢房的锁链便应声落地。
黑衣人一个接着一个走入牢房里,其中一名黑衣人突地挥剑刺向躺在地上不知是死是活的女子,“叮!”挥剑的黑衣人似乎没想到会有同伴阻止自己,不满地看向用剑抵了这一刺的同伴,责怪道,“你干什么?难道不清楚塔扎吉大人的命令么?”
“那你们可知道本世子的命令?”
低沉而威严的话语回荡在这大牢里,惊得一众黑衣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直到看见那人扯下自己的面罩,刀削般冷冽的脸庞暴露无遗,让黑衣人们大惊失色,纷纷跪倒在地,“参见世子。”
“唔!”
突地,方才那挥剑想要杀掉奕歌的黑衣人痛苦地捂着喉咙,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拿剑冷冷盯着自己的世子,他恐怕到死都不能明白,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死。
“你们看清楚了,地上躺着的是本世子的世子妃,若是谁再敢动半点歪念头,本世子不介意多送他一程。”
黑衣人皆低垂着头,谁也不敢辩驳世子的话,待过了半晌,直到听到世子说“撤”,众人才抬头起身,沿着来时的道路迅速消失在了夜色中。
奕歌的消失让秦淮阳大动肝火,甚至不惜瞒着宋玉隶派出了江湖杀手去追踪,可是被宋玉隶知晓后便立即禁止了,让他暂时不要管此事,即刻赶回皇宫。皇后的哥哥镇北将军的捷报已经从前线传了回来,这几日宫里想必就会有大的动静,他们在宫里不能没有眼线。秦淮阳虽心有不甘,但是献王是老师最为宠爱的外孙,他知道老师一生的愿望便是让献王坐上皇位,如今老师去了,老师的遗愿便是他接下来要死命去完成的。当下,秦淮阳便收拾了东西往宫里赶去了。
秦淮阳刚走了大约半个时辰,昨日回村里找人的大夫便带着人回来了。那蛊师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进了国公府瞧见了宋玉隶,既不行礼也不说话,只是板着张脸,瞧不出任何情绪来,只是眼角的不满仍旧泄露了他心里的想法。宋玉隶知道时间紧急,也就不在乎这些繁文缛节,“你便是蛊师?你养的蛊,能吃毒么?”
蛊师微微抬了抬眼睑,似乎极为不屑,“我养的蛊虫,不是谁都能用的。”言下之意,倒是他们要找的蛊虫,宋玉隶心里便松了口气,“你有什么条件只管提便是了,不论是多少银子本皇子都答应你。”
“呵。”
这一声嗤笑在安静的大厅里显得尤为刺耳,一旁站着的大夫冷汗霎时便下来了,一个劲地给蛊师使眼色,让他悠着点,可蛊师自然是不将这些皇子王爷的放在心上,他隐居世外早已多年,若不是这群官兵以村人的性命相威胁,这王爷的命同他又有何干系。
“你不要银子?那你要什么?只管开口便是。”
“我什么都不要,这蛊虫可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要想我救人,就得备好一间房,里面除开一张床,一盆温水,一块干布以外,什么都不要放。房里不能有任何人,只有门口能站人,若是做不到,这人,我便不救了。”
将七弟同这来路不明的蛊师放在一个房里?若是放在以前,宋玉隶断然是不会答应的,这天底下想要七弟命的恐怕不止那么两三个,这要是是别人事先设好的圈套怎么办?七弟如今终日昏迷着,这蛊师要是想杀他易如反掌。但他决定赌这一把,就算这蛊师当真有这胆子赶在国公府杀人,他也绝不会让他活着走出去。
宋玉隶下令让下人们依照这蛊师的要求备好房间,再派了一众侍卫,将房间团团围住,只要里面有一点不妥的声音便即刻进去取那蛊师的人头。直到房门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那蛊师关起来,宋玉隶的心仍是一直吊着,总有不好的预感。可眼下又没有别的法子,瞧见一旁的大夫一直抖着身子,便叫人将那大夫抓了过来。
“这蛊师,是什么时候到你们村子上的?”
大夫回想了下,“有一段时间了,大概是两年前,当时他病得快死了,我就试着救了救他,没想到竟然救活了,他好了之后便在村子里住下了,只是谁也没看见过他出来过,性格古怪的很,村子里的人也就都不和他打交道,可每次只要有谁生了大病,我又救不好的时候,他便会突然出来,用他养的蛊虫将人给救活,算是我们村里半个活神仙了。”
听着,宋玉隶便稍稍放了点心,依着这么说,这蛊师倒真的有些法子,只是这身世实在古怪,苗疆人素来不喜同外族人打交道,所养的蛊虫若是为外族人所用便会被赶出苗疆,这蛊师怕是当年犯了什么错,被赶了出来,这么看同宫里怕是没什么关系。
房间里一直寂静无声,叫外面等着的人很是着急,宋玉隶都快将这房间绕着走上上百圈了,中午吃了午膳便又赶来这儿守着,问了侍卫里面可有什么动静,可侍卫都说里面没听见半点声音。他正要觉着不对,要推门的时候,里面又传来一句,“住手。”宋玉隶便不敢再动了,沉了沉气便又开始在房外踱步,好让心里的焦灼稍稍减弱一些。
直等到星星都忍不住探了个头出来瞧着下面的情况,这紧闭了快一日的房门总算是开了,宋玉隶一个箭步便迎了上去,“如何?”
却见那白日里还神采奕奕的蛊师,好似在房里消耗了自己所有的精力一般,面色十分憔悴,就连声音都疲惫不堪,沙哑着说道,“这毒不好解,得再用上三日的光景,谁都不准靠近这房间。”